(一)
我这人向来自食其力。父亲教导我别指望他人会善待自己,继母告诫我只有独立才能赢得生活;我都尽力做到了。至少在十七岁半那年离家之后,我从不曾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我见过为了口吃食便出卖自己的女人,而我不曾那样堕落。若他人只是走马观花地匆匆一瞥,的确会觉得我的生活状态糟糕到了那种地步。为了得到某些东西,我也曾举棋不定,最后又做出愧心的事来。没错,我在人生路上做过一些“错误”的决定。即使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皈依宗教,他仍能判断对错、区分善恶。
我的名字叫做贾丝汀·米德,在我四十三年生涯中,我爱过的人就那么几个。不,那是夸张的说法。就只有两个,因为自己的愚蠢和自私而失去的那两个;一个是我的儿子,另一个是我的狗。
(二)
我再次离开了队伍。夕阳西下,我坐到商店外那张长椅上,身旁是那个黑人老头。我将旅行包放在膝上,克制住自己不把头放上去休息。九月的黄昏之光在身后渐渐落幕,阴影在我的脚边一点点地越变越长。
“多美的夜晚啊。”我的同座轻声细语的说着,好像挺怕说出口一样。
“我想是吧。”
“别随口应付我啊。”
“伊利市巴士站离这儿有多远?”
“这里是康妮奥特维尔,伊利市在三十英里以外呢。”
“那我还是别走着去那儿了。”
“所以得坐巴士啊。”
我知道还得再回商店去,拿出一些所剩无几的备用现金,买一张能到另一个城市去坐车的车票。我忽然感到饥肠辘辘,以及计划落空后的精疲力竭。我想躺下来休息。米契辜负了我的期望,他并没有把我带到伊利市,只把我送到了伊利县;这跟波士顿市郊的人声称自己是波士顿人别无二致,没想到我会再次踏过同一条河、被同一伎俩给耍了。
“坐车是为了回家吗?”
“不。那是我父亲的家。”
“不也是你家吗?”
“好长时间都不是了。”
“可你也不是这附近的人啊。”
“是的。我也是误打误撞到这儿的。说来话长了。”
我们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看着夜影逐渐向周围延伸。我打量着巴士时刻表,仿佛它是茶叶。我想找一班更快、更便宜且更舒适的车,能够像变魔术一样将我带去波士顿,当然这样的车是不存在的。
“那么你家在哪儿呢?”他的声音仍旧比耳语声大不了多少,使得他的问题听上去比这话字面的含义更具哲学意味。
我突然灵光一闪,为何不返回西雅图呢?反其道而行之,等待亚迪回到城里、出现在酒馆,我就能好好地教训他了。这个有板有眼的推想让我激动不已;可紧接着,我意识到亚迪更可能独自去酒馆,而不是带着狗,我可不愿冒这个险。不,我还是得追上他才行。
终于,我回答这个老头子说:“哪儿有我的狗,哪儿就是我的家。”
“我曾养过一只不错的狗,陪伴我度过了好些年苦日子,却从未有所抱怨。”
“狗很少会抱怨。”我说着,背上旅行包回到商店里。再出来的时候,老头子已经走了。
我面向车厢左后方弯腰坐在了靠窗的位子上,窗玻璃上划过一道道水渍干涸的斑痕,那是之前的暴风雨所遗留下的。我感到精疲力竭,晚餐就吃了微波炉加热的玉米煎饼,此刻却还堵在腹部中间,弄得我十分难受。
我偷带了一罐可乐上车,以冲淡包装食品的金属味儿。三十英里这么远的路程够我打个盹儿了。我阖上双眼,却看到了马克,我脑海里全是它那银白色的小脸蛋,鸳鸯眼上少许黑毛。我的狗马克西姆,是以《与星共舞》中那个交际舞者的名字命名的。我是那个节目的铁杆粉丝,尽管我这辈子唯一一次跳交际舞是在初中;当时风靡迪斯科,体育老师却要我们全去学跳方块步。所有人都认为我给狗取那个名字是因为我俩一起跳舞,但事实上,我恰好是在命名之后才知道犬类自由式的。
送给我狗的人叫罗德尼·帕里斯。他人很好,却有个不幸的缺陷——他结婚了。当然,我和他相好之前对此并不知情。我从不跟结了婚的男人约会,对那些声称“已经分居”的男人也是敬而远之。然而他确实结婚了,这令我失望之极,因为我真的喜欢他。这么久以来,他是第一个每次见面都能使我快乐的男人。在我发现了他的妻子——更确切的说,是她发现了我之后——我就跟他断了。我当着他的面关上门,转过身来,慢慢瘫倒在地。我经历过太多次失恋,不会不知道痛苦总会过去的,但那一刻我被击垮了。我的小狗这时大概四个月大,猛地跑到我瘫坐的地方,把它的泰迪熊玩具搁到我的膝上。我这个从不流泪的女人继而失声恸哭,它便满是担忧地看着我。我抽着鼻子,忍住随时会决堤的滂沱泪水,抱住它发誓说,它就是我最需要的那个人。
至今如此,不曾改变。
此刻,我感到那么久以前强忍住的满怀悲恸正顺着胸口往上翻涌。我两手握拳,抵住紧闭的双眼,满心希望没人坐在旁边,听到我像心碎少女一样抽噎的声音。为了抑制住想哭的冲动,我从口袋里掏出了手机。手机电池量所剩无几。我阖上手机盖,祈祷亚迪能在电池用完之前打电话给我。不知何时我才能给手机充电。车子驶进伊利市巴士站时,天已经全黑了,我还得迎接这个漫漫长夜。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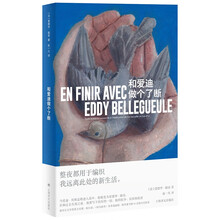
这是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和《马利与我》《我在雨中等你》一样,读者很难不为这样一本以狗为主角的小说动容。——《柯克斯评论》
这本感人至深的小说很让人有所共鸣。——《出版家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