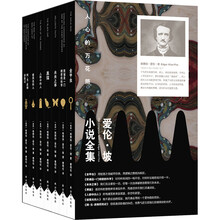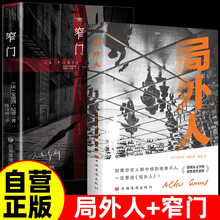《潘热作品选集1 某人》:
我热爱大自然。在办公室里工作竟把大自然给忘了可真蠢。我本来是绝不会想到您会如此缺乏与大自然的接触。我们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习惯于某个作息时间、某项工作、某种安排。我们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根据自己的工作和闲暇,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当我们有闲暇的时候。闲暇。多么可怕。我说的是以前的闲暇,我以前有过的闲暇,在办公室里,以及那些在咖啡馆里的交谈,那些浪费了的时间。所有这一切都是操心怎样平易近人,怎样生活在群体之中,怎样关心别人,怎样对别人推心置腹。我知道这会带来什么。而我在大自然里做了什么?我甚至已经不知道大自然就在那里。以及鲜花、树叶和昆虫。而当人们意识到这些的时候常常太晚了。幸亏,幸亏我逃出了地狱。我及时地这么做了。我发现自己忘记了大自然是在一次散步中偶然意识到的,就像这样,而上帝知道我是不是很少散步。我离开办公室来到了这里。应当诚实地说我不是独自做出这个决定的。有些事情帮助了我。我已经被人们所知道的那些麻烦事搞得烦恼到了极点。总之我对此已是忍无可忍了。
这里。就是这里,又是环境。应当继续描绘其轮廓吗?让我们慢慢来吧。
唉,这里还不是乡村,也不僻静。我还是与别的人搅在了一起。但至少不是办公室了,描述应当准确。这是一所家庭式膳宿公寓①。位于郊区。几公里外就是真正的乡村了。我住在这里大约有十年了吧,我已经搞不清楚了。反正是在十年前我做了一件事情。就在我再也无法撑下去的时候,在我就要忍无可忍的时候。一个处境与我相同的朋友把我拖进了他的计划。我那时攒有两三个钱,他也是,我们把这些钱合起来买下了这所膳宿公寓。这所房子,应该说,是加斯东想到把它用来做家庭式膳宿公寓的。他需要我同意,让我们大概能够敞开肚皮吃饭。几个寄膳房客,最少量的。就这样。
花园很难看。二十米长二十米宽。中间是那棵栗树,而顶里头是杂物间,那是一间木板做的小杂屋。由于旁边那个工厂,我们不能待在花园里。到处都是黑色的粉尘以及工厂食堂烧焦的油烟味儿。到了夏季真是令人遗憾。我们一年到头已经是人堆人地挤在那间杂乱的大屋子里,本来是完全可以去别处的。开始时我们曾试着每天打扫一下花园,但那可真是一件累人的活计。一层油腻的粉尘。光只打扫一下椅子和桌子就需要许多时间。我们放弃了。
我真诚地暗自寻思,我会一直寻思到底,我是否正好切入问题的要害。我已经感觉到了威胁着我的危险。除了环境以外,还有居民。与居民一起的,还有我。如果不做自我审查,我绝对无法平静地谈论他们的事情,甚至无法描述他们。一切都交错在一起,一切都被弄乱了,一切都相互阻碍。谈论加斯东已经使我感到不舒服了。我原打算不说姓名的。只说经理,房间一,房间二。这样不具名,就会有点儿模糊,有点儿不确定。杂烩,并不明确。但是有个声音在对我说,这可能会让人感到厌烦。难道我会让自己令人感到讨厌吗?我认为不会。当别人询问时,就应当尽可能地给予准确的回答。我说什么来着,询问。谁询问我?没有人,大人。请不要说我在回答问题。因为有人说过了。有人早就说过。在谈到我生活中的其他事情时,当我曾试图摆脱那些问题时。他在回答问题,你们看。那大概是警察。带有警察的口气,他必须回答,人们强迫他,人们逼问他。这一类蠢事。我的草稿想必写得不好。错到这种地步,给人如此错误的印象。真令人讨厌。至少是缺乏能力。总之我不想给人我在回答问题的印象。尽管我在回答问题,也不要给人这个印象,我刚才无意中说过人们在询问我。我是不由自主说出来的。够了。又是一件需要解释的事情,但说到底这样更好,推迟了切入问题要害的时间。
这个印象,这只是一个印象,它大概由来已久。在一开始,在我的初稿中,我就已经感觉我在回答问题。在某处有个模糊的问题我回答了。更为模糊的,甚至不是回答,请大家理解我。没有一个诸如您到哪里去或者您在做什么这样的句子。并不明确但出现了。或许是太不明确以至于我把它当成了问题?这是可能的。我本该伸长耳朵,本该再次开始的。我本来可以避免回答,如果不是必须的话。此外,可能那个时候我在虚构,我在尽力保护自己,这些拙劣的手稿把我折磨得痛苦不堪。我尽力将其中的错误掷回给来自某处的那个询问。这是可能的。不管怎样我继续用极其模糊的印象来回答。感觉非常地模糊。感觉。迷雾。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此外,总是因为我那功能减退的耳朵,我听到的就是这样或是我认为听到了答复。一个真正的贞德在事后证实这一切是很痛苦的。进入无声对话的状况并且再也无法摆脱它。比痛苦更甚。而我们本来可以做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登山,跑步,我不知道。误入歧途,像这样,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愚蠢地,把时间都用来寻思自己是怎样弄错的。因为现在,我吹毛求疵、耍花招也没有用了,我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是弄错了。已经无药可救了。即使竭尽所能。
不要失去理智。让一切都整齐有序,掌握一切。我用一个自己的问题开始这篇报告。这不一样。那张纸在哪里?一直回到这个问题上,不要看不到它。
当我在花园里搜寻的时候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记忆似乎中断了,分散了。我是不是探着脑袋朝花园大栅栏门看,是不是一边注视着街头一边瞎想来着?我是不是在想象对面花园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什么也看不见,那里也有一堵墙。右边有几棵杏树怪物似的探出墙头。房顶上有一个风向标,呈机车形状。邻居是一个铁路退休人员。人们从来没有见过他。确切地说是我,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大概我出门的时间与他不同。因为我出门是为了去采集植物。但膳宿公寓里有些人看见过他,甚至跟他说过话。除非我搞错了,除非是另一个人。邻里关系、家长里短这些事情最让我心烦。我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无关痛痒的小消息,这些小消息可能会使我分心。但屎就在不远处,我提前避开了。我说邻居们让我感到心烦。那么为什么要去想象他们在墙后干些什么事呢?难以理解。我的秉性令人难以理解。因为当我想到他们的时候,除了一些穷光蛋的故事,我想象不出别的事情,可我还是要想象这些故事。可能在这以后我就能较为容易地摆脱这些事情?也许。但这仍然是难以理解的,因为严格说来它们什么也不能给我。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