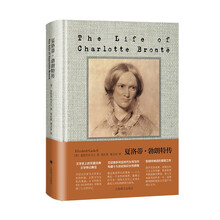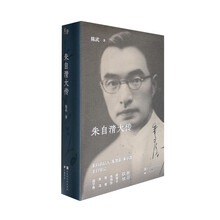“我可以爱!”
日夜思念着许广平的鲁迅,心潮起落,面临着种种抉择。
在事业上,鲁迅对此后的方针“很有些徘徊不决”。是专事写作,还是一心教书?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这两件事,颇有些势不两立。倘兼做两样,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结果是两面都不讨好。所以,他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自己想,我如写点东西,也许于中国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1]
在爱情方面,鲁迅虽倾心于许广平,但也并非毫无顾忌。他说:我的“这些顾忌,大部分自然是为生活,几分也为地位,所谓地位者,就是指我历来的一点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为的剧变而失去力量”[2]。为此,鲁迅颇关注社会的舆论。与此同时,鲁迅还有一种顾忌,就是他与许广平的相爱,是否是将许广平当作“牺牲”?一旦这种心绪在心头泛起,他就沉闷不语,犹豫不决。思念恋人的鲁迅急于奔赴广州,往中山大学任教,与许广平团聚。但恰在此时,许广平因与学校右派学生关系紧张,欲往汕头任教。她在1926年11月7日的信中说:届时“如汕头还缺教员,便赴汕头”。鲁迅收到这信时,顿觉当头泼来一瓢冷水,感情上也似乎掀起了难以平息的风波。因此,在思虑了几天之后才写了复信。信中不无惆怅地说:“我的一个朋友或者将往汕头,则我虽至广州,又与在厦门何异。”所以,“我的行止,一时也还不能决定。”
中山大学
离他而去?
有鉴于此,对于此后所走的人生道路,鲁迅也有种种思虑。他在1926年11月15日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借自己的升沉,看看人们的嘴脸的变化,虽然很有益,也有趣,但我的涵养工夫太浅了,有时总还不免有些激愤,因此又常迟疑于此后所走的路:(一)死了心,积几文钱,将来什么事都不做,顾自己苦苦过活;(二)再不顾自己,为人们做些事,将来饿肚也不妨,也一任别人唾骂;(三)再做一些事,倘连所谓“同人”也都从背后枪击我了,为生存和报复起见,我便什么事都敢做,但不愿失了我的朋友。第二条我已行过两年了,终于觉得太傻。前一条当先托庇子资本家,恐怕熬不住。末一条则颇险,也无把握(于生活),而且又略有所不忍。所以实在难于下一决心,我也就想写信和我的朋友商议,给我一条光。[1]
中年人的婚变,往往顾忌多端。尤其是像鲁迅这样的名人和伟人,产生诸多顾忌,实属必然。他不能不考虑谣言的中伤。在北京时,有客人来访,他请他们在客室小坐,因为没有让到卧室,他们便不高兴,说他是“金屋藏娇”。他和许广平南下,人们便放出流言说:“鲁迅是把许广平带到厦门去了。”鲁迅在厦大辞职欲往广州,厦大又有教员说:“这是因为‘月亮’不在厦门之故。”而高长虹的先利用,后攻击,尤使鲁迅愤激而悲哀。诸如此类的流言和攻击,是否会影响他在文坛的地位?他不能不加以思索。鲁迅也不能不考虑他和一位比他小18岁的年轻姑娘结合,是否是把对方当作“牺牲”,特别是他欲往广州,许广平反而想到汕头工作时,他的心中便不能平静,甚至生出某些疑虑和奇想来。在北京时,鲁迅为购置八道湾和西三条的住所,大量投资,致使债台高筑;现在,一面要创造新的生活,一面又要供养母亲和朱安,经济上压力甚大,此后的生活又怎样安排?这真是“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诸多困难,使鲁迅不得不一吐苦衷,和许广平商量,但是,爱火燃烧,又使鲁迅坚决地表示,无论如何,“不愿失了我的朋友”。
许广平真不愧为伟大的女性,在这关键的时刻,她以无限真挚的爱情,温暖着鲁迅的心,给鲁迅以勇敢和力量。她在1926年l1月16日写给鲁迅的信中说:“几个人乘你遁迹荒岛而枪击你,你就因此气短么?你就不看全般,甘为几个人所左右么?我好久有一番话,要和你见面商量,我觉得坦途在前,人又何必因了一点小障碍而不走路呢?……况且你敢说天下就没有一个人是你的永久的同道么?有一个人,你就可以自慰了,可以由一个人而推及二三以至无穷了,那你又何必悲哀呢?”[1]在《两地书》原信中,许广平还针对着他们为创造新的生活一事,特别为鲁迅分忧解难。她说:“你要做的事,不必有金钱才达目的的,措置得法,一边做事一边还可以设法筹款的。”[2]
针对鲁迅常常想到自己是将许广平作“牺牲”因而不免自愧,感到对不起人,许广平则在信中指出:“你‘向来常常想到的思想’,实在谬误,‘将人当作牺牲’一语,万分不通。牺牲者,谓我们以牛羊作祭品,在牛羊本身,是并非自愿的,故由它们一面看来,实为不合。而‘人’则不如此,天下断没有人而肯任人宰割者。倘非宰割,则一面出之维护,一面出之自主,即有所失,亦无牺牲之可言。”[3]而且,在《两地书》原信中,许广平还有更为直率的表示:“那一个人(即指她自己—着者按)也不是定专为别人牺牲,实在不如此自己不好过,这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4]也就是说,这是爱情,是爱的奉献,只有如此,才是心之所安。
关于未来生活的道路,鲁迅有三种设想,并要许广平给“一条光”。许广平也坦诚地指出:“你的苦痛,是在为旧社会而牺牲了自己。旧社会留给你苦痛的遗产(即指朱安),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有时也想另谋生活,苦苦做工,但又怕这生活还要遭人打击,所以更无办法,‘积几文钱,将来什么事都不做,苦苦过活’,就是你防御打击的手段,然而这第一法,就是目下在厦门也已经耐不住了。第二法是在北京试行了好几年的傻事,现在当然可以不提。只有第三法还是疑问,‘为生存和报复起见,便什么事都敢做,但不愿……’这一层你也知道危险,于生活无把握,而且又是老脾气,生怕对不起人。总之,第二法是不顾生活,专戕自身,不必说了,第一第三俱想生活,一是先谋后享,三是且谋且享。一知其苦,三觉其危。但我们也是人,谁也没有逼我们独来吃苦的权利,我们也没有必须受苦的义务的,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就是了。”[1]在《两地书》原信中,许广平还更进一步写道:我们是人,天没有硬派我们履险的权力,我们有坦途有正道为什么不走,我们何苦因了旧社会而为一人牺牲几个,或牵连至多数人,我们打破两面委屈忍苦的态度,如果对于那一个人(指朱安—着者按)的生活能维持,对于自己的生活比较站得稳不受别人借口攻击,对于另一方,我的局面,双方都不因此牵及生活,累及永久立足点,则等于面面都不因此难题而失了生活。对于遗产抛弃,在旧人或批评不对,但在新的,合理的一方或不能加任何无理批评,即批评也比较易立足,则生活不受困,人人可出来谋生,不须“将来什么都不做”,简直可以现时大家做,大家享受,省得先积钱,后苦苦过活,且无把握,但这样对遗产自不免抛荒,而事实上,遗产有相当待遇即无问题,因一点遗产而牵动到管理人行动不得自由,这是在新的状况下所不许,……在新的生活上,没有不能吃苦的。至于做新的生活的那一个人(指许广平自己—着者按),照新的办法行了,……而且那么办立时什么都可以做,不必候在民国十七年……[1]
许广平的直率和果决,给鲁迅以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几乎将鲁迅心中的迟疑和顾忌一扫而空。说到许广平欲往汕头的想法,那也不过是一时之念,并不是已成之事实。为了彻底消除鲁迅的疑虑和不安,许广平在信中说:“汕头我没有答应去,决意下学期仍在广州。”又说:你“单独为‘玉成’他人而自放于孤岛是应当的吗?我心甚乱,措辞多不达意,又恐所说令你生新的怪异感想,不写几个字,又怕在等看信,我觉得书信的传递实在讨厌,费时而不能达意于万一”。[1]鲁迅接信后,这才高兴地说:“无论如何,我还是到中大去。”又说:“总之我以前的办法,已是不妥,在厦大就行不通,所以我也决计不再敷衍了,第一步我一定于年底离开此地,就中大教授职。
但我极希望那一个人也在同地,至少也可以时常谈谈,鼓励我再做有益于人的工作。”[2]
鲁迅的爱情之火在熊熊燃烧,许广平的爱情之火也同样在燃烧。这纯净的火焰,将最终融化一切,将结束他们两地相思的生活局面。如果说,当鲁迅和许广平离京南下时,他为了经济、为了舆论、为了“遗产”、为了种种顾忌,曾与许广平谈妥在民国17年,也就是1928年再创建他们的新生活,那么,至少在1926年底,他们开拓新生活、创立新的家庭的时限已决定提前了,鲁迅也不再为了经济、舆论和“遗产”而迟疑观望了,他的种种顾忌,都为许广平的爱融化了。到这时,鲁迅的心情骤然变得如晴空一般,万里无云,他尽管穷得一贫如洗,但却充实得像个腰缠万贯的富翁,他的行动也不再有任何迟疑,恰恰相反,倒像是一个坚决冲锋的士兵。他反过来称赞许广平,说“HM比我有决断”,并检讨自己的“脾气实在坏”。他先前曾顾忌舆论,怕累及自己在文坛的地位,现在则一变而为蔑视舆论,相信自己,已不再顾忌因为和许广平结合而影响他作品的力量。他说“以中国人的脾气而论,倒后的着作,是没有人看的”,但“只要作品好,大概十年或数十年后,便又有人看了”。[1]恶意的中伤,想把他和许广平分离,他却偏要和许广平同在中大任教,并说:“我想同在一校无妨,偏要同在一校,管他妈的。”[2]在回顾自己的生活时,他又坦率地作了自我批评:“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历来并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因为那时预计是生活不久的,后来预计并不确中,仍须生活下去,于是遂弊病百出,十分无聊。后来思想改变了,而仍是多所顾忌……,但这些瞻前顾后,其实也是很可笑的,这样下去,更将不能动弹。”[3]
不仅如此,鲁迅在1927年1月11日致许广平的信中,又以其富有哲理性的独特语言,再一次地表白了对许广平的热烈的爱。他说:我对于“来者”,先是抱着博施于众的心情,但现在我不,独于其一(即指许广平—着者按),抱了独自求得的心情了。这即使是对头,是敌手,是枭蛇鬼怪,我都不问;要推我下来,我即甘心跌下来,我何尝高兴站在台上?我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对于这样的,我就叫做“朋友”。……我牺牲得不少了,而享受者还不够,必要我奉献全部的性命。我现在不肯了,我爱对头,我反抗他们。[1]鲁迅也已经深深懂得,恶意中伤、流言蜚语是必然会有的,除非他和女人不见面,不讲话。如果自己只是一味隐忍、退让,他们便得寸进尺,永不完结。为此,他蔑视他们了。他对许广平说:“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2]
“我可以爱!”是鲁迅战胜了社会舆论,清除了心理暗影,消除了对许广平想赴汕头任教的误会之后,发自内心的爱的宣言。他以骄傲、自豪和满足的心情对许广平表示:“置首于一人之足下,甘心什倍于戴王冠,久矣夫,已非一日矣……”[3]
大半生没有享受过爱情幸福的鲁迅,如今已完全陶醉在爱情的幸福之中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