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格拉克(Julien Gracq,1910-2007),法国20世纪著名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少年时曾就读于著名的贵族学校亨利四世中学,后进入以培养精英而著称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主修历史与地理。年轻时,格拉克深受超现实主义影响,所著的《安德烈?布勒东》一书一直是研究超现实主义的重要专论。可是他本人并不想归属于任何文学流派,而是匠心独运,自成风格。1938年发表处女作《阿尔戈古堡》。1951年写的《沙岸风云》获得龚古尔文学奖,被评论界誉为战后法国文坛的一朵奇葩。但格拉克认为,文学活动与社交和功利毫无关系,因此他拒绝领奖。除了长篇小说,格拉克还娴熟地运用多种文学体裁进行创作,著有散文诗《巨大的自由》(1947),剧作《渔夫国王》(1948),随笔《首字花饰》(1967)和《边读边写》(1981)等。格拉克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和独立傲世的人格使他在法国文坛享有极高的地位。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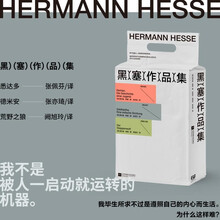







——廖星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