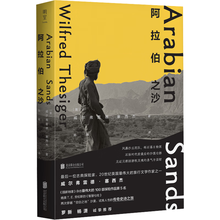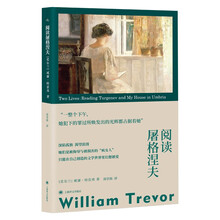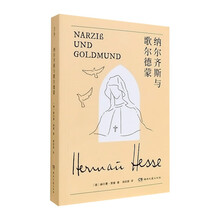《阿兰》:
如果您打开了这本书,那是因为您对阿兰·罗伯一格里耶或多或少感兴趣;如果您在这一篇文章中停下来,那您就是对他特别感兴趣。因此,在继续阅读这一章之前,请先阅读《假阳具》以及《合同》。
从这些阅读中能够得出,某件尚未言明的事情在缓缓地让我们的情色一性关系变坏,甚至本应让这关系完全停滞:鉴于我与现实的妥协能力是与生俱来的,这不会成为什么大事件:我的丈夫是不是有一种变幻不定的男性能力呢?这没什么大不了,我不至于在必要的程度外还为此困扰自我。因为他准许而并没有诱使我,去找一些旧日情人,我从来没有理由向他隐瞒,而且我乐于向他讲述我的遭遇,开心的或不开心的:“讲述”的习惯并不是出于协定——不隐藏任何东西——而是出于纯粹的向密友吐露心声的兴致。我的丈夫是我当时最好的朋友,我向他讲述我的小艳遇,因为这些都让他开心,他的兴致如此高以至于他会毫不犹豫地教导我,当他为我的情人们(及女情人们)设身着想时,他评价我对受伤的心缺乏柔情。而这不无道理:在婚外的活动中(从短暂的晚会到考究的扮演),创意总是出自我。总是。
——可您的丈夫,在这当中,他不仅仅是您的密友啊!
——当然,不过,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如果我们不考虑他与茹尔当的私情的话(见《阿司匹林》),阿兰不会“到别处去看”,不会脱离夫妻关系(conjugo),并且他寻求满足自己的欲望,常常与我分享我的一位或数位作风自由的朋友,她们准备好服从他的怪异要求,而且无望地期待着这件事情能往更传统的方向转变,又或者,他将我,他的妻子,他珍重的物品,在庄严的姿态中送到他的密友的抚摸之下,又或许,与一位年轻的施虐者共同享有我(我会再说到这一点)。滥交主义所倡行的无节制的身体交叠是——自不待言——绝对被排除在他的色情活动之外的。
对,阿兰不仅仅是我的密友。当我说他的男性能力变幻莫测时,我并不是说它消失了,而只是无法预测;我们婚后一年,在凯朗果夫街的家里,他的奶奶过世的那晚,他才断除了性无能的魔咒(对心理分析师来说,这又是一个难以决断的个案)。他并没有在厄运最终破灭后,就因此回到他并不期待的正常的道上。谁要是以我们交合的次数评价我们的性生活,将会发现它确实可怜!幸亏性生活的乐趣并不在那而在别处,在鲜有参与的高贵层面,痛苦和羞辱才是乐趣和爱情的源头。
对于普罗大众,鞭子是象征这一怪异的偏离的工具。我已经说过,我们并不为器具而着迷,使用器具的方式必然比它们的数量和种类更加重要:是思想让物质活跃而不是相反。
我们的第一条鞭子,叫作“丈夫鞭”,是在一家狗用具商店里买的,它的柔韧性极好,我在婚前将它送给了阿兰。第二条,是一位慷慨的朋友送我的礼物,出自一家鞍具制造商(爱马仕)。最后一条是黑色宽边皮带,配有银环的象牙手柄——象牙在当时可以买卖——是一位工匠从阿根廷的放牛人的皮鞭中汲取灵感而制成的。
在器具的组合中有一条马鞭,是阿兰数小时驯马体验的纪念品,还有使用舒适的小链条和一些狗链子,有一段时期,我还戴过其中一条优雅而隐秘的短小的链子,在一个美好的早晨,一位女发型师说道:“您钟爱的小母狗走丢了吗?”我没有勇气对她说,那只受宠爱的小母狗,就是我。这一条我(如此)珍重的细链被一个偷窃癖者盗走了。
在许多的年月里,我都是在皮鞭之下,后来,在一位以萨德为榜样,喜爱调换角色的年轻施虐者的逐渐引导下,我就将皮鞭的手柄决然地拿在了手里。
——那您的丈夫曾臣服于您吗?
某些记者这样写了,是为了让他在常人眼里显得可笑,而常人又是易于讥笑任何服从的男人的。阿兰从未想过要到镜子的另一头去,即便这也不会有任何不适。他对自己有限的品位而假装遗憾,根据他的定义,“萨德式一色情”应该由异质来补充完整:“萨德式一异质一色情”。这一特点一下子就将他挡在了我的仪式之外,而常常,几乎总是,有一些男信徒参与我的仪式(阿兰并不敌视他们,不过对他们没有任何兴致),不过这都不妨碍他让我讲述,详细与否,视其心情而定,甚至是在他“回缩”到他的幻想孤独之后……
“合同”已经言明:他的幻想排他性在于萨德式地控制(非常)年轻的女子,在缺少女孩的情况下。他自己也笑着重述了一句路易斯·卡罗尔的话:“我非常喜欢小孩,不过,小男孩除外。”他曾寄给我的一些图画是一目了然的:漂亮的女孩被绑起,血迹斑斑……我不相信他的幻想曾有过动摇,从童年到老年,即便它在他的作品中变得越来越明显,直到烟花的“最后绽放”,《情感小说》,过分的,唯一的文本,在一切约束之外:临床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