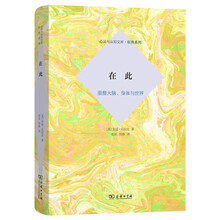大异于儒家士人的在民而不自视为民、不安于在民并总是希望有朝一日重返庙堂而为天下所用或者用天下,庄子却能以释然欣然之心态逍遥安处于民间社会。而庄子之追求其自身的“无用”,以及不愿成为棱牛而“入于大庙”,一方面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保全性命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更是为了从己身上消除所有可能被君王罗致笼中的潜在的工具性因素,以一种与当政者绝对不合作的姿态,保持其非政治化的民间生存方式。纵然这种自我边缘化的生存方式常常伴随着贫困和苦难,但对于庄子而言,个体在世的终极依据和价值惟需至上之道而完全不需要通过政治活动来确证,因此只要载道于心,何妨以此游身于人间世?从这个意义上说,庄子通过“自埋”“自藏”、“陆沈”于民,真正挺立了独立卓异的个体人格。<br> 仍需强调的是,即使庄子已属“四民”阶层,且对底层民众怀有深切的哀怜和同情,我们也不应把庄子思想定位为民众意识的代表或处于无声状态的劳力者所发出的声音,其“逍遥游”也更不应被理解为底层民众所渴望的生存方式。换言之,“逍遥游”这种生存方式归根结底仍属于“士”而非“民”的生命哲学。而庄子之所以选择驻身栖心于民间,实质上是为了永远避离污浊的政治场域,宁愿食其自力(例如织屦)也不食君之禄,宁愿在底层辗转挣扎也不希求显耀于庙堂——并且民间生活原本另有一番乐趣在内,从而坚守一种由外而内彻底非政治化的个体生命理想。因此,所谓民间化和非政治化本为二而一的两个方面:前者是形式,属于“民”的范畴;后者是实质,属于“士”的范畴。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