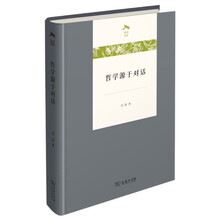社会科学在启蒙运动中诞生
毋庸赘言,18世纪使“科学”享有极大的荣耀。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里写道:“哲学精神现在也就是观察和精细的精神。”观察、实验、分析;基于细致的研究制定清晰严格的一般法则——这是确实可靠的方法,是笛卡儿和牛顿的产物,现在被认为臻于完善。因此所《拉瓦锡与夫人》,雅克·路易·大卫绘,1788年拉瓦锡在夫人的帮助下,在巴黎兵工厂建立了一间精巧的化学实验室,在此他进行了各种实验,为他宣布实现化学革命奠定了基础。
需要做得的仅仅是把这种方法应用到依然被迷信和混乱所困扰的各个领域。培尔的思想代表这个世纪的精神——“错误并不因为其古老就好些”;让我们用有效的脑力劳动来清除过去的一切马虎和轻信。这也是亚历山大·蒲柏在著名诗句“人类的正当研究对象是人”中所表达的意思。
在这个世纪里,自然和物理领域里的新进展鼓舞了人们对科学进步的信念。到该世纪中期,电成为大众的玩具,专家和业余爱好者都喜欢演示这种神秘力量。1746年,穆申布鲁克穆申布鲁克(Pieter van Musschenbroek,1692—1761年),荷兰实验科学家。发明了莱顿瓶(电瓶);1752年,美洲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进行了著名的实验,证明闪电就是电。到该世纪末,亚历山德罗·伏打发现了把电能储存在一种简单电瓶中的方法,人们制造出最初的蒸汽机和简陋的火车,在大批人群的围观下乘气球上天(1783年在巴黎)——“工业革命”开始了。凯伊、克隆普顿、阿克赖特、纽可门和瓦特使英国进入了一个机器技术的时代。其后果到19世纪初才显露出来。汽车、铁路、飞机、电报和机械化工厂的萌芽在18世纪已经隐约可见——仅仅隐约可见,但足以暗示技术无限进步的诱人前景。在理论方面,达朗贝尔、拉格朗日和世纪末叶的拉普拉斯等数学家改进和完善了牛顿力学。在其他科学领域,布丰描述了各种生物形态,瑞典的林奈对生物进行了分类,莫佩尔蒂和狄德罗对生物的起源做了推测,多少预示了19世纪的进化理论。化学不甘落后,开始反叛亚里士多德,并且在18世纪大约从施塔尔(1717年)到拉瓦锡(1783年)施塔尔 (Georg Ernst Stahl, 1659/60—1734年),德国化学家和医生,提出燃素说。拉瓦锡(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 1743—1794年),法国化学家,用氧气学说推翻燃素说。逐渐形成一门现代科学。
不过,启蒙运动期间,占据舞台中心的是对人的研究。在C.E.雷文(《自然宗教和基督教神学》,1953年)看来,科学在18世纪可能遭受了一次“突然的日全食”。与17世纪相比,真正伟大的科学家确实寥寥无几。——原注这里是令人振奋的前线,在这里人们能够把当时对人本身的强烈兴趣与同样受到尊重的牛顿和洛克的科学方法结合起来。今天,我们往往着重看18世纪社会科学的缺陷,即过分的简单化和过分的乐观主义。错误似乎就出在要把人文简化成物理,把人和社会说成牛顿式机器。但是,不能否认,18世纪奠定了各门社会科学的基础。经济学、社会学、历史研究、政治科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后来在现代世界得到了发展。它们都脱胎于启蒙运动,它们的创始人是当时那些全能的启蒙者,如休谟、伏尔泰、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所写成的法国启蒙运动的经典著作之一是他对政治科学的开创性贡献,这在前面已经谈过。在18世纪60和70年代,人们的兴趣开始集中在经济学家身上。他们在法国被称作“重农学派”。(Physiocracy的意思是由大自然进行统治。)
经济学
18世纪经济理论的背后隐含着当时人们的某种伦理关怀和问题。现代经济学家非常讲究“科学性”,他们会很惊讶地得知他们这门学问最初是道德研究的一个分支,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18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是道德哲学教授。他在写出不朽的《国富论》(1776年)以前写过一部论述道德情感的著作(1759年)。爱尔维修的《论精神》对重农学派产生深刻影响。这部著作在1759年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它公然鲜明地支持享乐主义伦理——带来快乐即为善,造成痛苦即为恶。沙夫茨伯里伯爵、弗朗西斯·哈奇森(亚当·斯密的导师)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1694—1746年),苏格兰道德哲学家、美学理论家。和休谟都以比较温和的方式论证类似的主张。对于经济科学来说,这个主张的意义在于,经济学把永远追求个人幸福最大化的“经济人”作为自己的基本假设。第一位重农主义者魁奈在其开创性作品《经济表》(1758年)中开门见山地宣布:“用最小的公共代价获取最大量的快乐,乃是最完美的经济行为。”没有这种“经济人”,也就不可能建立一门经济科学。“经济人”相信现世幸福就是人生目的,因此他们要以系统的、有预见性的方式来为之奋斗。现代意义上的经济科学的一个前提,显然就是对这一享乐主义伦理的普遍接受。这对于今天的人们似乎已司空见惯,但是启蒙思想家对“追求幸福”的重视则反映了某种新的倾向。古希腊人重智慧轻幸福、古罗马人重权力,中世纪人推崇圣洁;加尔文和新教徒尽管据说是带来了“资本主义伦理”的某些因素(勤劳、节俭、节制),但无意把现世成功作为终极理想。
现代经济学的另一个前提是经济个人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学者和信奉者想当然地认为,不受任何团体支配的自立自强的个人,乃是最典型的社会单元。社会和思想的进化在很多方面都为此做了准备。霍布斯、洛克和卢梭帮助这些独立的个人走到一起创立政府。在新的经济思想中另一种现在人所熟知的因素是社会和谐观,即认为个人活动的总和可能产生社会和谐。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经济人——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每一个人都不断尽力去为自己所能控制的资本谋求最有利的使用”——用什么能够防止出现那种意愿相互冲突的混乱局面?或者说,救治社会无政府状况的良方是什么?斯密指出,幸好上天凭借一只“看不见的手”,确保在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时社会整体随之受益。《国富论》的一些部分接受了曼德维尔提出的著名观点——“私人恶德乃是公共美德”。人们追逐财富,贪求奢糜,反而给穷人提供了工作,给国家带来了财富。这种社会和谐观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得自于牛顿的宇宙比喻:所有的质点都在运动,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宏大体系。
在重农学派和斯密之前,人们对经济问题也有许多思考。孟德斯鸠1748年就已经提出了建立一门研究社会现象的一般科学的概念。所有的法国重农主义者都承认从《论法的精神》中受益匪浅。甚至自博丹那时起,除了大量探讨具体问题的务实文章外,也有一股严肃的经济理论思考的潜流在涌动着。洛克本人以及与他同时代的达德利·诺思都提出了重要的思想。在法国,坎特龙坎特龙(Richard Cantillon,·—1734年),英国经济学家,长期住在法国。的《论商业的性质》在18世纪初期就以手抄本形式流传(直到1755年才付印出版),梅隆梅隆(Jean Franois Melon,1675·—1738年),法国经济学家。1734年发表的《关于商业的政治论》也是对“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攻击。
这里应该谈谈这些被称作“重商主义”的早期经济学思想。思考经济问题,并不新鲜。在亚当·斯密之后,人们往往把斯密之前的一切思考都斥为即兴遐想和不着边际——思维简单,支离破碎,错误百出。对于从16世纪晚期到18世纪初期的这些早期经济论著,人们夸张地使用了“重商主义”这个词——这个词是后来的发明,旨在对各种现象进行分类,有些像现代历史学家把“封建主义”套用在中世纪的政治秩序上。最近一些研究者怀疑这个术语是否够用,怀疑对这批文献的贬低(把它们说成至多具有历史价值)是否公平。重商主义据说是一种用显而易见的方式来增强经济实力的纲领。它着眼于商业,其判断通常是管窥蠡测、浅见薄识。但是,尽管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及其之后的一些人)相比,这些思想散乱而不系统,但是这些开拓性思想为后来的大综合做了准备,而且最先提出假设:人能够有意识地指导自己的行动去增加财富。17世纪,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就试图把笛卡儿的数学分析方法应用于经济现象。一般而言,与后来更辉煌的重农主义者相比,重商主义者对用计划来改善经济的可能性怀有更大的信心,也更乐观。但是他们也看到有时“法则”会压倒统治者的意志,因此他们建议明智的政治家应该顺应“自然”,而不要对抗自然。
无论他们有多少可取之处,早期经济学者到了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的时代就逐渐衰落式微。人们指责重商主义者提倡干涉“贸易自由”,违背了自然法则。旧的经济秩序,无论是否得到所有的“重商主义”理论家的认同,本身是管制性和歧视性的。它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进口商品与本国产品竞争显然是坏事,因为这样会使本国的手工业者失业,因此必须加以限制乃至禁止。金银流失也被视为坏事,而赢得贵金属则是好事。“良好”的贸易享受补贴的鼓励;出口本国产品来换取外国的原料就属于这种贸易。关税、禁令、补贴都被用来确保实现“贸易顺差”和保护国内制造业。此外,国家有时还试图控制工资和物价。
这种“体制”很容易导致腐败,因此在1750年以前就零零散散地出现了一些抨击,有人还建议最好用“贸易自由”来取代这种臃肿的特权体系。大卫·休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性批判。他指出,贸易顺差是一个幻想,从长远看,经济法则总是在打破这种幻想。顺差带来了硬币,从而引起物价上涨,结果是出口下降。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贸易是逆差,物价就会下落,就将赢得市场。因此,最终总会实现一种平衡。(法国的先驱者坎特龙大约在同时也提出了基本相同的观点。)与自己的朋友和苏格兰同胞亚当·斯密相比,休谟的经济思想既不全面也不系统,但是为亚当·斯密的思考做了铺垫。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