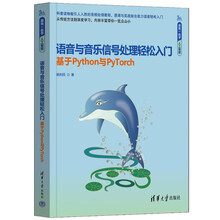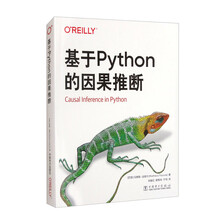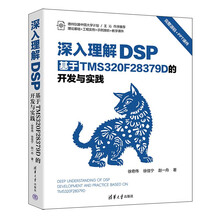第一节
1
尽管医生的办公室很暖和,我却感到了刺骨的寒意。我是个加州女孩,今年19岁,第一次在密歇根大学过冬。在这儿,寒意似乎无处不在,让人挥之不去。在去医学院的路上,我的头发和衣服上都积了厚厚一层雪。尽管头发和衣服早就干了,但我还是能感觉到从脚底传来的阵阵寒意,这让我的腿生疼生疼的,走起路来拐得也更厉害了。
医生的办公室既简朴又敞亮。我坐下来,漫无目的地四下看了看,然后把腿盘起来,心不在焉地搓着脚踝,想着自己过去进过多少个类似的房间。先是长达几天的检查和等待,然后是更多的检查,更多的等待。这次我来是因为耳鸣。刺耳的噪音已经持续好几周了,就像我被丢在了你能想到的最吵的摇滚音乐会上似的。有时它会盖过其他声音,有时它则像背景音乐一样。这让我夜不能寐,简直要抓狂了。我知道这种症状叫什么——耳鸣(tinnitus),这个拉丁词的本意是“鸣响”——但这根本无法描述我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声音既像是外面传来的,也像是我脑子里发出的。它震荡着我的鼓膜,声音是那么响亮,我简直不敢相信别人竟然听不到!别人对我说话的时候,无论周围有多安静,我都需要他们提高音量,要不就索性趴在我耳朵边上说。这就像是消防车呼啸而过的时候,你得大声说话,对方才能听见。求求你放过我吧,我不断这么想。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声音不但不会离开,还会和我长期相伴。很快,我就学会了和它共处。这种声音是如此熟悉,以至于我很难意识到自己有耳鸣。
门开了,一位40来岁的大夫走进来,后面跟着几个局促不安的实习医生。他们在旁边挤来挤去,争夺观察病人的最佳位置。大夫开门见山地问我,可不可以让这些实习医生观摩诊断过程。我点了点头,冲他们笑了笑,但其实我心情很糟,因为我看得出来,自己的情况不太妙,医生会向他们展示任何人都不想听到的诊断。他们都躲避我的目光,低头假装忙着看笔记。他们还没有掌握医生式的笑容,就是那种医生始终挂在脸上的,即使面对坏消息也不会消失的笑容。
尽管我直到12岁才意识到自己有问题,但其实问题早就存在了,只不过最初的征兆太不明显,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罢了。我家里一直很热闹,附近所有的小孩都喜欢来我家玩,所以屋里总是充满了笑声、音乐声和争吵声。我和弟弟们都很好动,打架时不管不顾,总是边追边打。朋友来玩的时候,我们动不动就尖叫,或是蜷在睡袋里从长长的楼梯上滚下去,或是满屋子疯跑。这一切都掩饰了我笨拙的举止——我总是被东西绊倒,撞到东西上,或是弄伤自己。作为家里3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孩,我决定要像弟弟们一样坚强。虽然丹尼尔和我是双胞胎,彼得才3岁,我却总觉得自己才像家里最小的那个。丹尼尔既聪明又帅气,还很擅长运动,在各个方面都是超级明星。我决心要赶上他。
跳芭蕾的时候,我也是最笨拙的那个。我动作不协调,毫无平衡能力。我不停地抹平粉色紧身衣上的皱褶,想要变得更优雅。但无论我多努力,都没法保持平衡,维持某个姿势,也没法像其他女孩一样轻盈起舞。我那严厉又死板的教练总是大喊“丽贝卡”,所以我开始逃课了。我会躲进更衣室里偷吃饼干,免得再丢人现眼。
还有其他的一些迹象,比如我侧着头看电视的样子。我会用左耳对着电视,从眼角斜着看。我还经常走神,尤其是坐在教室后面的时候。老师管我叫“梦想家”,连我都知道这 是在说我“注意力不集中”。但没有一件事严重到能引起我那忙碌而喧闹的家人们注意。
不过,只追溯到我的童年还远远不够。没有人能想象得到,早在丹尼尔和我这对龙凤胎在母亲肚子里抱成一团的时候,悲剧和喜剧就分别在我俩身上埋下了种子。再往前,就要追溯到东欧,或许是基辅,也就是我父母的祖先生活过的地方。在无数场战乱过后,东欧人口锐减,出现了近亲通婚。就这样,一个突变的基因悄悄留在了我的身体里,无人知晓,直到我12岁开始看不清黑板的时候。
尽管我家里很闹腾,很少有清静的时候,但我常常快乐地回忆起儿时的喧闹,回忆起那些嬉笑、聊天和没完没了的歌唱。我们几个孩子都努力显得比其他人聪明,因为我们知道这样会让爸爸妈妈开心。于是,我们家里总是充斥着俏皮的笑话和机智的反驳。我妈妈过去是个专业歌手,我们常常在她弹钢琴的时候围在旁边夸张地大声歌唱,假装是在百老汇演出,直到她站起身来,领着我们边唱边跳地上楼做作业去。那个时候,我一点也不喜欢安静的地方,独自一人的时候会浑身不舒服。只有打开电视或放上音乐,弄出点声响,我才会觉得开心,感到放松。现在则截然相反,安静的地方反倒成了我的救赎。
到我10岁的时候,一切都变了。那时,距离家人注意到我的视力问题还有好几年,家里出现了一种新的噪音。起初,那只是从牙缝间挤出来的不易察觉的低声抱怨。最后,父母之间的战争已经升级到了大吵大闹。我和兄弟们不得不冲过去劝架,求他们不要再吵了,或是做一些让他们开心的事,只要他们不继续吵架就行。等他们注意到我有点不对劲的时候,我的父母已经分居,陷入了“看看这样能不能解决问题”的僵局。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么做起不了任何作用。
我告诉爸爸自己看不清黑板以后,他觉得我可能需要配眼镜,所以带我去验了个光。在检查过程中,医生总是皱着眉。这么多年以来,我对这种表情的含义已经了然于胸。检查完毕后,他告诉爸爸,我眼球后面似乎有些东西,需要进行更全面的检查,但他这里设备不足,他也无法做出专业评估。于是,我们去找了眼科医生,后来又找了一位接一位的眼科专家。我们去了加州大学、旧金山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去请教那里的专家。视力表换成了越来越复杂的设备和测试,其中一个测试需要我戴上硬邦邦的镜片,上面有几根线接在我的眼球上,还有一个测试需要我尽可能久地盯住亮光,不许眨眼。我一直很纳闷,配个眼镜要这么麻烦?
每一次,我都等着医生面带微笑地走出来,冲我们点头致意,说他已经弄清了,没什么大碍,马上就能搞定。有一个测试我做过好几次,医生让我在看到小光点后揿下按钮。有时候我明明什么也没看到,却揿了按钮,因为我希望让每个人都满意。我想在测试里表现出色,让每个人都夸我做得好,戴一副可爱的眼镜回家,不用再惦记我的眼睛、父母的争吵和他们看我时那忧虑的眼神。我想考虑那些12岁的孩子应该考虑的事,和朋友一起出去玩,煲电话粥,讨论男生,聊有没有男孩子喜欢自己,聊在即将到来的中学舞会上要穿什么裙子。
最后,诊断结果出来了。医生告诉我父母,他们认为我得了“视网膜色素变性”,一种无法治愈的遗传病。我视网膜里的细胞正在慢慢死亡,他们预计我成人后很可能失明。我爸爸妈妈必须决定用什么样的方式告诉我这个消息。你会怎么告诉你的孩子呢?你能用什么样的话给一个小女孩解释这件事?我无法想象,当他们得知女儿在未来的某一天将再也无法看见父母和兄弟,再也无法看见整个世界的时候,内心是多么痛苦。
打一开始,妈妈就确信我应该得知真相,应该弄清自己的身体状况。她觉得,我知道的越多,越有利于在精神和身体两方面做好准备,直面未来。她坚持表示,如果我知道了真相,我就会理解,为什么很多事我做起来都那么难,我就会理解,看不见空中飞过的网球、跳舞时笨手笨脚、晚上去厕所时总会碰到东西并不是自己的错。她知道这是个挑战,但我别无选择,只能勇敢面对。她相信,即便我年纪很小,也应该了解真相。
我爸爸则表示激烈的反对。在他眼里,我还是他的小宝贝。他害怕让我听到那个他用“B打头的”来掩饰的词——“失明”(Blind)。他认为应该把消息一点一点透露给我,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去消化和接受。他让医院和抗盲基金会把资料寄到他的办公室,以免让我看到。起初,我只知道自己的视力越来越差,特别是晚上很难看见东西。我的视力和听力都是缓慢衰退的,没有对儿时的我造成很大的冲击。但我不确定,如果父母一开始就把真相告诉了我,我会不会理解。一个12岁的孩子怎么想象得出失明是什么样子呢?
回到我19岁那天,在密歇根那个温暖的办公室里。医生坐在我对面,把诊断书递给我,实习生们纷纷尴尬地避开眼神。医生没有转弯抹角,而是友善而直接地告诉我,我将来会失明,也会失聪。
他告诉我,这是一种遗传疾病。尽管根据我目前的症状还不能断定,但他怀疑我得的是乌瑟尔综合症。这种病的主要症状是听力和视力同时衰退,但他以前见过的病例年龄都比较小,主要是先天性耳聋或童年就出现类似症状的人。当时,这些细节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只记住了头一句话。那两个词仿佛给了我当头一棒——失明,失聪,失明,失聪——即使是耳鸣也不能淹没这个声音。我仍然努力保持微笑,在恰当的时候点头附和,努力做个合格的病人。
现在回想起来,我本不至于那么震惊的。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失明”或“失聪”了。我知道自己视力下降得越来越快,听力也越来越糟糕。或许是我过去一直没有做好获悉真相的准备吧。这是第一次有医生对我和盘托出,让我了解自己的状况。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这件事。我将来会失明,也会失聪,这病没法治,我永远也不会好了。
我努力提出一些问题,问他我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失明失聪会在什么时候到来。但我得到的回答全是微微摇头和“抱歉,我们也不清楚”。得到答复后,我微笑着向他表示感谢,然后站起身来。我镇定地站在那里,和其他医生道别,然后走了出去,努力不让自己显得软弱。我知道,他们肯定在背后对我的遭遇感慨不已。我离开医院,走进风雪中,但这次我丝毫没有意识到寒冷。
等我回到宿舍的时候,我已经很清楚自己听到这个消息后应该做什么了。那就是,什么也不做。我没有立刻通知父母,也没有去校园里找丹尼尔,更不想被一群朋友或爱慕者团团包围。我回到房间里,摘下帽子,放下长发,让它们遮住耳边的助听器。我知道,我带男生回家的时候还是会偷偷摘下它们,塞进床垫下面。我知道,我还是会尽一切努力,在不提及视力问题的情况下弥补糟糕的视力。有时候,我觉得这就像是命中注定的悲剧,和我12岁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同。要是我在视力测试中做得更好,或许我的父母就不会离婚,或许我就不会遭此厄运。或许,当我知道自己会失去什么以后,时光可以倒流,我可以不站在这里。当时,我觉得自己即将失去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