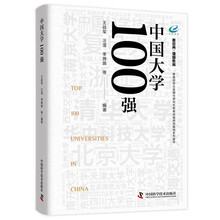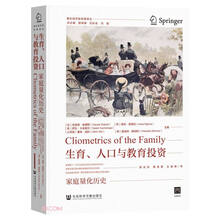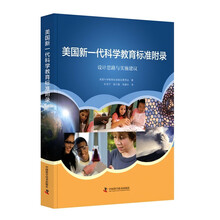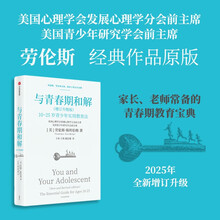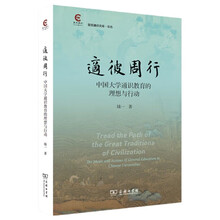1.教育主体
教育主体由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构成。叶澜先生在《教育概论》中提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承担的任务不同,但相对于教育活动的其他基本因素,他们都处于主体地位,也就是说,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是互为主客体,互为存在的关系,尽管二者承担的任务不同,但都是教育活动的承担者,都处于主体地位。因此,在“受孕”仪式里,存在三个教育主体:施戒者,受戒者,受戒者父母。
在“受孕”仪式过程中,受戒者的父母从吉日的选择,师傅的选择上都给孩子施加了一定的教育影响,所以,对于受戒者来说,父母是教育者;施戒者,在被选为师傅之后,对受戒者及其父母在行为和思想上也产生了一种约束,即在“度戒”期间,父母与子女必须分离,起居生活一切从简,受戒者在这段时间必须由施戒者“养育”,因此,施戒者是受戒者及其父母的教育者;范根内普认为,所有的过渡仪式都有三个阶段:分离,边缘(阈限)、聚合。分离意味着个人或团体离开了先前在社会结构中的固定位置或一套文化环境的象征性的行为组织;居中的边缘或阈限时期,仪式主体的状态模糊不清,他经过的是这样一个领域,很少带有或者不带有任何过去的或者即将到来的状态的特性,在第三个阶段中,通过过程完成之后,作为仪式主体的个人或团体再次处于稳定的状态,由此拥有了一些明确规定的和“结构”类型的权利和义务,被期望依照一定的习俗规范和道德标准来行事。可见,此时的受戒者属于该仪式的第一个阶段,正在和受戒前的生活分离,形同尚未出生的孩子,完全脱离了之前的生活,一切行为的习得都来自师傅和父母,所以受戒者在这一过程中属于受教育者,是学习过程的主体。
在《文化与承诺》中,米德将整个人类的文化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长辈向晚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后喻文化则是指未来重复过去。洞波的瑶族文化总体上看属于“后喻文化”,整个社会的变化十分迟缓微弱,长辈的过去就是每一新生世代的未来,他们已为新一代的生活奠定了根基。后喻文化是数千年前、甚至是野蛮时代人类社会的基本特质。由于没有书面和碑文记载,每一次变革都必须同化在人们的体验之中,并在每一世代的长者们的记忆和行为模式中加以贯彻。所有文化的连续性至少有赖于祖孙三代的存在。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