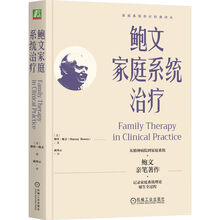我觉得好像买了一般读者不屑一顾的东西,类似萨德侯爵的性爱著作。可是,任何人瞥见医学书籍里恐怖的黑白照片就不会想到它是一本性爱书籍。我尴尬地僭越了应该是研究者和专业执业人士的保留地,我既不是研究者也不是医生,我似乎在篡夺一种权威,无形中破坏了某种医生和病人间不成文的、微妙的社会契约。
我实际上是个博士,但是博士头衔不能让我在医学领域获得任何资历。更糟糕的是,我也受到了社会对医学博士学位的敬畏以及人文领域博士学位边缘化的影响。虽然法国可能不一样,但在美国,哲学博士不具有医师特有的权力和权威。我从来没有搞清楚我的文学学位能有何用途,像我从前的许多同事那样在所有信纸上印上一英寸大小的字,或者把多年的分析训练作为实际收获,而不去考虑头衔。尤其我现在是“不工作”的母亲,第一个选择好像假模假式自命不凡,第二个选择似乎是我屈服于我始终抵制的一种文化倾向。每当一个医师或者家庭医生带着轻松口吻、父辈般熟悉的神情和我打招呼,“你好,凯瑟琳,我是琼斯医生”,我总是尴尬,无言以对。医学院的年轻学子到第三学年时大都具备这样的派头。
可是一旦破解这些环境里常用医学术语的实质,我确实渴望得到他们提供的东西:客观性、经验式探究。
那时,研究生学习法国文学和文艺批评,可悲地欣赏和沉溺于捉摸不定的知识。经过各种角度,如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现象学、女权主义批评、解构等游戏般地看待各种可爱的诗作和小说之后,我像只饥不择食的老鼠猛扑在医学上。我厌倦了真理的相对性,转变了视角和看问题的方法。我所需要的是派得上用场的信息和科学,通过经验数据验证的知识体系,而不是它的推行者是否有口才天赋;多些实在东西少些灵感发现,至少少些那些法国知识分子的灵感体验。我和一个朋友说起如何安排业余时间时,她回答我说:“知识就是力量。”她本人就是医师中间的少数派,似乎真诚欢迎外行人介入医学专业领域和提出自以为是的问题。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