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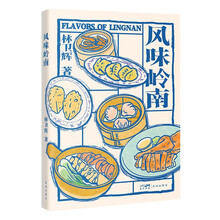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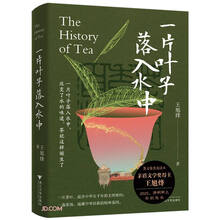





我吃东西向来不挑嘴,不过我承认自己还是有偏好的。例如,我觉得墨西哥瓦哈卡(Oaxaca)的烤蚱蜢就比盐腌的毛虫好吃(腌毛虫的味道颇似晒干的西红柿)。蚂蚁的味道苦苦的,可是蚁卵汤却很鲜美。还有,蒸鱼配上一种用曼答甲虫制的老挝酱,令我永生难忘,那雄甲虫的麝腺产生的香味像极了蓝霉乳酪。
读者放心,本书不会讲到吃虫子。多年下来,我倒觉得这个题目并不是多有趣。但是,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是虫子等奇特食材引我一头栽入直至现在仍未停止的一件事:借着吃来探索这个世界——文化、历史、感情。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台(NPR)的利亚纳•汉森(Liane Hansen)曾经说我是“美食写作界的印第安纳•琼斯”,我也要努力做到不浪得虚名。所以,读者会在书中看到我实地所做的食品及文化报道,而地点则出人意表——包括了泰国的一处榴梿农庄、智利外海的一艘渔船以及美国得克萨斯州达灵顿的州立监狱。
我从来都是借食物体验事情。我外祖母出生于斯洛伐克和波兰之间的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 Mountains)地区。她的英语说得 不错,但是挥洒糕点可比说起英语来得自在。她是慈爱的人,还要借烹饪表露这份慈爱。以前她来我们家做客的时候,我们给她预备一包25磅(11.5公斤)的面粉,她就把整个探亲假期耗在厨房里。我一放学回家就闻到阵阵东欧菜香。当晚晚餐就可吃到一块厚厚的“帕嘎奇”,即泡菜火腿馅的烤饼,另外还有刚出炉的甜味罂粟籽馅的酥皮卷当作饭后甜点。外婆从不和我们提她的故乡,我却觉得我们兄弟六个和那个老家亲近极了。
我母亲遗传了外婆表达亲情的手艺,也继承了外婆的全套东欧私房食谱。但是,我母亲是受美国同化的第二代移民,她并未受斯拉夫风味局限。她会剪下杂志上的美食新点子照着做,也会实验从小区左邻右舍打听来的家常菜单。鲔鱼锅面、美式蘑菇奶油汤以及葡萄酒烧牛肉、鸡肉扁豆糕、馕料猪肉等创意欧式美食,都是我们家餐桌上常有的(不过不及泡菜出现的频率高)。
我父亲从朝鲜战争中退伍时,我才2岁。他一退伍马上就投入餐饮业。在我成长的年代里,他一直在通用食品公司(General Foods Corporation)的餐馆和学校业务部工作,外食乃是他职务的一部分。如果他出差的时候带着我,我就跟着他到处下馆子。他本籍爱尔兰,家乡菜不外乎大块肉与马铃薯,但是他以多年与主厨共事所得的美食知识感到自豪。大约是我要进大学的那个时候,他顺理成章调入加洛兄弟(Gallo Brothers)酿酒厂工作。这家公司虽然不以高档酒品闻名于世,我父亲的职位却要求他恶补了一番葡萄栽培法和酿酒学的课程。每当我们父子对饮之时,他的品酒经总是滔滔不绝。
我从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下厨了。因为我是大哥,爸妈离家度周末的时候我就得扛起打理弟弟们晚餐的责任。这件事我做得兴趣盎然,不久就找出家里仅有的一本食谱来参考,并且试做自己发明的菜式。
我父亲嗜好打猎,冰箱冷库里经常有他猎来的鹿肉、雉鸡肉等野味。我母亲却不爱调理这些山珍野禽,所以就任它们冻在那儿,等到年度清仓的时候再把它们扔掉。后来我得知,野味是美食家最爱的珍馐,便征求母亲同意让我拿它们当烹饪食材。16岁那年我就试做了用菰米和野菇为填料的烤雉鸡(那天晚上我的弟弟们却叫了比萨外卖)。
那一阵子,每年秋季都有一个周末是我跟着父亲到缅因州的帕卡德狩猎营(Packard’s Hunting Camp)去猎鹿度过的。有一年在营中吃到了帕卡德太太的鹿肉糜馅饼,我就决定回家自己做做看。母亲食谱里的甜肉糜馅饼做法繁复,要用许多苹果和苹果酒。
那时候我刚考到驾照不久。我们家住在康涅狄格州,境内到处是苹果园和苹果酒作坊。新英格兰区各州的果农们谈起苹果种类、吃法、哪一家的苹果酒质量较佳,可以争上几个钟头。
这些评论我听得津津有味,所以光是采办肉糜饼的材料就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因为我开着母亲的旅行汽车跑遍了康州,到处试吃试喝,随时和苹果农聊天。这一趟苹果之旅比我后来做成功的肉糜馅饼可精彩多了。
我做的肉糜馅味道不赖,但是比大多数人吃惯的瓶装甜肉馅口味油腻多了。一般人连切下来一片的量都吃不完,更遑论在感恩节大餐或圣诞大餐之后当甜品吃。我调制了好几加仑的肉馅,结果只用了三只大饼的馅量,其余都进了冷库。以后我再没做过甜肉糜饼,但是一直未改到处找农民聊天试吃的习惯。
我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上大学期间,骑着摩托跑遍了那里风味特殊的餐馆、烧烤店、鲶鱼现捞现吃摊、墨西哥小吃摊。后来我休学跑到丹麦,骑着另一辆摩托车在丹麦的大陆区到处跑,寻找最典型的丹麦乡村小店佳肴。我交了几个丹麦女友,学会了用丹麦语品评黑麦面包、鲱鱼、丹麦火腿、丹麦乳酪。两年后,我重回学校,在得州大学修了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研究”的学士学位。
我是我父母两系亲族之中第一个念完大学的。当时我想以写作为业,家里人都认为这是胡闹。结果我刚出校门就进了一家广告公司,担任文字撰稿工作。几年后,我在康州哈特福德开起自己的一家小公司。那时与我共枕的女友是一位很漂亮的餐饮业人士,她的另一位共枕男友是外烩厨师戴维•格拉斯(David Glass)。某日,她因为把什么东西忘在格拉斯家里了,就拉着我一起去找。当时格拉斯不在家,他的厨房里却有几大锅小牛肉高汤,整个屋子里弥漫着巧克力的味道。
我和这位女友的交情不长,格拉斯亦然。但是我对格拉斯的厨房却念念不忘。和女友分手后,一次假日,我请格拉斯来为几位客户外烩晚餐。我们共拟菜单的期间,他教我学会从不一样的观点来思考饮食。
格拉斯那时候刚从巴黎学艺归国,他师承的是名餐馆阿谢特拉德(Archestrate)的主厨阿兰•桑德朗(Alain Senderens),也就是“新烹饪”(nouvelle cuisine)的大狂人。不过,1980年我熟识的朋友之中还没有人听过“新烹饪”这个名词。
那一次晚餐,从第一道菜——龙虾肉色拉加芒果泥配上雷蒙夏多奈白酒(Raymond Chardonnay)起,格拉斯就令我与诸客户心悦诚服了。饭后,我缠着格拉斯要他再教我几招。他让我去买一本戴维•莱德曼(David Leiderman)写的食谱《在美国做新烹饪》(Cooking the Nouvelle Cuisine in America)来看。书中的食谱很有意思,但真正吸引我的是前面的序言。莱德曼概括了刚萌芽的这一派想法:采用时令土产食材,回归地方风味的淳朴……这些要领现在大家已经听得太多,都嫌烦了,可在那时候却是一鸣惊人的。
1981年,我把自己的广告公司迁到加州拉斐特的一处山坡华宅,戴维•格拉斯也成为那儿的常客。加州东湾(East Bay)乃是新兴美式烹饪的摇篮,我也和许多北加州人一样,变成一个追逐美食的人。我和新婚的妻子,每逢周末就开着车到处跑,游遍加州的农庄和渔人码头。我车中随时带着一只铸铁的长柄小锅、一把菜刀,以便走到哪儿就烹饪到哪儿。那时我心目中的美味大餐就是一瓶好酒、一个老面发酵的大面包,加上一些从海边岩石缝现抓的淡菜。
1985年,我和妻子搬回奥斯汀,生了第一个孩子。当时的得州似乎没人知道马克•米勒(Mark Miller)正在加州掀起一股西南部烹饪新风潮,我觉得我该告诉得州老乡这件事。我写了一些专题,分送到每一家我认为有可能刊登的报章杂志,结果都是石沉大海。
过了几年,我的一篇稿子里的几段文字在《奥斯汀纪事报》(Austin Chronicle)上出现了。我打电话给这家另类周刊的主编路易斯•布莱克(Louis Black),问他付我多少稿费。他说会寄10美元给我,又说该报需要短篇的餐馆试吃评论。我三言两语就和他谈妥了稿约,心里高兴极了。
我的餐饮写作生涯就这么开始了,大概每写一篇得到稿费20美元。后来,篇幅越写越长,而且内容包罗也广了。没过多久,我就只写饮食,而完全不提餐馆了。
我常写的一个题目是辣椒,包括如何栽种、如何食用、如何用来烹饪,以及如何辨认不同的种类。我谈到辣椒的精神药物效用,引用了安德鲁•韦尔(Andrew Weil)说的话——他那时还不是自然健康论的权威,他曾把吃辣椒后的兴奋状态与吸食大麻和可卡因之后的反应相提并论。我不久便被人称为“辣椒狂一族”的作家。
为了要找奥斯汀作家琼•安德鲁斯(Jean Andrews)在《胡椒:驯化的椒类植物》(Peppers: The Domesticated Capsicums)之中所说的全世界最辣的辣椒,我跑到墨西哥的瓦哈卡去。为了要找不为人知的萨尔萨(Salsas)辣酱汁,我跑到加勒比海地区去。1991年,我创办了“奥斯汀纪事报辣酱节”(Austin Chronicle Hot Sauce Festival),至今仍是全美国最大规模的辣酱比赛之一。我算是找到了人生的定位。
品尝辣椒和追寻相关的刺激慢慢延续到其他类型的历险。因为寻找失传的辣椒品种,导致我去研究墨西哥谜样的文化,进而产生对中美洲历史的浓厚兴趣。我变成了烹调探险家,努力追查古代萨巴特克人、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失传了的食谱。我会把整个假期耗在中美洲古代废墟里,拿着破陶片和古代烹饪器皿请教考古学家。
后来,我开始帮美国航空公司(American Airlines)的机上刊物《美国风》(American Way)撰稿。因为经常要远行到拉丁美洲、法国、加勒比海,我与妻子和老板的关系都大打折扣。1994年,我被广告公司解聘,妻子也提出离婚诉讼。在孤家寡人的处境下,我决定做个全职的自由撰稿人。
这是我一直向往的职业:飞行于世界各地,以有趣的饮食为题写作。我的旅行开销大部分由《美国风》和《自然史》(Natural History)负担。工作虽然得意,收入却不怎么高。做了五年,到1999年,我穷到一文不名。所以,当《辣椒杂志》(Chile Pepper Magazine)主编的职位可坐时,我不得不欣然接受。我周游列国的日子于是告终。
本书收集的40篇文章是我自己的中意之选,另外附有20则食谱。头两章“馋人大追踪”和“他吃的那个我也要”,是我周游世界寻找饮食刺激的五年中写的。我在这些早期的文章中发现,怪异的食品本身未必有趣味,必得有趣的人吃了它,或是某人为了有趣的原因吃了它,它才有趣。
写作历练渐渐多了,我又发现,不一定非得到鸟不生蛋的地方才会遇见有趣的人。“乡土原味”和“欧洲人的怪癖”这两章,记录我在美国南方和欧洲边走边吃的历程——努力想做到吃多少就理解多少。
我现在会怀念那些到处旅行的日子,居无定所也教我学会享受安居一处的乐趣。在“市郊的印第安纳•琼斯”这一章里,我收集了一些近期给《休斯敦周报》(Houston Press)写的文章。也许是我年纪大了,近来发觉自己老家的市场和餐馆几乎和我在外国所见的一样有异国风味。拜各国移民集中之赐,我不必走遍世界就能和柬埔寨农人、越南捕虾者、非洲籍厨师以及墨西哥每个省份的人畅谈了。遇见我从未听过的香药草或是我从未吃过的蔬菜,总是令人兴奋的,在自家后院就能看见这些东西则更让人兴奋。
所以最后一章的标题是“斯人而有斯食也”。风味奇特的吃食虽然依旧令我着迷,我却也从经验中学到,最简朴的食物能挑动最深的体验。我可以老老实实地说,是与鬼灵共享面包的那一天使我改变了。那个故事和最后一章里的其他各篇,叙述的是我最私人的饮食经验。这些记述把我的吃之旅带回原点。旅程开始是为了品尝怪异的东西,之后慢慢转变成探讨各种文化如何在食物中体现,那也让我对自己有了更深的认识。
本书所收集的这些文章,是为了说明这个少见的行业,以及用以理解一个人怎会变成满脑子只想着吃的东西。我和弟弟们(他们的情况比我好不了多少)相聚时,这是个热门话题。
这也许多少和我外婆与我母亲投注在每一顿饭中的那股原始的爱有关系。她们把不能言传的情意都放进烹饪里了。如今我吃每一顿饭时都试着去彻底领会那些情和意。
还有一点是我确知的:每当情感澎湃的时刻,我就特别想吃泡菜。
探索吃的世界,凭借的是坦然无畏、一副铁胆,还有一股追求情感与文化层次的渴望。不做作而讨喜,绝无多数追逐山珍海味的美食写作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
——《柯克斯评论》
从得州监狱的厨师到欧洲顶*餐厅的主厨,作者描述的人物无所不包,读来既令人赞叹,又让人垂涎。多数谈论美食的作品只是让你走进厨房,本书却教你整装待发,踏上自己美食的探索之旅。
——约翰·索恩(John Thorne),美食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