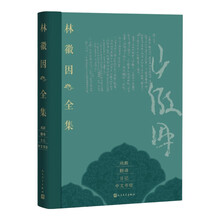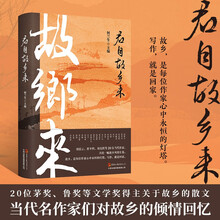荒谬的神话
——黄群司
在一座寸草不生而且非常陡的山上,有一个光着臂膀的男子,在太阳的暴晒下费力地把一块与他的身体不成比例的球形巨石推上那高不可攀的山顶——[破折号不间断,统改]然而这还不够,在他千辛万苦地将这块巨石推上山顶后,那块巨石会因为自身的重量再次从山顶滚下去。而这个男子却只能看着巨石的影子,在被汗水模糊的双眼里逐渐地离自己远去。最后,他又得默默地走下山去,在山脚下找到这块巨石,并重新把它推上山顶——就这样,永无止境。这个男子,就是罗马神话中科林斯国的建立者和国王:西西弗斯(Sisyphus)。
西西弗斯为什么会在那里受着这种永无止境而且荒诞的折磨呢?因为他犯了罪。然而他的罪名也是荒诞的:河神阿索玻斯的女儿埃癸娜被朱庇特这个好色鬼给掳走了,西西弗斯则向女儿的父亲告密。朱庇特恼羞成怒,派出死神要将他抓到冥界去,但是机智的西西弗斯用计谋绑架了来抓他的死神,使人间长时间没有了死亡。这位人间英雄的行为彻底触怒了朱庇特,朱庇特派出了勇猛的战神,将死神救了出来,并将西西弗斯送往冥界。可是西西弗斯却在去冥界之前,吩咐妻子不要埋葬他的尸体。于是他在到了冥界之后,对冥后珀耳塞福涅说,没有被埋葬的人是没有资格待在冥界的,要求冥后给他三天时间回人间处理后事。冥后同意了,但是西西弗斯回到人间后,迷恋上了大地的美好景色,不愿去阴冷的冥界受罚,把对冥后的承诺抛到了九霄云外。直到西西弗斯死后,他被众神判逐到地狱那边,在那里,一块永远也不可能停驻在山顶的巨石已经等着他了。
在那里,他要孤独地把一块十分沉重的巨石推上山顶,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它从山的另一边滚落,再重新把它推上来——他要永远重复着这个毫无意义且令人绝望的动作。
诸神认为没有比这更可怕的惩罚了。的确,当自己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后,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所有的努力都化为乌有——我相信任谁都会在这种前功尽弃的打击下产生绝望。
西西弗斯比普罗米修斯还要悲剧。毕竟,普罗米修斯只是被绑在悬崖上,让一只嗜血的大雕日复一日地啄去自己重新生长出来的内脏,他并没有为此而付出什么努力。可是,西西弗斯费尽心血,将那块巨石一寸又一寸地推上去,最后却看着自己的努力成果在自己面前破碎——这种痛苦,已经超越了推那块巨石所造成的身体上的劳累,成为了一种可怕的心理负担。
可不是吗?我们常人眼里的山顶代表着令人羡慕的成功,而西西弗斯的山顶却是代表着令人畏惧的失败。拖着那伤痕累累的身体来到山顶,却只能精疲力竭地看着自己的努力付诸东流。然而,最痛苦的是,自己还得把这个失败继续下去,还得创造一个新的失败使自己再度沮丧。
我能想象到那个场景:西西弗斯躬着身子,汗水犹如喷泉般地在他身上不断涌出,洗濯着他那双粘满泥土的干裂的双手和坚实的双脚,沉默的巨石在他的推动下慢慢地向山上挪动着。最后,顽皮的巨石在到达山顶后,一溜烟儿地在西西弗斯绝望到近乎麻木的目光中滚下山去。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西西弗斯那道坚毅的身影和那块与他不分不离的巨石依然在陡峭的山腰上不停地闪现。然而,一开始绝望无比的西西弗斯,在与这块巨石搏斗了成百上千次之后,不再把这块巨石当作一种惩罚,而是把它当成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憎恨它,因为每当他看着这块巨石在山顶上屹立的那一刻——哪怕那一刻只有几秒钟,他心中也会涌现出一股短暂而宝贵的自豪。就这样,西西弗斯在这种绝望的惩罚中获得了超脱,在一步又一步前往山顶的脚印中超越了那块巨石的重量,在这种永无休止的折磨中获得了一种专属于他的荒谬的快乐。
尽管他这种快乐在常人眼里是可笑的,但是我依然将他当成一个无人可及的英雄去膜拜。他是一个荒谬的英雄,他用自己无数次的失败获得了荒谬的快乐。虽然,他的每一分努力都会使他离失败更近一步,他每把巨石往上推高一寸,巨石离滚下去的那一刻就更近,但是他坚信:在这无数次的失败后,总有一天,他能够欣慰地看着那块巨石像座雕塑一样稳稳地屹立在这天地之间的山顶,用胜利者的自豪傲视众神——尽管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是一件可能的事。他的坚持是荒谬的,不合逻辑的,因此这就注定了他不会成功,他的每一次成功都将是下一次失败的开始。
跟他相似的还有两个人:填海的精卫和游侠骑士堂·吉诃德。但是,我觉得后面这两位似乎比西西弗斯更悲剧一些。
精卫填海的故事已经是家喻户晓。相传太阳神炎帝有一个女儿名叫女娃。因久居天宫无聊,有一天,女娃驾船游东海而溺,其愤愤不平的灵魂化作一种花脑袋、白嘴壳、红色爪子的鸟,栖息在发鸠山,发出“精卫、精卫”的悲鸣,人们便将此鸟叫作精卫鸟。精卫衔草石由发鸠山飞往东海投入,誓言要填平东海,让后人不会再淹死于海中。
我不知道精卫有没有思考过一件事情:那就是,根据物理定律,草石只能把等体积的海水给排挤开来,并不能改变它的质量,把草石丢进海里,除了把海平面变高了一点点之外,其他什么也没做成——也就是说,精卫不但没把海填掉,反而还把海给填高了。它在做真正意义上的机械效率为零的无用功。它永远不可能也根本不可能把海填掉,填海的梦想只能是痴人嘴里可笑的梦。
如果说精卫的行为是可笑的话,那么堂·吉诃德的行为绝对会让人笑得眼泪都流出来。《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堂·吉诃德,看传奇骑士小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以至于他天真地认为这个世界上曾经存在着那些以一人之力抵抗百万大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与美丽佳人有着一段乌托邦式的爱情的骑士。于是为了践行伟大的骑士道,他穿着一身烂盔甲,骑着一匹名叫“若昔难得”的瘦马,持着一柄生了锈的长矛,带着一个和他一样疯狂的名叫桑丘的侍从,开始了锄强扶弱、铲除人间邪恶、威风凛凛的骑士之旅。不用说,一路上闹出了许多笑话:诸如把客栈当作城堡,把一个从理发匠手中抢来的铜盆当作是神器“曼博里诺头盔”,把转着的风车当作百手巨人,把一群罪孽深重的苦役犯当作无辜之人给放了却遭到他们恩将仇报的毒打,把根本就不存在的心上人杜尔西内娅当作是一个丑陋的农妇……然而他始终认为是“魔法师搞的鬼”。
堂·吉诃德没有认识到,那些所向披靡、勇敢无畏的骑士只不过是文人笔下的脆弱神话,一旦到了现实就会像来到空气中的鱼一样窒息而死。他们那伟大的精神像太阳一样高高地挂在天上,耀眼得使俗里俗气的世人羞愧难当,遥不可及。而堂·吉诃德居然妄想把这个太阳带到地面上来,希望人们在接受它崇高的光辉后会变得和谐相处。可堂·吉诃德错了,这个太阳那崇高的光芒只会灼伤世人,不会使他们开窍,因此堂·吉诃德的“壮志”自然遭到了世人的嘲笑。堂·吉诃德的那些壮举,只有少数真正帮助了别人,更多的是给别人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造成了事与愿违的结果。
尽管如此,西西弗斯依旧默默地把巨石推上山顶,再默默地看着它滚下山顶;精卫还是锲而不舍地把一块又一块、一撮又一撮的草石,填进那无底洞般的大海;堂·吉诃德依然一如既往地在现实世界中践行着他那荒唐可笑、但又崇高无比的骑士道,在别人变着花样的嘲笑中固执地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用自己的一切,缔造着属于自己的荒诞不经却又永垂不朽的神话。
他们的追求使他们的处境一日不如一日,他们的努力不断地加剧着他们的失败。西西弗斯每把巨石推高一寸,巨石离滚下山的那一刻也就越近;精卫每把一撮草石填进海里,海水离淹没大地的那一刻也就更近;堂·吉诃德在现实中每践行一次他的骑士道,无妄之灾也就离他更近。
是的,他们的行为如此之荒谬,以至于世人都对他们投以嘲笑的目光——但是,正是因为他们的荒谬,才能使其成为一个个永恒不老的神话。如果西西弗斯屈服于沉重的巨石之前,精卫绝望于浩瀚的大海之前,堂·吉诃德失望于残酷的现实之前,那就不会有这三个为世人所传颂的不朽传奇。
虽然顽皮的巨石永远也不可能屹立在山峰之巅,无垠大海也永远不可能化为平地,伟大的骑士道永远也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但是他们依然坚信着属于他们的荒谬信仰。
我可以想象到,他们是快乐的。西西弗斯哼着歌儿,不慌不忙地以优雅的姿势推着巨石;精卫迎着海风,兴高采烈地将草石填入海中;堂·吉诃德骑着若昔难得,带着诙谐而憨厚的侍从桑丘,不停地践行着那崇高美好的骑士道,他们在这荒谬的旅行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快乐。
因此,他们快乐的根源恰恰是他们的痛苦:那块永远都会滚下山去的巨石,那个永远都深不可测的大海,那种永远也不被现实接受的骑士道——这都是他们痛苦的根源。西西弗斯因为巨石而受到永无休止的惩罚,精卫因为被大海淹死而产生令人嘲笑的填海之愿,堂·吉诃德因为骑士道而受到的种种飞来横祸。尽管如此,他们仍然顽固地将这些荒谬的信仰当作自己的梦想,当作自己生存的意义,当作自己的快乐。
尽管他们的神话连同他们本身都是一个荒诞不经的笑话,但是他们却比那些嘲笑他们的正常人要伟大千百倍。作为西西弗斯,他比那些成天为了情爱或各自利益而明争暗斗的神要了不起;作为精卫,它比那些时不时在海军头上拉一堆大便的海鸟要了不起;作为堂·吉诃德,他比那些媚上欺下、口是心非的伪君子要了不起。那些自诩正常无比的神、海鸟、俗人,能比西西弗斯他们正常到哪里去?
让我在此,向这三位不为世人所理解的荒谬英雄们致以最真诚的敬意——我始终相信,终有一日,西西弗斯能站在山顶上一边摸着屹立的巨石一边傲视众神,精卫能在天空中自豪地看着化为平地的大海,堂·吉诃德能够威风凛凛地坐在若昔难得上与桑丘一起看着安居乐业、和谐共处的人们。他们会在这荒谬的人生中获得超脱,实现自己的伟大梦想,在这荒谬的痛苦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伟大欢乐!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