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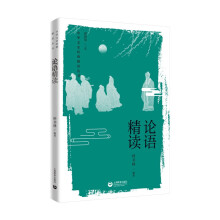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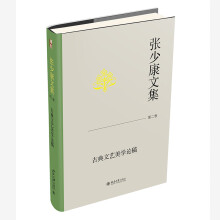
I.《如果种子不死》
“一个可能很快就凋萎的桂冠,我一点都不想要。”
遭遇人生变故与舆论谴责之后,面对创作与道德间的冲撞与撕扯,
五十岁的纪德回望半生,展开自我清算,
写下坦率到天真的回忆录与忏悔书:
前半部分追溯敏感压抑的童年时光、悉数坦白青春的悸动与爱恋,
在他的成长路上,天性与束缚不断角力,禁欲主义与无畏之爱展开持久对峙。
后半部分记录改变纪德人生、写出《地粮》等系列作品的北非之旅及与王尔德等人的真实交往,
以率性之姿跃出时代的禁锢,引领数代青年展开一场朝向自由的长久叛逃。
II.《地粮·新粮》
不错,它们使我们受到了耗损,但也构成了我们的光辉。”
二十八岁的纪德,游历北非、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南部,在崭新的天地间写下《地粮》。
他狂热地表达生命的能量,想摆脱文学界的矫揉造作,宣称要让文学“赤脚踩在地上”。
六十六岁的纪德,用一生的思想食粮回应少作,时隔半生,再度谈论爱情、孤独、自由、欲望,
凝结成一段段沉思中的美丽箴言,命名为《新粮》。
III.《遣悲怀》
——“我强制自己对自己高度忠诚。我有新的东西要说。”
《遣悲怀》献给灵魂伴侣、创作原型玛德莱娜:
“我的所有作品都向她致意;没有任何书写像我的这般源自如此私密的动机。”
写作,是哀悼和丧失最后的救赎,切开自我的所有截面,直面欲望、背叛和愧疚,
也展示懦弱、遗憾和伤痛碾过身体的痕迹,
允许自己越过边界,在道德与现实的鸿沟里反复来去。
《纪德日记》则包含了纪德一生创作的核心注脚,横跨人生重大阶段,将自我作为方法,
这种赤诚的袒露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史中都堪称绝无仅有:
“我想以一种更神经质、更尖锐、更干练的方式表达自己。”
这是更真实鲜活的纪德,对自我和时代的透视散落在道德、自由、人性、美学、阅读、政治、欲望的吉光片羽里。
I.《如果种子不死》
我出生于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当时我父母住在美第奇街一套位于五楼或六楼的公寓里,几年之后搬离,所以那套公寓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是我记得公寓的阳台,或说是从阳台上看到的景物:正前方的广场和水池中的喷泉──更准确地说,我记得父亲为我剪的纸龙,我们从阳台投向空中,它们随风飘过广场水池上空,一直飞到卢森堡公园,被高高的栗树树枝截住。
我也记得一张很大的桌子,无疑是餐桌,铺着一块垂地的桌布,我和门房的儿子溜到桌布下,他和我同龄,有时会来找我玩。
“你们在下面搞什么鬼?”保姆大声问。
“没什么。我们在玩。”
我们把带到桌下当幌子的玩具大声晃动,其实我们玩的是别的:我们不是在一起玩,而是两人紧靠着,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玩的是叫作“坏习惯”的游戏。
我们两个当中,是谁教对方这个玩法的?是谁先开始?我不知道。必须承认,有时候小孩不必人教,自己就会发明这些游戏。至于我,我不记得到底有没有人教我,我又是如何发现了这种快感。在我记忆所及之处,它就已经存在了。
我知道说出这件事是个错误,也清楚会造成的后果,我已预感到人们或许会拿这件事来攻击我。但我的自传存在的唯一原因就是真实。就当我是因忏悔才写这本自传的吧。
在那个纯真的年纪,人们希望孩子的心灵只有透明、温柔、纯净,然而我在自己身上看见的,却只有忧郁、丑陋、阴险。
大人带我到卢森堡公园去,但我不肯和其他孩子一起玩,离得远远的,一脸忧郁,待在保姆身旁,看着其他孩子玩。他们用小桶装沙子,做了一排排漂亮的沙堆……趁保姆转过头的一瞬间,我冲过去踩塌了所有沙堆。
II.《地粮·新粮》
拿塔纳埃勒,对于许多美好的事物,我耗尽了我的爱。这些事物的光辉来自我为之不断燃烧着的爱。我无法使自己厌倦。任何热忱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爱的耗损,一种美妙的耗损。
那些怪僻的意见,那些思想上的极端迂回曲折,那些分歧不一,永远吸引着我——异端分子中的异端分子。每一种思想,只有在它不同于别的思想时,才能使我感兴趣。因此,我排斥了同情。在同情之中,我看到的只是承认一种共同的感情。
拿塔纳埃勒,爱根本不是同情。
行动吧,别去判断这是好是歹。去爱吧,别担心这是善是恶。
拿塔纳埃勒,我要教给你热忱。
拿塔纳埃勒;宁可要一种悲怆的生存,也不要那种安宁。除了那死亡的长眠,我不需要其他的安息。我担心,在我一生中没有得到满足的种种欲望和精力,会继续存在而使我极度痛苦。我希望,在把压积在我胸中的一切情愫都表露在人间以后,我能心满意足而又万念俱寂地死去。
拿塔纳埃勒,爱根本不是同情。你明白,这两者并不一样,不是吗?有时,只是由于害怕失去爱,我才会对忧愁、烦恼、痛苦产生同情;否则,我是很难忍受它们的。要让各人自己去关心生活。
(今天我不能撰写,因为谷仓中有一个轮子在转动。我昨天就见到它了。它在打油菜。屑粒飞舞着,油菜籽纷纷滚落在地上。灰尘使人窒息。一个妇女在推磨子。两个可爱的男孩,赤着脚,在收油菜籽。
我哭了,因为我没有什么别的话好说。
我知道,在你没有什么话好说的时候,就不动笔。可是我却写下来了,对同一题材我还要写些别的东西。)
III.《遣悲怀》
昨天晚上我想着她,和她说话,就像我过去常做的那样,而且在想象中比现实里当着她的面更轻松自在;然后,我倏地想到:她已经不在人间了啊……
的确,我经常会去离她很远的地方,一走就是许多天。但自打孩提时代开始,我就养成了向她报告一天收获的习惯,并在心中将她与我的悲伤和喜悦联系在一起。昨晚我就是这么做的,但忽然想起,她已经死了。
一切骤然失去了颜色,变得暗淡无光,无论是近来我对一段远离她的时光所做的回想,还是此时此刻的回忆;因为我在思绪中重新经历那些事,都是为了她。我立刻明白,失去她以后,我的存在也变得虚无,再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
*
我不太喜欢“艾玛纽埃尔”这个名字,为了尊重她的谦虚,我在作品中给她取了这个名字。她真正的名字之所以令我欢喜,可能只是因为从小到大,她在我心目中一直召唤出优雅、温柔、聪慧和善良的形象。这个名字被别人使用时,我会觉得它仿佛被篡夺了;在我看来,唯独她有权使用这个名字。当我为我的《窄门》创造出“阿莉莎”这个名字时,并非是出于矫情,而是为了保留。阿莉莎只能有一个。
可我书里的阿莉莎并不是她。我描绘的不是她。她只是我构思女主角时的出发点,我不认为她曾在其中认出多少自己的身影。她从没和我谈过那本书,因此,我只能推测她读它时可能有过的思索。那些思索对我而言一直带着悲痛的色彩,就像一切源自她内心的那股深沉哀愁的东西;我是在很久之后才开始揣度出那种哀愁的,因为她那极为含蓄的性格一直阻止她将其显露、表达出来。我为我的书设想出来的情节无论再怎么美,难道不是在向她证明,我对现实的戏剧性一直视而不见吗?想必她感觉自己比阿莉莎简单得多,比她正常、平凡得多(我的意思是,比较不像高乃依描绘的女性角色,不那么紧绷)?因为她无时无刻不在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的美貌、优点,怀疑一切使她如此光彩照人、如此珍贵的事物。我想,我是在后来的岁月里才更加理解她的,但在我爱意最强烈的时候,对她的误解又何其深重!因为我的爱所带来的意义,并非在于接近她,而是在于设法接近我所创造的那个理想人物。至少这是我现在的感觉,而且我不认为但丁对贝雅特丽齐做的事与此有何不同。她已不在人世的此刻,我之所以企图重新找到、追溯她的往昔,那也是──特别是──出于一种做出补偿的需求。我不想让阿莉莎的幽灵遮蔽她真实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