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生命的第一口饭
这种生物有些像金龟子,大约 2.5厘米长,有带棱纹的柔软甲壳,会在海岸浅滩的沙子里窜来窜去。它察觉到了由气味、振动与光线变化交织而成的画面。它的蠕虫状的猎物会往沙里挖洞,企图以波浪形路线逃到安全地点。不过为时已晚。掠食者用钳状的上颚把猎物扯开,吸进嘴里、吞进食道,然后继续它的行程,寻找藏身处躲藏,让食物消化。
关于4.8亿年前的这一餐的证据,是在1982年发现的。那一年,还是硕士研究生的马克?麦克梅纳明(Mark McMenamin)为墨西哥政府调查索诺拉沙漠( Sonoran Des ert)的地质情况,在墨西哥索诺拉州图桑市(Tucson)西南方约100千米处的最高点朗山(CerroRajón)山侧进行挖掘,这里在古代曾是海底。他在一片灰绿色页岩上注意到一个很微小的化石压痕,当时他也没有多想,就把那个压痕从岩石上凿下来,和其他标本一起装袋了。
在未经训练的人眼中,这块化石只不过是大约 0 . 6 厘米长、隐隐约约的连续刮痕。当麦克梅纳明把它拿回实验室研究时,他辨认出那是三叶虫被蚀刻在硬化泥浆上的运动痕迹。在动物界里,三叶虫几乎要算是所有动物的老祖宗了:鱼类、双翅目、鸟类、人类。三叶虫在海床上留下无数化石,让它们成为了这种天然的自然博物馆里的固定班底。很多化石有多节式外壳,看起来像是鲎和蜈蚣杂交的产物。这种化石的纹路图样很有名,甚至还有一个 学名 :“多线皱饰迹”( Rusophycus multil ineatus)。麦克梅纳明保留了这个化石,也在自己的博士论文里提到了它。一直到二十多年后他担任曼荷莲学院地质学教授、研究早期的生命演化过程之前,他都很少想到这件事。
后来,当麦克梅纳明意识到他以前忽略掉了一些东西时,他再一次检查了这个化石。“它具有这种额外的特征,不只是三叶虫而已,紧邻的另一个弯弯曲曲的痕迹化石也有这特征。”?他说,“这些东西很罕见。”他推断,这个化石包含了两种生物相遇的证据。另外的那道痕迹,就是一只更小的蠕虫状生物想要钻进泥巴里的证明,从这些记号的排列来看,显然三叶虫就在它的正上方。麦克梅纳明用上了“ 奥卡姆剃刀”( Occam’s Razor)原理: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三叶虫要挖洞找吃的东西。他写道:这就是“第一口饭”的证据,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掠食者吞吃猎物的化石。
这一餐的味道如何?有可能想象出来吗?
在那个时代,也就是寒武纪(Cambrian Period)之前,就任何有意义的方面来看,味道都是不存在的。地球上的生命大部分是由漂浮、过滤和光合作用组合而成。细菌、酵母和其他单细胞生物,藏身在花岗岩的沟纹里或是沙粒之间。有些单细胞生物会凑在一起形成黏糊糊的细胞团。管状或碟状的生物体会搭着洋流的顺风车漂流。那时的“吃”,是指吸收海水里的营养成分,有时候是指某个生物体包裹住另一个生物体。
接着,经过数千万年——以地质学的时间尺度来说只是一瞬之间——海洋里充满了各种新生物,包括三叶虫,它成了生命演化史上最成功的生物类别 ;它们称霸地球的时间超过2.5亿年。三叶虫大约是5亿年前出现的,也就是我们所知的自然界真正开始的时间 :有史以来第一次,生命开始系统化地吞食其他生命。这些新生物和它们的前辈不一样,它们有嘴巴和消化系统。它们拥有较原始的大脑和感官,以侦测到明、暗、运动和泄露形迹的化学特征,并利用这种精巧的新工具来捕猎、杀掉猎物与填饱肚子。就像伍迪?艾伦( Woody Allen)在电影《爱与死》(Love and Death)里的角色鲍里斯(Boris)说的:“对我来说,大自然就是……嗯……我也不知道,就是蜘蛛与虫子,以及大鱼吃小鱼,还有植物吃掉植物,动物吃……它就像一座巨大无比的餐厅。”
三叶虫并没有存活到现在,那些化石也没有办法显示关于它们神经系统的信息,所以想要知道它们的感官能力,得依赖经过训练的推测。确实,它们可能完全没办法察觉像黑巧克力、葡萄酒这类复杂的气味。而人类的味觉,即使是讨厌的味道,都充满了微妙的东西,而且和其他气味、过去的事件、感情,以及我们所有的学习经验息息相关。三叶虫很可能不会有“愉快”这类的感觉,而且仅能保留一点点残存记忆。对它们来说,每一餐尝起来的味道都差不多,而每一餐显然大多来自化解饥饿感以及攻击的冲动。
然而,这些原始的味道元素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演化成就,而人类的味觉同样具有这种相同的基本生理学构造。当然,听起来像是将小泥屋与沙特尔大教堂 [1] 做对比。不过,味道的基础就此奠定了。地球生存条件的某些重大改变,引发了这场掠食者与猎物间的重大变革,也就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Cambrian explosion)。科学家们对于当时是什么状况并没有达成共识。有些科学家认为那是一场史前时代的全球变暖造成的,气温升高使长期冰冻的两极冰帽融化,海面上升了数百米,海水淹进内陆,淹过长了地衣与真菌的低矮山丘和岩石(树、草和开花植物在当时都还没有出现),侵蚀出潟湖并塑造出沙洲与浅滩,创造出相当适合生命体生长繁殖的温暖浅洼地。其他一些科学家认为这次大爆发是地球磁场方向改变导致的,更有人指称是突变—— 这种突变会导致动作电位(action potential)出现,也就是让神经细胞能远距离沟通的能力——或是DNA编码上的其他偶然变化导致的。
不管事件的精确顺序是怎样,在敏锐的感官与演化的成功之间,已经建立起一个相当牢靠的连接。就在身体与神经系统适应了日益增加的威胁与机会之后,一场生物学上的武器竞赛展开了。曾经一度只是“侦测与反应”机制的感官,为了引导出复杂的行为,必须发展得更有效才行。味道成了这个过程的关键。从三叶虫存在的时代到现在,觅食、捕猎和进食等行为,推动了生命不断地自我发展,最终在我们人类的大脑与文化成就上
达到巅峰。味道胜于视觉、听觉甚至是性,是我们之所以为人的核心要素。它创造了我们。麦克梅纳明说,最为讽刺的,就是世界上开始出现杀戮,并伴随着难以言喻的痛苦,但这也发展出智能和知觉,最终产生了人类的意识。
水果沙拉
那只是一道橘色的闪烁光影,不过却能穿过层层绿叶的缝隙。大约200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丛林中的猴群,已经靠乏味的食物过活好一阵子了。这些食物主要是叶子、味苦的树根,还有虫子加上些许辛辣的浆果。突然间,好像出现了很不错的东西。随着它们爬过树枝,视线受到了限制,眼前出现了更多橘色的光影。它们跳跃着,一起摆荡到正确的地点,用五根手指抓住并捏碎红褐色的果实,让果汁流满双手。其中一只在树枝上蹲下,背靠着树干,大口吃着果子,芳香混合着苦味在口中四溢——短暂且强烈的快感冲击着它。直到森林的地面上布满了吃剩的果核,这场“ 宴会” 才算结束。
猴群的世界也就只有几平方千米大,它们的活动范围可能和摩尔根兽的活动范围差不多。两者都在近似的环境里演化——在一颗巨大的流星撞击尤卡坦半岛(Yucatán Peninsula)海岸、导致使恐龙灭绝的生态灾难出现之前,靠食腐维生,躲避着掠食者。但是其中有两点重要的差异。我们的祖先以往先是在地面上猎食,然后才向上发展爬到树上。此时的猎食活动占据的是三维的空间,而不是二维的平面,而且还有着搭配深度知觉与生动色彩的新型视觉。这个进步把视觉和味道的距离拉得更近。伊甸园里最先引起夏娃注意的,想必就是禁果的鲜明颜色,这一点对于现在我们用餐也一样关键。颜色、形状和食物的排列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并且激起食欲。
大多数哺乳动物具有双色视觉,它们的视网膜(位于眼球后方感知影像的区域)包含两种特殊的感应细胞,即视锥细胞,它含有能侦测到光线中蓝、红波长的受体。具有双色视觉的动物可以分辨约1万种不同的色调。不过在大约2300万年前,某种猴类身上发生了基因复制。受突变影响的那些猴子,获得了第三组视锥细胞,这些细胞能调适光谱黄光带。更早以前的哺乳动物所看到的单调灰色的色彩,现在变成了紫、粉红、天蓝、淡紫、青、珊瑚红这些颜色。红色系变得更深、更精细,绿色系变得更柔和、更多样化。具有这种强化视力的灵长目动物——目前包括某些猴类(不是全部)、所有猿类、人类——最多可以侦测到100万种颜色。(鸟类有四种视锥细胞,看到的色彩更炫目、更丰富。)
要在丛林背景下发现水果很困难,就像玩“ 威利在哪里” 系列绘本一样 :眼睛和大脑必须从具绝对多数的色彩当中,发现与众不同的颜色。在20世纪90年代,剑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本尼迪克特?里根(Benedict Regan)与约翰?莫伦(John Mollon)着手测试水果视觉(fruit-vision)假说。他们聚焦于法属圭亚那丛林里的红吼猴( red howler monkey)。三色视觉仿佛要证明自身的演化效力似的,继大约1300万年前的美洲吼猴之后再度单独出现。要解释三色视觉为什么在演化上这么成功,也只能靠猜测,不过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可能解释 :彩色视觉有助于灵长目动物辨认出成熟的水果。
吼猴偏好“ Chrysophyllum lucentifolium”这种金叶树的果实,它的果实果皮坚硬,吼猴得用牙齿才能咬开,还有能够通过吼猴消化系统的巨型种子。果实熟成时呈现丰富的黄、橙混合色调,与周围的绿色背景形成了理想对比。一队研究人员在低湿雨林扎营数天,在他们头上大约 3 0 米处,是浓密的树冠。他们在猴群爬上树梢的时候跟着上去,收集它们摘下、吃过,然后丢弃的水果。
科学家利用光谱仪测量植物颜色的波长后发现,吼猴视网膜的色素,几乎像是为了让它们认出藏在叶子里的黄色成熟果实而量身打造的。这点很明显不是偶然,因为金叶树果实的颜色只占了光谱带里很窄的部分。自然选择似乎已经很巧妙地把两方调整得很和谐,制造了双赢局面 :猴子有果子可以吃,而果树获得了把种子散播出去的途径。(或许其他食物也占了一席之地 :在某些灵长目动物身上,三色视觉也许已经演化到可以在果实缺乏的时候,在绿叶丛里发现有营养的红色嫩叶的程度。)
总之,彩色果实并非只是一种稀少、美味的佳肴,甚至也不是史前饮食金字塔里的重要角色,它只是一个较广泛的生存策略的一部分。这些在夜间活动的猴子的祖先,此时已经变成在日间时段活动了。在白天的光线下,在树木的高处,色彩取代了气味。在智力与意识的发展上相当重要的嗅觉变弱了,现在,视觉才是重点。这种从某种感官偏向另一种感官的状况,都被写入基因里了:具有三色视觉的灵长目动物,比没有三色视觉的灵长目少了许多有用的嗅觉受体,也就是说,它们能探测到的气味比较少。
雨林与丛林充满可食用的叶子,不过果树就比较分散了,而且有些果树只在一年当中的特定时间结果。这种情况下,要生存就得靠一定程度的规划。为了能够一直有果实可吃,动物必须记住最好的果树在哪里、什么时候会结出可以吃的果实。水果是真正的奖赏,而且要靠聪明才智才能得到。吃水果的黑猩猩、蝙蝠与鹦鹉的大脑和身体的相对比例,分别比吃叶子的大猩猩、吃虫的蝙蝠与其他大多数鸟类要大。
不像独来独往的摩尔根兽,古代的猴子会整个猴群一起行动和作业,用声音、眼神和手势来沟通。这时,优越的视力也大有帮助。它们的眼睛位于头部的前面,这使得它们具有三维的视觉——奇怪的是,这样的眼睛分布是食肉动物的特色,食腐动物就不是这样。如此分布的眼睛能让潜在的猎物位于视野的中央,捕食者可以很快地认出猎物、评估胜算并发动攻击。不过对灵长目来说,纵深感能让它们更容易辨认出行踪隐匿、有保护色的掠食者的动作,并借低亮度的树枝网络来快速移动,此刻若踏错一步,就很有可能送命。由于每个个体只有一双眼睛,并且视线焦点对着前方,因此个体的生存机会就得依靠群体的集体行动,用多双眼睛盯着各个方向。
对捕猎来说,表情比较丰富,也会比较占优势。猿类与人类的大脑视觉皮层与身体大小的相对比例,要比其他哺乳动物的相对比例大,而且负责做出表情的神经中枢也比较大。所有哺乳动物表现出的恐惧、恶心、愉悦等生硬表情,不再只是出于无意识的反射,而是加上了个体细微之处的层次。一个目光交会就可以传达很多东西。就像海军陆战队的小组那样,猴群会像食物采集队一样运作,从它们的集体觅食,就可以预见现今的团体聚餐。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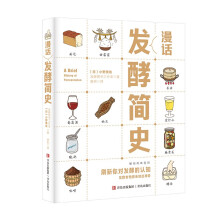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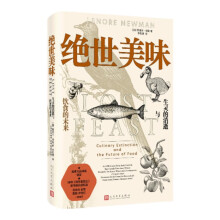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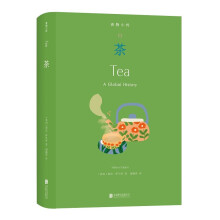

——庄祖宜,《厨房里的人类学家》作者
麦奎德探讨了刻意操纵味道如何实质影响人类生活经验的每个方面,从愉悦到痛苦、从欢乐到哀伤。这是一本令人惊叹、意义重大的著作,值得一读再读。
——戴维?珀尔玛特(DavidPerlmutter),《谷物大脑》作者
这是一个开始于10亿年前的故事……作者讲述的是关于科学、文化、历史、感官与我们的未来的故事。
——《科学美国人》
本书是烹调历史与味觉科学的出色结合。
——《出版人周刊》星级评论
这是对味觉本质的一次令人振奋的研究……作者在面对死局时泰然自若,充满热情,他对“味道的核心”进行了一次有趣的探索,而这个核心从未被真正触及过。
——《科克斯书评》
在复杂性与矛盾中探索味道……作者是一位巧妙的作家,具有进行生动隐喻的天赋。
——《商业周刊》
一个彻底的调查……作者解开了人们对各种味道偏好与反应不同的原因,本书是一场阅读盛宴。
——《书单》
又是一部野心宏大、壮阔史诗型饮食书写。但和我同样欣赏的迈克尔?波伦(MichaelPollan)系列作品不同,路线较偏科普;谈品尝事,竟溯源直至上古四亿八千万年前之生物起源时期,随演化与物竞天择历程,抽丝剥茧逐步形塑出人之味觉成形轨迹,一路读来,着实咋舌折服。
——叶怡兰,饮食生活作家,《Yilan美食生活玩家》创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