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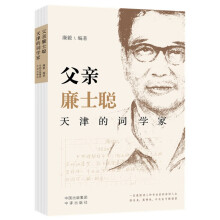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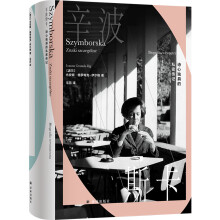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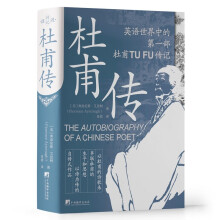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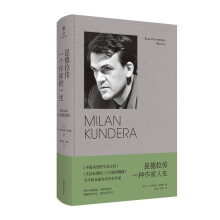
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自传体回忆录,回忆了一战前欧洲秩序井然、从容淡定的生活,他的中学、大学岁月,在世界各地的游学经历和艺术创作生涯,与欧洲文化名人的真挚情谊,一战爆发的真正原因和一战中人们失去理智的战争行为,以及战后的道德与价值观的倒退与混乱、法西斯的崛起和一个时代的结束。
1942年2月。里约的狂欢节一如既往地热烈。人群中,一位久经沧桑的异国男子,正尝试着忘记过去,接受眼前这久违的无忧无虑,像一个正常年代的普通人那样,跟随陌生的笑脸而欢笑。这对他并不容易。就在短短几个月前,一部回忆录刚写完,那是他作为一个欧洲人的回忆,挥之不去的过去。在远离故土千山万水的地方,那个曾经属于自己而现今已被粉碎的太平盛世又光芒四射地出现在他的眼前,一切在他的大脑再次回放,他于是记下它的一步步沦丧,记下世道人心的彻底改变。没有任何资料或笔记可以参考,多年记下的日记不知散落何方。完成这项工作后,他觉得疲惫极了。前往狂欢节的前一周,在写给亲人的信中,他告诉他们,自己和妻子现在会和小狗玩很久,比理智的人在正常的年代和小狗玩的时间要长很多。他还告诉他们,自己准备去参加狂欢节,但其实并不是那么开心,因为明明知道在其他地方,有房屋被炸毁,有人在死去。但如果不去参加这个盛大的节日,长久没有任何娱乐的他和妻子又仿佛活得太不像个人样,太过消沉了。就在一年前出版的《巴西——未来的国度》这本书里,他还专门提到这个全球闻名的节日,倘若自己不去亲身体验一番,怎么还算个作家呢?在南半球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安顿下来近半年时间了,他仍不能想象要在此度过晚年。可是,这是一片多么可爱的土地啊,他内心无比感激这些友善的巴西人。置身于淳朴简单的心灵间,徜徉于温柔旖旎的热带光影里,疲惫的灵魂暂且休憩。
三个月前,茨威格在客居的小山城彼得罗保利斯度过六十岁生日。妻子绿蒂费心准备了一件了不起的礼物:一套旧的法文版巴尔扎克全集。它和原房主留下的两本蒙田作品,以及一套歌德全集,成了茨威格目前拥有的所有精神食粮。流亡使他放弃了自己的所有收藏,只带着两个行李箱踏上前往南美的轮船。他心情矛盾。一方面,希望有朝一日还能重返欧洲,完成未竟书稿“巴尔扎克”,他甚至还将书稿留在了英国巴斯的旧宅中。但另一方面,他已暗暗预感到故土难回,在精神故乡欧洲,他热爱的一切均成云烟。被彻底放逐到自己的祖国和母语之外,他已被连根拔起。
在宁静的彼得罗保利斯,茨威格通过一台小小的收音机了解这个世界的命运。他每天收听广播,时刻关注最新战况。但是,每一场战役、每一次轰炸、每一回进攻或撤退,对于他,都是新的惊惶、失望和痛楚。同样流亡到彼得罗保利斯的朋友这样形容他:斯蒂芬就像一只蜜蜂,从每个花朵中吸吮苦涩。他总是想,如果有一天,纳粹的铁蹄踏上南美大地。他和绿蒂该逃向何方?他们已经太累了。
就在狂欢节的精彩高潮即将到来的那个清晨,茨威格夫妇和友人一道在里约共进早餐。餐桌上的一份报纸吸引了他的注意,“新加坡沦陷”“英军大溃败”“德军已向苏伊士运河挺进”。茨威格久久地看着这份报纸。报纸上,和这些战报赫然并列的,是狂欢节的喜庆照片。在这一刻,人类生活的荒谬和残忍令他感到难以忍受。当日,他和妻子提前返回了彼得罗保利斯。欧洲、亚洲和非洲,倘若一一沦陷,这场战争将是无限的噩梦。这证实了他的预感,回归的道路已封死,令人心怀希望的未来遥不可及。而今,他不再像一战时那样还能对民众发出自己的声音。他的《耶利米》在1917年复活节的德国出版时仍然销售一空。他当时还能前往日内瓦与罗曼·罗兰以及其他交战国的友人会面,他们仍能梦想通过努力创造一个更人道的世界。但是,“世界在这个时代倒退了一千年的道德”。如今,茨威格和他的朋友们感到,面对这个世界,他们无能为力。
邀茨威格同去里约参加狂欢节的好友费德后来回忆着那个清晨,他认为,假如那天报纸上刊登的不是新加坡沦陷,而是日本空军遭全歼,茨威格的反应并不会有所不同。茨威格曾经说过:“假如有人因为柏林遭轰炸而欢呼,我无法和他们一道欢呼。最残忍的事情莫过于,在这场战争中,唯独战争本身没有对立面。没有哪个国家拒绝战争。”德国作家弗兰茨·韦尔福尔在纪念茨威格的悼文中,引用了犹太经典中一个古老传说。当以色列的子孙们眼见法老的军队在红海全军覆没,便在岸上集体兴高采烈地大声唱起胜利的赞歌。在这片狂热的喧嚣之上,响起一个威严的声音:“我的造物,丧命众多。你们,和他们一样,只是我的创造物,你们却要欢呼雀跃来庆祝胜利吗?”这个声音,在茨威格心中,想必没有沉寂。
罗曼·罗兰曾称茨威格为“获取了弗洛伊德那把危险钥匙的诗人”,是卓越的“心灵捕手”。他收藏伟大艺术家经典作品手稿的嗜好,尤其反映出其对于人类心灵活动的高度关注。同样,这种能力和敏感也体现在他对政治环境和战争局势的观察和判断上。对于时代的悲剧和人类的隐秘本能,他具有慧眼。早在一战期间,从欧洲大街小巷的群情激愤中,在前所未有的集体歇斯底里中,他就看到弗洛伊德所发现的人类内心深处反文明的野蛮本能,从而对席卷整个世界的狂热充满警觉。“这世界如此荒诞,但我们觉得自己没有义务去附和它。”
作为孜孜不倦的旅行家,他的足迹布满半个地球。通过印度、南美和北非之行,茨威格很早便认识到欧洲不是世界中心。于是,一种对于全人类命运的关心,一种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对和平的信仰,使得他一生远离任何蛊惑人心的力量,而和欧洲所有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结成同盟。他从来都自视为欧洲人,自视为世界公民。他将自己对欧洲共同体的信仰归功于故乡,在20世纪初的维也纳,各民族的人们将吸收到的高雅文化向内转化为修养和情趣,专注于精神生活。“人们并不像今天这样将宽容视作软弱,而将它尊为道德的力量。”1932年,在一次题为“关于欧洲的道德毒害”的演讲中,他强调,“新的教育必须从改变了的历史观出发,其根本核心在于,必须更加强调欧洲各民族的相同点,而非其矛盾。孩子们被教导热爱家乡,诚然无可厚非。而我们希望的是,除此之外,还要教育他们热爱欧洲,我们大家共同的家乡,乃至整个世界和全人类。祖国这个概念,不是怀着仇恨的表达,而是运用在与其他国家的联合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相对宁静的时间,茨威格有意识地四处宣扬他的信念,他的听众从来不限于某个狭小的国家或地区,他的演讲语言从来不限于自己的母语。那时的他依旧对这个世界有信心。他没有想到,短短几年之后,欧洲和整个世界都还要再经历更残酷的迫害与杀戮,突破已有所有的生存经验。“在此之前,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还从未露出如此狰狞的面目。”
“旅行,持续不断地旅行,从一个星空下到另一个星空下,到另一个世界中去,并不等于摆脱了欧洲,摆脱了对欧洲的担忧。”刚到巴西不久的茨威格已经历过一次精神崩溃,他已无力再次出发。从狂欢的里约提前返回彼得罗保利斯的他,已暗自做好了最终的抉择。他的精神似乎不再受到压迫,内心也恢复了平静,为最后的时刻做着准备。那天和他通过电话的友人们事后才懂得了他语气当中的意味深长。在这最后一个夜晚,他和妻子再次将前日同去里约参加狂欢节的朋友邀至家中,共度了最后的四个小时。茨威格把从老朋友那里借的书归还给他,并和他下了最后一盘棋。
在最后的日子里,茨威格曾经和友人讨论过死亡。想必他对死亡早做过深入的考虑。历史上那些不朽的人文主义者的命运越来越吸引他,离世前几个月,他着迷于蒙田的著作和他的一生,完成了《蒙田》这部最后的传记作品。对于他,蒙田是“在某种特定时刻展现自己全部意义的作家”,“为了真正读懂蒙田,人不可以太年轻,不可以没有阅历,不可以没有种种失望。蒙田自由和不受蛊惑的思考,对像我们这样一代被命运抛入到如此动荡不安的世界中的人来说,最有裨益。”①[1]他受教于蒙田,称蒙田代表了他所有的精神楷模。
而蒙田说过,“谁学会了死亡,谁就不再有被奴役的心灵,就能无视一切束缚和强制。”在最后的时刻,茨威格保持了他作为一个欧洲人的优雅,保持了内心的自由,足以让他的欧洲和整个世界永久怀念。
十二年前,我接受台湾城邦旗下出版社委托翻译茨威格的这部作品,同年在台湾出版。去年,友人希望再次出版这部译稿,我于是翻出旧稿,予以修订,再次将它从头到尾地看了一遍。也许是年龄和阅历都有所增长的关系,这一次,茨威格的回忆在我心中引起更多思考。字里行间,我试图将他的时代和我的时代相连。
我们积累的各种人类经验,无论进步还是倒退,都已远远超越了一百年前的人。虽然越来越多人看待世界的视角已不再受限于国家和民族主义,但在人心深处,狭隘与宽容之间的较量何曾停止。当别处有人在死去,我们是否还会心有戚戚?面对蛊惑,我们是否还有可能陷入群体的歇斯底里?前方的路,会不会再次从负面完全颠覆已有的生存经验?在特洛伊讥讽过卡桑德拉,在耶路撒冷嘲笑过耶利米的人,我们还会不会随声附和他们?
1915年,罗曼·罗兰在给茨威格的一封信中,充满理想地描述了战后人类应有的共同事业,“……那会是一件超越所有政治和艺术规划的伟大事业……一座建立在所有教堂之上的教堂……一个伟岸的信仰时代将要开启。”在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眼中,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仰”——那连接人与人的东西。二十一世纪的我们,也许还很有必要记起这古典的“信仰”,保存好那连接你我的东西。
[1]①引自舒昌善译《蒙田》。
……
总序张炯
前言/1
太平盛世/1
上个世纪的学校/29
情窦初开/67
人生大学/91
巴黎,永远青春的都市/127
通向自我的曲折道路/163
走出欧洲/183
欧洲的光芒与阴影/199
一九一四年战争的最初时日/223
为精神团结而斗争/247
在欧洲的心脏/265
重返奥地利/293
重返世界/317
日落西山/340
希特勒上台/374
和平的垂死挣扎/406
译后记/456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种巨大转变的见证人,每个人都迫不得已成了见证人。
——汉娜.鄂兰
★在阅读《昨日世界》的过程中,我被书中如此多被遮蔽的事实震惊和触动。茨威格书中有许多对自己生活片段的描述,有一些我们也用在了电影中。在读到《昨日世界》之前,我们其实对他生活的时代所知甚少。
――韦斯.安德森,《布达佩斯大饭店》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