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早期欧洲
那么,谈论现代早期政治思想到底意味着什么?“现代”国家的成长,及其由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民族边界构成的堑壕,无疑是现代早期的一个核心特征,而且它以某种方式影响了那些进入其力场(Field Force)的所有形式的政治组织。但是,作为本书主题的西方政治思想正典,在那个时期也同样受到了形形色色的政治形式的塑造:意大利城市国家、让人眼花缭乱的德意志管辖区、尼德兰商业共和国,更不用说还有神圣罗马帝国,它既自觉地返回古代帝国又致力于成为民族国家(尽管最终失败),又与其他世俗的和教会的主权主张者处于持续的紧张关系之中。现代早期的概念不仅包含现代国家或现代经济的崭露头角,还包含文化和智识的发展,后者起源于各不相同的,并不具有明显现代特征的社会政治形式,例如意大利城市国家,文艺复兴在那里开花结果,或萨克森选侯领地,至少据历史传统说法,马丁·路德在那里发起宗教改革。
这些情形大相径庭,不仅体现在其政治形式上,而且体现在公共权力、私有财产权和生产阶级之间特定的相互作用上。这些差别将造成各具特色的政治话语传统。即使当某个时刻,城市国家与君主国在神圣罗马帝国薄弱的统治下偶尔结合在一起时(也就是德意志人与西班牙人、意大利人与荷兰人的情况),情形依然如此。当然,意大利人与德意志人,西班牙人与荷兰人,就此而言还有英格兰人与法兰西人,都分享着一份共同的文化遗产;而且我们论述的时代始于特殊的文化统一体的某一时刻,该文化统一体表现为:联合起西欧学者们的拉丁语,整套基督教神学,复兴的希腊古典政治哲学,由欧洲人文主义构成的“文人共同体”。然而,这个共同的智识词汇表只是使各民族传统的多样性更加突出。西方政治理论所承袭的语言在适应不同的背景环境时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灵活性;每一种特殊的历史形式都提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问题,同一话语传统被调动起来,不仅是为了给出不同的答案,而且是为了回应不同的问题。
尽管存在着这些差异,谈论“现代早期欧洲”是否仍有意义?或者更具体地说,设想西欧是一个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实体,在本书所覆盖的年代里经历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历史发展模式,是否有意义?后面我们将更多强调民族发展的特殊性,但是眼下让我们考虑共同的基础。
在这部政治思想的社会史第一卷中,我曾指出,在其所有变化形式中,西方政治理论都是由两种权力来源,即国家与私有财产权之间的显著张力塑造的。所有的“高等”文明当然都有国家,有些还有复杂的私有财产制度;但是,起源于古希腊罗马尤其是西罗马帝国的,在后来的西欧出现的发展,把财产权当作一个独特的权力中心,赋予了其相对于国家的异乎寻常的自主地位。
例如,可以考虑一下罗马帝国与早期中华帝国的对比。在中国,一个强大的国家通过挫败大的贵族家族并阻止他们占有新征服的领土,任命中央官员管理新征服的领土,来确立自己的权力。?同时,农民处在国家的直接掌控下,国家保留农民财产作为税收和兵役的一个来源,并确保土地占有的碎片化。相形之下,罗马并未依靠强大的国家就实现了帝国扩张,它由非职业人员统治,在一个小城邦的最小政府中实行土地贵族的寡头政治。尽管农民是公民共同体的一部分,他们仍从属于有产阶级;帝国扩张后,由于要征召农民士兵远离家乡服兵役,致使许多农民的土地被剥夺。土地日益集中在贵族手中,(至少在罗马时期的意大利)它大多由奴隶耕作。当共和国被帝国及其官职结构取代后,土地贵族仍继续聚敛庞大财产。在中国,巨大财富一般源于中央政府的官职,然而在罗马帝国,土地仍是唯一稳定可靠的财富来源。即使在其鼎盛时期,相较于中国,帝国也是“统治薄弱”的,主要通过地方贵族的巨大网络来实施管理。
就我们所知,罗马帝国乃是强大帝国和强大私有财产权相结合的首例。这种强有力的,尽管有时并不轻松的合作关系,在罗马的“统治权”和“所有权”概念中得到表达。当罗马的“所有权”概念应用于私有财产时,它无比清晰地表达了私人的、排他的、个体的所有权及其所包含的一切权力的观念,而“统治权”则界定了一种附属于特定的民政长官,最终附属于皇帝本人的发号施令的权利。在西方法律政治思想史上,私有财产权和公共司法权并非总是如此泾渭分明,然而,罗马人在区分国家的公共权力和财产的私人权力方面确实开辟了新天地——不仅在理论上也在实践上。在中国,国家和劳动被国家占有的农民之间形成了一种直接的关系,在罗马,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基本关系并不存在于统治者和臣民之间,而是存在于地主和某种从属于他的劳动者(可以是奴隶,也可以是作为租户和佃农而被剥削的农民)之间。帝国解体后所剩下的就是这种基本关系,它幸存了下来并成为后几世纪的社会秩序基础。
国家和强大的私有财产权两个权力极点的存在,再加上依靠有产阶级,很大程度上实施地方自治的帝国统治模式,即使在罗马帝国中也造成了最高权力的碎片化趋势。最终,碎片化趋势占了上风,留下了一个使农民束缚于地主的人身依附网络。当帝国解体,墨洛温王国、加洛林帝国及后继国家进行过几次权力再度集中化的尝试后,土地贵族的自治权开始在所谓的公共权力私有化、封建“主权分割化”?过程中自我伸张,随之而来的是公共职能被下放给地方领主和其他各种独立权力。这种下放的公共权力同时是一种占有权,即支配生产阶级的劳动,(尤其是从虽拥有土地,但在政治和法律上臣属于领主并为其劳动的农民那里)以租金或实物形式占有其产出的权力。由于找不到更好的术语,我们只得将封建主义或“封建社会”这个充满争议的概念,用于指称这种西方特有的主权分割化,它以具有历史独特性的方式赋予私有财产权以公共权力的性质。就我们的目的而言,“中世纪”时期大致可以被这种独特构造的统治地位及其衰落所标识。
这种封建分割化以多种形式和不同程度存在。封建君权在有些地方会比其他地方更强大一些;部分欧洲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更高权威亦即神圣罗马帝国或教皇的支配。但是,政治分割化甚至影响到那些并不符合典型封建制度的欧洲政治实体。例如意大利,它被称为欧洲封建主义的“薄弱环节”,因为这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城市贵族,在北方尤为明显,这与其他地方的土地领主阶级形成对比。然而,不仅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国家具有自身的碎片化统治,这可被称为一种城市封建主义,而且如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之所以能成为大商业中心,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们在碎片化的封建秩序中作为贸易纽带而履行着至关重要的职能。
无论我们是否选择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之间划出界限,至15世纪末,我们都能确认一种新的政治权力格局,以及财产权同有别于封建分割化主权的国家之间的新关系。当然,领主和自治的法人团体仍占据着突出位置,但是,正在进行中央集权的君主制(特别是在英格兰、法兰西和伊比利亚半岛)现在登上了舞台中心,甚至在对不同的政治形式,如意大利城市国家和德意志公国施加一种新的政治动力。例如,尽管意大利北部曾是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之间的竞技场,对城市国家自治权的挑战却日益来自法兰西和西班牙这样的君主国的领土野心。
关于封建主义的衰落,已经有许多解释。一些历史学家主张,正如封建主义的出现是由贸易萎缩所标示的,或者甚至是由其所导致的,商业扩张和货币经济的增长则不可避免地使封建主义寿终正寝;其他人却言之凿凿地指出,贸易和货币是封建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内在地敌对于它。封建主义的衰落常常被归因于黑死病(14世纪40年代影响西欧的流行病)期间的人口骤减;还有人认为,人口骤减使农民在与需要劳动力的领主谈判时获得一种优势,此时领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转变。一些历史学家指出,农民可能还有另一种谈判优势,即商业扩张过程中城市中心的增长带来的逃生路线。那时,领主试图重新强加并强化农民的依附地位,由此激起了各种各样的人民起义,而且,尽管西方的起义被成功镇压,封建秩序实际上却呜呼
哀哉了。
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可以归因于土地贵族对于一种足以防范叛乱威胁、维护秩序的更强大中央权力的需求,或者(也可能同时)可以归因于封建君主感受到了巩固自己地位的强大压力,因为来自农民的收入变得更加不稳定,君主与地主之间就农民劳动力的使用展开的竞争也更加激烈。当贵族的斗争演变成雄心勃勃的领土国家之间的战争时,压力变得更加巨大,如百年战争中发生的最明显的事情那样,它起初是一场围绕法兰西君权的王朝斗争,后来则变成了法兰西和英格兰围绕领土边界问题的战斗。由于不断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它深深侵入欧洲并控制着东西方贸易路线)的商业挑战和地缘政治挑战,巩固中央统治的领土国家的动机得到进一步强化。
这些因素无论单个还是所有都可能是重要的,但这不是故事的全部。商业扩张、瘟疫、人口变化、农民起义和王朝斗争,这些在欧洲的不同地方都发生过。我们甚至可以承认,作为一种非常普通的动因,它们都在封建主义的衰落中发挥了作用。但是,抛开“诸封建主义”的多样性不说,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结果;使封建秩序让位的“转变”也远非一种。例如,西欧的农奴制终结了,而东欧却亲历了所谓的“二次奴役”。即使在我们主要关注的西欧,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也截然不同,例如在英格兰就大不同于在法兰西;这些差异伴随着不同的国家形成路径。在君主与异常团结的贵族阶层合作发展的英格兰,领主掌握了最好的土地,包括因人口锐减而被闲置的地产。在法兰西,君主国巩固了一个贵族家族的统治而反对其敌手,它帮助保证了农民仍占有绝大多数土地,以此作为中央集权国家一个关键的税收来源。
在这些不同的背景下,商业扩张也具有不同的影响。所有主要的西欧国家,更不用说经济高度发达的亚洲和阿拉伯穆斯林帝国,都深入参与了国内和国际贸易。但是,只有在英格兰,一种独特的资本主义“商业社会”“自发地”出现了,并产生了一种与众不同,甚至在其他最商业化的社会中也找不到的历史动力。?当资本主义在英格兰出现时,它并不单纯是更多的贸易、更广阔的商业网络,即不单纯是性质不变的数量增加。“资本主义的兴起”不能被仅仅解释成一个量变过程,即接近某个临界量的“商业化”。实际上,当英格兰的经济发展开始一种独特转向,产生了某种有别于传统商业模式,即古老的转让获利形式或“贱买贵卖”的东西时,它还远不是欧洲主要的商业势力。诞生于农村的英格兰资本主义造就了一种新型社会,以及一种独特地由竞争性生产,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利润最大化和持续资本积累的强制力所驱动的经济。当欧洲其他经济体后来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时,它们很大程度上是在回应英格兰资本主义带来的军事和商业压力。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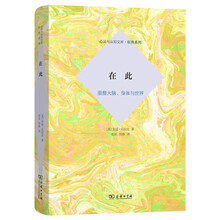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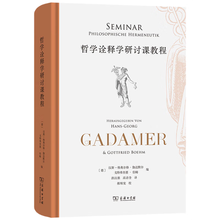



——《泰晤士报》
这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学科分析,伍德成功地将理论整合到历史的变迁中。观点清晰,文笔流畅,是任何一位想要以新视角理解政治理论史的读者的必读书。
——谢尔登·沃林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荣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