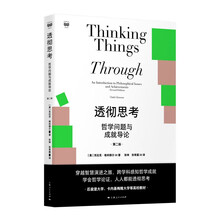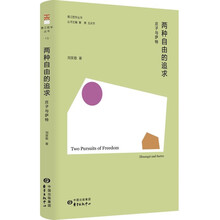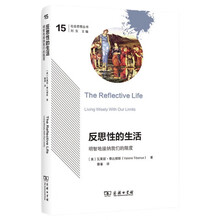伯林:跨文化的狐狸<br /> 刘东(清华大学)<br /> 一、消极自由与当代中国<br /> 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过去以后,正是鉴于来自欧陆的历史决定论和价值一元论已给当代中国造成了空前的灾难,也是鉴于这场“空前”却未必“绝后”的灾难的浓重阴影,人们便不能不向一个勇敢的先觉者表示他们迟到的敬意,而这位思想的英雄就是顾准,——他当年在巨大的思想压力下,最早领悟到了英美经验主义思想的魅力:<br /> 这就可以谈谈终极目的了。1789年、1917年,这股力量所以强有力,一方面因为它抓住了时代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它设定终极目的。而终极目的,则是基督教的传统:基督教的宗教部分,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1000年,基督要复活,地上要建立起千年的王国——一句话,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基督教的哲学部分,设定了一个“至善”的目标。共产主义是这种“至善”的实现。要使运动强大有力,这种终极目的是需要的,所以,当伯恩施坦回到康德,即回到经验主义,说“运动就是一切,终极目的是无所谓的”时候,他破坏了这面飘扬的旗帜,理所当然地要成为修正主义。……<br /> 说过这一段话,民主这个问题似乎也好解决一些了。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反之,如果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标,相信相互激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他就会相信,无论“民主政治”会伴随许多必不可少的祸害,因为它本身和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的合法存在是相一致的,那末,它显然也是允许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br /> 显而易见,只要稍稍对比一下身在英国的以赛亚?伯林对于俄罗斯思想家赫尔岑的类似信条的概括,就可发现顾准这把对准“终极目标”的简洁明快的奥康姆剃刀,究竟是来自哪一条哲学路线:<br /> 他相信,生活的终极目标就是生命本身,每日每时都有自己的目的,而不是另一天或另一种经历的手段。他相信,那些遥远的目标是梦想,对它们的信念是一种致命的幻觉;为了遥远的目标而牺牲现在,或当下的可以预见的未来,必然会导致残酷而徒劳的人类牺牲。他相信,在与人无关的客观世界里找不到价值,价值是由人创造的,并随世代的转换而变化,但仍然约束着那些据此生活的人们;痛苦是不可避免的,而绝对可靠的知识既是不可企及的,也是不必要的。他信奉理性、科学方法、个人行动,和经由经验发现的真理;然而他倾向于怀疑,那些对普遍公式和定律、对关于人类事务的规则的信念,是一种非理性的、有时是灾难性的企图,企图摆脱生活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的多样性,逃向我们优美幻想的虚假保障之中。<br /> 接下来要说的是,就我本人的记忆所及,中国人真正较早接触到来自英伦的以赛亚?伯林的思想,那就应该是在1989年5月号的《读书》杂志上。而即使把写作和发表所需的时间都算进去,构思那些文章的时候,也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大家应当都还记得,那期杂志上的头一篇,是甘阳利用了伯林《自由四讲》的台湾版,而以“消极自由”为口号,在为某种曾经引起过普遍失望的退避态度进行辩护:<br /> 那么,“社会责任感”错了吗?“忧国忧民”不好吗?当然不是。全部的问题是在于:当你怀抱社会责任之时,当你忧国忧民之时,你与这“社会”、与这“国”和“民”是否还有某种界限?或者说,你是否还有某种作为一个“个人”所必须具有的、无论如何不能让弃的东西?一种回答是“没有”,我与社会、国家、人民是完全一体、完全同一的,我没有任何个人的东西不可以让渡、不可以放弃;另一种回答则是:“有”,我与社会、国家、人民并不是完全一体的,我有我自己的绝对独立性,我有任何时候都不能须臾让渡的东西,这就是:我的“自由”。……<br /> 五四“个性解放”所向往的“自由”说到底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艺家所标榜的“意志自由”,而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即“公民自由”。当代政治哲学一般把前者称为“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而把后者称为“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真正的“个人自由”首先强调的是“消极自由”而非“积极自由”,亦即如前所述,个人自由乃是最低原则,而非最高原则。正如自由不能被他物所替代,同样,自由也绝不妄想涵盖一切,取代一切,“自由就是自由”,不是别的。<br /> 时至今日,权且放过写作上述文字的具体动机吧。无论如何,在那个时候能向国人宣讲作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的以赛亚?伯林,还是令大家耳目一新的!虽则如今我们真正对伯林了解多了,仍会觉得那种简单的引用还是太过性急了点,并没有能真正深入到伯林本人的复杂内心。——从学理的层面来说,当时最为要害的症结是,就这么来套用所谓“消极自由”概念,来躲闪硬生生摆在面前的无可回避的社会承当,那是绝对地误用和滥用了伯林。正如我们后来所惊喜地读到的,其实以赛亚?伯林本人,反而曾经最被他同时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坚忍担当意识所震撼与吸引:<br /> 他所热爱的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和屠格涅夫使他对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且让他感受到他们身上那种毫不逊色于自然或是社会制度的征服力量。同样来自于俄国传统的还有对知识分子本质上所具备的劝诫和道德功能的认识。<br /> 再比如,作为赫尔岑的欣赏与追随者,伯林不可能没有从前者笔下读到过这样的对比性批评:<br /> 西欧人最后形成的那种孤芳自赏的个性,起先我们觉得它与众不同,继而又发现它片面单调。他们始终酬躇满志,他们的自负使我们气愤。他们从不忘记个人的得失,他们的处境一般并不顺遂,心力大多花费在生活琐事上。<br /> 我并不认为,这儿的人从来就是这样;西欧人不是处在正常的状况——他们正在退化。没有成功的革命风起云涌,没有一次能使他们脱胎换骨,然而每一次都留下了痕迹,搅乱了人的观念,于是历史的潮流顺理成章地把污浊的市民阶层推上了主要的舞台,挤走了被铲除的贵族阶层,扼杀了民间的幼苗。谢天谢地,市民精神与我们不能相容!<br /> 我们无所用心也罢,精神不够深邃,行动不够坚定也罢,教育方面太幼稚,修养方面太贵族化也罢,但是我们一方面既更懂得生活的艺术,另一方面也比西欧人单纯得多,我们不如他们那么与众不同,然而比他们更全面。我们这里有识之士不多,但这些人才华横溢,气度恢宏,决不受任何局限。<br /> 另外,再从历史判断的角度来看,那种断言五四之“阙失面”的说法,也同样是太过性急地对于一场复杂的文化热潮,贸然给出了以偏概全的总体否定。而如果对照一下具体的史实,正如我此后的个案研究所示,其实恰恰是在那场运动中,中国的文化人才第一次自觉或不自觉地,接触到了与“消极自由”相关的思想概念:<br /> 周作人对于他所投入的这场文化运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其主帅理解得还要深刻。——这方面最鲜明的例证,表现在由他领衔发起的跟“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及其精神领袖陈独秀的那场论辩上:“我们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同盟运动表示反对。”令人惊叹的是,尽管周氏在这里并未使用所谓“消极自由主义”之类的术语,但他却确凿无疑地把握到了此种主张的主要神髓,足见其天份之高!<br /> 于是也就不妨说,对于一场众说纷纭、泥沙俱下的思想热潮,给出如此整齐划一的全盘否定,这本身就相当吊诡地太过一元论了。而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验之于历史的原生态,我们原本并不难想象,五四时代既然如此开放与奔放,它在理路和取向上就必会是多元混杂的,那时候又没有什么机构去规定意识形态的“主旋律”!所以,如果不是后世沿着激进主义的逻辑去抹下革命油漆,原本就根本不存在一个被强行诠释成的、好像是铁板一块的五四。<br /> 当然,还是应当再宽容地说一句,纵然不能无视这些思想上的磕磕绊绊,可在当年那种宏大叙事占据主导的情势下,能以英国经验主义的态度去进行相应的解毒,总还是可以诱使我们对于西方哲学了解得更加全面一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甘阳当年的那篇文章,跟陈维纲较早前那篇同样发表在《读书》上的意在解构卢梭“公意”观念的文章,在思想取向上仍有异曲同工之处:<br /> 卢梭的根本错误,在于他抽掉了民主的价值基础。当他宣称多数人有权剥夺少数人的权利,宣称主权者有权迫使公民服从其所规定的“自由”时,他已经否定了人道主义原则,否定了人的本质。这样一来,构成社会主体的已不再是人,而是国家本身。国家取代人而成了目的,成了中心。<br /> 在这里,我们便接触到了卢梭社会哲学中最核心的思想——普遍道德观和国家至上主义。他所理解的人,并不是自由发展自己的主体,而是遵从某种特定道德观念的公民。这种力图将人变成某种普遍道德复制品的思想不仅反映在卢梭的学说中,而且也支配了雅各宾专政的整个实践。这种把国家当作目的,把人作为手段的理论在实践中的第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把人分为国家的有用手段、工具和对国家有害或不利的工具。它暗含的结论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应该无情地消灭后者,这样,本来是为了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革命,最后变成了维护国家,维护某种普遍道德的革命,变成了消灭人的革命!<br /> 当然相形之下,以上这番简单的引述,还只是从思想的萌芽过程,来回顾以赛亚?伯林在中国大陆的最早回声。——比及九十年代以后,一旦那些更早接触过这类思想的华裔学者纷纷漂洋来访,诸如此类的说法就更是屡见不鲜了,因为英美思想正是他们的看家本领,而且他们所擅长的这种家数,又正好可以切中当年大陆思潮的某些要害。比如,张灏在前几年也曾发表过诸如此类的访谈:<br /> 高调的民主观由卢梭开其端,然后黑格尔,然后马克思——这些人所倡导的民主自由观念,我为什么称之为高调的民主观呢?卢梭所追求的自由不是自然的自由,而是人的自由和政治上的自由,就是人生活在人群中所有的自由,他的自由观里面道德感非常充实。卢梭把人分成两个自我,一个是内心深处的“精神我”,一个是外在的“躯体我”。所谓自由以及与自由有关系的公意,不是一个普通人躯体的、感官的要求,而是每个人真正的、内在的心灵要求。所以卢梭说,“精神我”常常也就是群体的公意,“精神我”也是可以跟社会的“大我”连在一体的。换句话讲,你个人、表面、躯体的“小我”说的话常常是肤浅的,不能代表你真正的人的精神要求,而民主所要发展的,是人内在的精神的自由,这才是最珍贵的——这个东西在西方也是很重要的,就是“积极的自由”。……<br /> 高调的民主观在西方近代常常以“共和主义”为出发点,对民主思想有其重要贡献,但也有危险性。一方面,因为民主政治的现实常常与道德理想有很大的差距,容易使人失望幻灭,因而有产生民主政治逆转的危险。更重要的是,这种民主观里面时而出现一些激化的倾向,可能使政治走向权威主义甚至极权主义的道路。<br /> 另一方面,高调的民主观可能导致“民粹意识”的产生,因为它认为民主表达的是人民的公意,而人民的公意不是指构成人民全体的众多不同集团利益的协调整合,它也不代表全体个人私意的总和,而是指存乎其中又驾乎其上的道德意志——这公意既然不是反映现实社会中个人或利益集团的私意,便很容易产生一个观念:真正能体现公意的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先知型的领袖或者道德精英集团,他或他们可以代表或领导人民实现他们“真正的意志”。<br /> 众所周知,最是坚持不懈地在推广此类观点的,则又要数早年曾跟哈耶克念过书的林毓生。——也许是其性格使然,他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场合,反复地甚至不厌其烦地去伸张同一个观点。也正因为这样,我才会在一篇评议他的学术贡献的文章中,捎带着也描述了大陆的学风在经验主义思想方法的影响下,顺应着改革(而非革命)时尚而发生的丕变:<br /> 过去,由于革命意识形态的强烈排他性,大陆学者中间虽不能说没有例外(比如顾准先生的遗著《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但大体上却未能对自柏克以降的思想脉络给予应有的重视。而现在,怀德海、波兰尼、哈耶克的名字却一时间不胫而走,直有跃升为“显学”之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察觉到,至少照经验主义的观点来看:向着某个理想中的历史终点的不断躁进,难保不给历史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相反,对于传统活力的保守与开发,却可能是整个社会稳步变革的基础。<br /> 只可惜,最为讽刺和令人失望的是,果真到了这个时候,被看作现代政治不二法门的消极自由和低调民主,却不仅没有显出什么预期的神效,反而招惹或鼓励出了更多的问题。——说白了,在这个万马齐喑的物质主义时代,正因为太过“消极”和太过“低调”,没有足够的超出一己之私的民气可用,也磨合不出原本必不可少的公民文化,人们眼下根本就是“消极而不自由,低调而不民主”。甚至,恰好是对应着这种时髦的论调,整个社会都因为其成员基本龟缩在小我之中,而显得公共空间严重发育不全:<br /> 虽然从一时看来,这种历久弥新的杨朱主义确乎在支持着当代中国的发展,因为对于私利和私欲的追逐与满足差不多已经可以说是这场现代化运动的唯一心理动机,然而由长远视之,这种并无精神向度的现世主义的紧紧封闭的“小我”,毕竟又在规定着当代中国发展的局限,因为整个社会终须依靠各个成员之超出自身的祈求才能得到良好的发育。<br /> 当然,谁对这些微妙的发展也不会是先知先觉。不过凑巧极了,刚好就在1989年5月号的《读书》杂志上,而且还是紧挨着甘阳的那篇文章,恰恰也发表了我本人于一夜间急就的《衰朽政治中的自由知识分子》。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深信“执两用中”之智慧的我,却是向来都不喜欢剑走偏锋,尤其不愿意先去走这边的偏锋、好留着那边再去走对面的偏锋——当然也是受到了胡适案例的牵引——所以,尽管同样处在那场暴风雨的前夜,自己在谈论自由主义思潮时,却并未流露出一丁点儿自信,倒是对历史充满了悲剧性的预感:<br /> 或许并非很自觉地,胡适借此又帮助中国刚刚形成的知识分子们创造了一种新的传统——自由主义传统。这种传统的一般特点是:总是号召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但又总是注意保持个人的独立地位;总是珍重自己对于政治的发言权,但又总是超乎政治之外地不愿付出卷入其间的代价;总是强调个人的独立判断能力,但又总是愿意以社会共同利益为准;总是批评社会的种种弊端,但又总是保持一种温和节制的态度;总是和现存的政治组织离心离德,但又总是尊重和利用现行的法律秩序;总是要求社会制度的不断改革进化,但又总是不赞成使用激进的手段;总是祈望人类历史的不断进化,但又总是渴望看到这种进步能够取道于缓慢的调整;总是在内心深处对人的生存状态怀有强烈的价值理想,但又总是倾向于在现实层面采取谨慎的经验主义方法……它在小心翼翼地、左右为难地维护着个人的自由。它的优点同时也就是它的弱点。……<br /> 他的悲剧就在于:在一个衰朽的政治中,偏偏要去做一个只有在正常有序的政治中才能发挥作用的自由知识分子。他认识到了自己在一个合乎理性的民主制度下应该扮演的角色,却看不出自己在一个不合理性的专制制度下应该何适何从。他过多地寄希望于舆论的监督作用,却没有想到在一个不尊重公意的政权眼中舆论是可以置之不理的。<br /> 众所周知,对于自由知识分子的这种局限性,胡适很早以前就曾借着丁文江之口,非常突出和反讽地表白过:<br /> 然而在君(即丁文江——引者)究竟是英国自由教育的产儿,他的科学训练使他不能相信一切破坏的革命方式。他曾说:我们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br /> 其实他的意思是要说,我们是来救火的,不是来放火的。照他的教育训练看来, 用暴力的革命总不免是“放火”,更不免要容纳无数“趁火打劫”的人。所以他只能期待“少数里的少数,优秀里的优秀”起来担负改良政治的责任,而不能提倡那放火式的大革命。<br /> 然而民国十五六年之间,放火式的革命到底来了,并且风靡了全国。在那个革命大潮流里,改良主义者的丁在君当然成了罪人了。到那个时代,在君曾对我说:“许子将说曹孟德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我们这班人恐怕只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br /> 平心而论,也正是鉴于这样的消极社会现状,以及由此刺激起来的复杂问题意识,才使我们至少可以从阅读心态上去理解,为什么重新站到了过激立场上的崔之元,后来又要在同一本《读书》杂志上,转而去为刚被清算过的卢梭翻案。——说得更具体点儿,我们至少借着这种回溯了解到了,无论崔之元的论述有没有历史文本根据,陈维纲当年那种干净利落的卢梭批判,都还是把问题给过于简化处理了。<br /> 本文针对对卢梭的误解,进行拨乱反正。论证了卢梭的“公意”理论来自他对“个人意志自由”的彻底的逻辑展开。这是卢梭对现代民主理论的最大贡献,即将个人自由与作为生活基础的人民主权内在地联系起来——彻底的自由主义必须是民主的自由主义。<br /> 一旦我们从个人意志自由角度去理解卢梭,围绕他的“公意”理论的误解就烟消云散了。“公意”不仅不排除个人自由,而且以保证每个人的自由权利为基本目的,因为这是每个公民共享的“共同利益”之所在。卢梭所希望的自由,比“在法律之内的自由”更彻底,他要求公民相对于法律本身的自由,即法律必须反映每个公民共享的“公意”,否则法律就变成了王权、上帝或社会中的“特殊利益”的产物,公民在服从法律时就不象服从自己的自由意志一样了。<br /> 不过平心而论,同此后很快就陡然急转的其他人一样,上面的论述也还是留有其本身的思想缺陷。而在十几年过后,此间的要害也早已显现无遗:一方面,如果在惊喜地读过伯林之后,有些学者又转而看出了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观念——特别是所谓“消极自由”概念——的局限,从而不再像以往所表现的那样,一见哪种西方学说就把它当成万应宝丹,那当然可以算得上思想的一大进境;可在另一方面,要是他们只是因为发现了这种思想的局限性——而且主要是嫌它像王国维说的那样“可爱而不可信”——就马上哗啦啦地倒向了这种思想的反面,全然不顾这个“反面”在当代中国的尚未远去的可怕阴影,那就只能陷入极度恶性的原地打转了。<br /> 细细想来,即使在如此深重的历史灾难之后,还会有人再次转向身后不远的深渊,其间的诱惑只怕也不是纯属偶然的,或者也有其深不可测的历史文化根源。——如果再把眼界放得更宽,得以发现不光是在中国大陆,而且甚至是在整个儒家或汉语文化圈,在香港、台湾乃至日本、韩国的哲学系,隶属于欧陆的德国哲学都几乎被当成了唯一的哲学,而最后由一位德国哲学家所写的最后一本书,也都几乎被当成了最终的真理或真理的代称,我们就会被一种深不可测的“魔咒”给惊呆了!说真的,我私下里常会为这件蹊跷事而默默出神:来自欧陆、主要是德国的哲学话语,到底何以在这块被移植过来的土地上,一变而为主导性的思想话语,取代了原有的主流意识形态,从而在深层支撑了共产主义运动,这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的“谜中之谜”。<br /> 这问题需要更久长的寻思与论证。不过在眼下,至少可以先对“德国话语在中国的上升”,从一个侧面提出尝试性的解释——这大概是跟当时刚刚脱胎的雏形知识分子的特定心态有关:这些人乍从士大夫的身份转变过来,由此作为一种寻求全面发展的文化人,他们对于政治学说所表现出的渴望,与其说是在繁琐的操作层面,不如说是在激烈的玄谈层面,与其说是在散文化的科层里,不如说是在充满诗兴的快意中。而这样一来,简约素朴、一清二爽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就宛如一杯太过平淡的乏味白水,缺乏深奥的思辨性和飞扬的文学性,不能匹配他们诗意的想象力与热情。就此还可以提出一个佐证:或许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现在仍然可以从身边看到,最容易摇身一变和急速左转的,特别是其中最显得意气用事的急先锋,尽管敢于从进城民工谈到亚非拉美,又从古代思想谈到世界经济,却往往都是出身于文学系的,这同样不会是纯属偶然的!<br /> 那都是不堪回首的后话了。——如果再把心情转回到当时,仍然应当公正地再说一遍:还是应当感谢对于伯林“消极自由”概念的及早传播,它赶在国人至少还比较愿意读书的那个年代,及早就在中文语境里造成了针对伯林的难得的阅读传统。以至于到了后来,即使在全民阅读率普遍下降的今天,这个阅读传统都还能帮助保住印数的底线,支撑着我们在图书市场的配合下,在由我主编的《人文与社会译丛》里,几乎把伯林的主要著作都给悉数译成了中文,从而也总算小小地成就了一项事业。<br />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