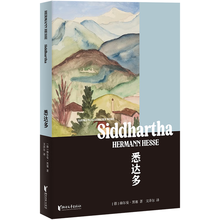厚重的云层彻夜笼罩柏林,此时晨光正勉为其难地露出。在城市的西边外围,轻盈的雨水恍如烟雾般飘荡在哈维尔湖的湖面。
天水合为灰茫茫的一片,直到对岸才刻划出一条黑色的界线。那里静悄悄的。没有任何灯火。
札菲尔·马栩,柏林刑事警察队——简称刑警——的重案调查员,从他的大众牌国民车爬出来,对着雨水偏了偏头。他是这种雨的鉴识专家。他知道它的滋味和气味。这是从北方过来的波罗的海雨水,冷冽,包含海洋的味道,而且带着浓烈的盐分。一霎时,他好像又回到了二十年前,在U潜艇的潜望塔中,熄灭灯光,从威廉港出航,滑进一片黑暗。
他看看手表。才刚过早上七点钟。
他前方的路边停了三辆车。其中两辆的乘客在驾驶座上睡觉。第三辆是一辆普通警察——即一般德国人所称的“普警”——的巡逻车。车里空无一人。从打开的车窗里,传出断断续续含糊不清的无线电通话杂音,在潮湿的空气里十分刺耳。车顶上的旋转警灯照亮了路旁的树林:闪烁一阵又一阵的蓝黑,蓝黑,蓝黑。
马栩放眼寻找普警巡逻人员,看见他们站在湖边一棵湿答答的桦树下避雨。他们脚下的泥巴里隐约有个苍白的东西。旁边一条木头上,坐了一名穿着黑色田径运动服的年轻人,胸口袋上有一个党卫军的SS徽章。他俯背向前,两只手肘靠在膝盖上,双手抱着头的两侧——一副苦恼的模样。
马栩吸下最后一口香烟,将烟蒂一掷。烟蒂在湿漉的路面上嘶一声熄灭。
他走过去,一名警员举起手臂敬礼。
“希特勒万岁!”
马栩没理会他,一脚深一脚浅地走下泥泞的湖岸去查看尸体。
那是一具老人的尸体——冰冷、肥胖、光秃,而且惊人的自皙。从一段距离以外看去,有可能被误认为是抛弃在泥巴里的一具雪花石膏雕像。粘了泥土的尸体,面朝上,半身横陈在水面外,两臂大张,头歪向一边。一只眼睛闭得死紧,另一只半张半阖地睥睨着混沌的天空。
“你叫什么名字,下士?”马栩有一口轻柔的声音。他眼睛没有离开尸体,问那名行举手礼的普警。
“瓦特卡,少校阁下。”
“少校”是党卫军的一个头衔,和德国武装防卫部队的军阶相当,那个瓦特卡——虽然疲惫不堪而且浑身湿透——似乎迫不及待要展现他的敬意。马栩不用仔细观察,也知道他是哪种类型的人:三度申请转入刑警队,全部被拒绝;有一个为元首生产了一足球队儿女的尽职妻子;一个月薪水二百马克;一种怀抱着希望的生活。
“嗯,瓦特卡,”马栩又用那轻柔的声音说,“他是在什么时间被发现的?”
“才一个钟头以前,长官。我们在尼克拉的巡逻正要收班时接到呼叫。第一优先事件。不到五分钟就赶到。”
“是谁发现他的?”
瓦特卡举起大拇指对肩畔的方向指了指。
穿田径服的年轻人站起来。他看起来不超过十八岁。头发修剪得非常短贴,淡棕色的轻薄发根下,露出粉红色的头皮。马栩注意到他刻意避过尸体。 “你叫什么名字?”
“党卫军一等兵赫曼·约斯特,长官。”他讲话有撒克逊口音——态度紧张、心神不定、急于取悦,“就读于席拉希坦的瑟普·戴特利希训练学院。”马栩知道这个学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起来的水泥兼柏油畸形建筑,位于哈维尔湖的南边。“我大多数早晨都在这一带跑步。天色还很昏暗。起初我以为是一只天鹅,”他无助地补上一句。
瓦特卡哼了一声,脸上露出不屑。一个党卫军军校的学生,竟然害怕一个已经死了的老头子!难怪乌拉尔山战役拖拖拉拉永远打不完。
“有没有看到其他什么人,约斯特?”马栩用叔叔一般慈蔼的口气对他讲话。
“没有,长官。半公里外的野餐区有一个电话亭。我打了电话,然后回到这里等,直到警察抵达。路上都没有看到任何人影。”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