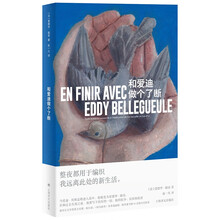首部描写“俄罗斯新贵”生活的半自传性小说,2005年俄罗斯畅销小说,入围当年俄罗斯国家畅销书奖提名。
它是充满反讽的“真正的当代文学”,还是满足普通人窥探欲的通俗小说?对该书的争论成为当年俄罗斯文坛的重大事件。
卢布廖夫卡,坐落于莫斯科西郊森林中偌大的别墅区,高墙上赫然写着“闲人勿进”。住在这里头的可不足猛禽野兽,而足当今俄罗斯的政要和富豪。《偶然》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我走出卧室,准备对丈夫说我酝酿了很久的话,这时候我的手在颤抖。我与他之间,有九年的共同生活,有八岁大的女儿,还有一个妙龄的金发女郎,一个星期前,我在餐厅撞见他和她在一起。
“我们还是分开住吧。”我望着他的眼睛,说得很平静。
“好吧。”他漠然地点了下头。我转身回卧室睡觉。
这种嫉妒所带来的心痛,您何时可曾体验过?如果我是但丁,我会把这种酷刑排在热油锅的后面。或者干脆取而代之。
我撕碎了他所有的照片。
第二天,我又把它们都粘好了。
正在我心力交瘁几近崩溃之时,电话铃响了起来。
一个冷冰冰的男性嗓音在电话另一端叫着我的名字和父称。然后这个声音告诉我,我的丈夫死了。五处枪伤。其中两处击中要害——肺部和头部。就在我们莫斯科住所的院子里……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