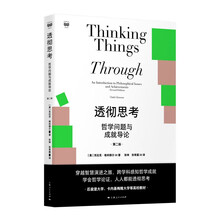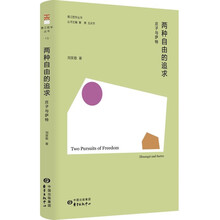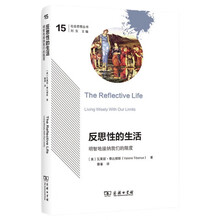严格说来,施莱尔马赫与朱子在主观面与客观面的对比其实有着某种程度的不对称:此不对称倒不是强调朱子论《论语》的心灵与文本两面中,缺乏施莱尔马赫之由心理与语言而建立的循环操作(但须指出的是,朱子在《读书法》与解读《孟子》中,也初步涉及了语言层面的脉络性与循环性),而是首先在于“语法成素”侧面。
简单来看,施莱尔马赫的“语法侧面”谈的就是语言。语言以及充分的语言“知识”是理解文本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与朱子就不同文本的相互解释以及这些解释中所涉及的“理一分殊”原则,确实有其论述上的差异。然而正是因为这种不对称性带来的差异,突显了朱子在经文互解中所关连到的“理”脉络(即“理一分殊”纯然作为文本的诠释“原则”)其实欠缺一语言的“知识脉络”。施莱尔马赫把“语言”面向极度延伸到“时间”范畴(语言的历史既成与未来发展),并由此而拓展语言知识。面对这样的拓展与延伸,朱子“理一分殊”的难题正如张岜将的研究所指出的,缺乏对经典彼时语言之原则性的重视。“理一分殊”建构的是义理脉络而非文理脉络。文理脉络要求的是意义与意旨,因而需要更进一步要求对文字知识的训诂与考察,从而以一较为充分而完整的语言知识作为意义解释的基础.才可进而顺畅义理脉络(朱子确有这方面的大量说明,但并不在理一分殊原则的范围内)。相反来说,缺乏语言知识,文理即不甚可靠,不可靠的文理无法支持大规模的、义理之间的整合。如果这种整合不可行,“经文互解”即不可行。
其次,施莱尔马赫的“心理侧面”之操作,乃是要求理解与掌握作者的内在生命与外在生命的知识,并由此知识的“生命强度”转而要求读者与原作者之间进行一种“生命的等同化”,同情、共感与分享皆由此而来。此大致上仍类同于朱子之以心比心强调诸主体之间的相互比配--尽管此诸理解主体需要进一步跨越到道德生命,正如施莱尔马赫的心理主体也需要扩张到历史生命。不过以心比心的范围在于文本,心理的重构(特别是外在生命)则往往广至整个时代与文化。这种范围的大小,同时也决定了朱子之诠释主体之间的沟通限度(文理脉络之不足),而须转向以义理脉络来弥合这种限度。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