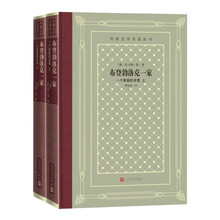在1992年2月,我知道柏林墙倒塌两年后,东德守墙的卫兵因格·亨里奇受到了审判。在柏林墙轰然倒塌前,二十七岁的他曾射杀了一位企图翻墙而过的二十岁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从1960到1990年的短短三十年间,只有空气、飞鸟可以穿越的“隔离人民的墙”的柏林墙下,先后有三百位东德欲越墙逃亡者被无情的子弹射杀,成为墙下的冤魂。
仅仅是为执行上峰的命令么?亨里奇的律师辩称这些卫兵的天职就是服从,罪当不在卫兵个人。然而,法官西奥多·赛德尔却在一种人性的高度断然反驳:“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是啊,李钟岳也是活在体制内的满清的官员,但他守住了自己的良知,他没有把体制的命令、上司的命令当做作恶的借口。李钟岳知道自己放在首位的是一个人,然后才是满清的县令。虽然李钟岳背负体制的重压,但李钟岳也有自己的选择,以自杀来抗击恶政,来说明良知的正当性。李钟岳死了,他的牌位曾被人们放到秋瑾的纪念堂配享,就是人们和历史对他的最好认可和公允的评价。李钟岳也是“抬高一厘米”的人,在面对恶政时不忘抵抗与自救,是“人类良知的一刹那”,这一厘米是高于人顶的一厘米,是长在体制之上的一厘米,也是见证人类良知的一厘米。
你问,李钟岳比晚清的那些官吏多出些什么?我说,只多出一厘米!
而对于秋瑾来说,秋瑾比晚清的知识分子多出了些什么?我说,她比女人多出了男人气,比男人多出了英雄气。我知道对当求仁得仁的机会到来的时候,秋瑾不能不死,无论对革命党,无论对满清,秋瑾必须死。我想到了鲁迅先生,其实在乌篷船欺乃的绍兴,在有师爷传统的绍兴,秋瑾的家和鲁迅、徐锡麟的家只是隔了几条胡同、几条水,物理的距离很近,又有着留日的背景且重叠,也可称作同学的。但秋瑾和鲁迅的性格却是两样,一是赤裸的火的赤焰,一是冰裹着的冰与火的赤焰。鲁迅对战士和革命家的名号一向是警惕的,1927年,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热血的青年开欢迎会,鲁迅却兜头泼了冷水,“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土’‘革命家’”。鲁迅的思想深处,对一些空头的名号是警惕的,无论空头的文学家、革命家,还是所谓的战士。这和秋瑾不同,“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土’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