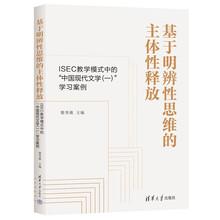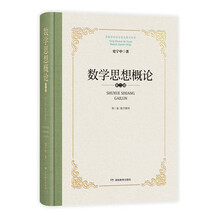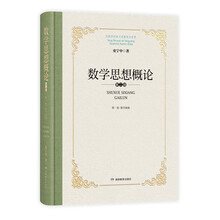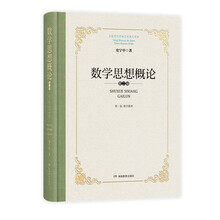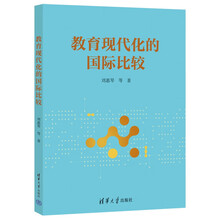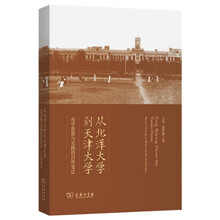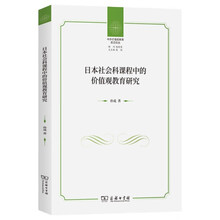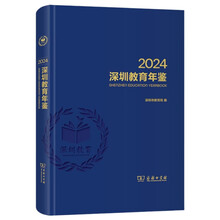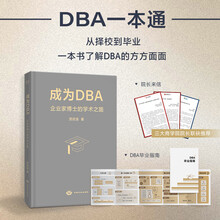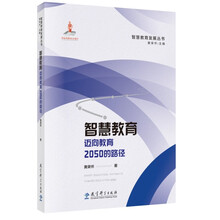“学生第一”还是“学生第二”?课堂上教师究竟应该努力维护“师生平等”还是努力做着“平等中的首席”?苏格拉底的对话是否平等?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是否可能?如果说师生之间更有效的对话是隐含了某种“不平等的原初状态”的对话,那么这种状态是否威胁着教育的自由和平等?伯林说:“堵塞他所有去路,而只留一扇门”,那么,当有人宣称:“我比他们自己更明白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的时候,我该如何看待“他是一个人,他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
1.任何一种主义或许都是以偏救偏。重要的也许不是它说出了什么是绝对正确的,而是提醒了被忽略的,伯林的理论可能也是如此。
查尔斯·泰勒在辩驳伯林两种自由的分割时,引进了“重要性”概念:任何自由都涉及动机,动机关联何者“更重要”。“有多少扇门向我敞开”,是自由的定量判断,是个“机会概念”。“为什么要自由”是定性判断。即使是“不受阻碍的”消极自由,也有一个某事不受阻碍“很重要”的理由。否则,他举例,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大街上的红绿灯很少,伦敦大街上则很多(对大多数人的大量日常自由的量,意味着更多的限制)。那么,能否因此得出,阿尔巴尼亚比英国自由?一般不会。英国的选举权,可能许多英国人几年才使用一次,有人根本不使用。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