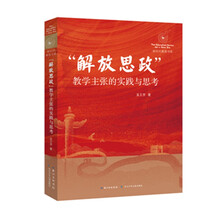为什么我把自己有关教育的论述统称为“摸不着门”?是天太黑还是门太高?是我们身在此门中还是身在此门外?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十多年前开始,我们好多做文学研究的,不约而同地把关注点移向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上。我想这可能是学术的自然升华吧。
我在北大做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大众文学、通俗文学的,我早说过这样一个观点,中国主要落后在中间层次上,落后在大众文化上,落后在教育上。我跟钱理群、曹文轩等老师说,咱们现在文学研究的许多成果,有多少转化到中学了呢?几乎没有。
我1990年的时候到中学当老师,看到语文教参,有点吃惊,那上面的观点和我们在大学校园里所谈论的相比,好像是在两个世界里。鲁迅在《拿来主义》里提到了尼采,可《拿来主义》的教参仍然把尼采说成是德国资产阶级反动哲学家,脱节是如此之大,脱节至少10年以上啊!而当下的中学语文界采用的则是我们上个世纪90年代的说法,总是落后有10年左右,存在着巨大的对话空间。主要原因就是很多学术成果不能及时转化为教育成果,这些学术成果成了我们这些学者的自说自话,成了学者之间的对话。其实鲁迅那个时代的思想高度我们可能很久都赶不上,但就说他们自身吧,也没有很好地传播出去,只是一些大学的学生学者写文章互相给对方看,《新潮》、《每周评论》的那些人,也就是胡适、鲁迅他们之间在互相启蒙,可老百姓还是那些老百姓,与启蒙无关。
从1917年到1937年启蒙了有20年吧,可日本人来了还是有那么多人去当汉奸,其中很多“底层汉奸”倒不是为了功名利禄,绝大部分是因为愚昧,他们觉得人家日本人这么大老远地来到这里不容易,晚上找不着路,打个灯笼给人家带带路做做好事,打完灯笼我回家睡觉去,也不知道要钱。当时很多老百姓是无意识地做了汉奸的事,他们没有国家观念,鲁迅所说的什么国民性改造,改造民族灵魂之类,根本听都没听说过。
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有强烈的救国救亡的意识。我认为救国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革命,一种是教育。革命不能总搞,搞一回两回就行了,代价太大。归根结底还得靠教育。教育事业发展到今天,成就是巨大的,代价也不小。应试教育的弊端越来越凸现出来,教育最后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近年来独木桥多造了一些,但后面涌来了更多的千军万马。挤过去之后怎样?彼岸还有很多独木桥。教育的本质应该是让人过更好更幸福的生活,成为更完善的人,而不是千人一面,培养应试的机器。面对眼下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我们应该思考的不仅是增加有限的就业岗位的问题,而且应该思考何谓教育,何谓育人之道。这自然有一个“教育之门”的问题。那么,咱是一直就在“此门中”呢,还是永远“摸不着门”?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