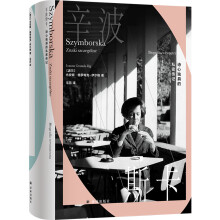第五章 安娜·斯涅金娜——雕刻叶塞宁<br> 一、忧郁天国<br> 1925年12月28日上午,一个妇女来到列宁格勒“安格里杰尔”旅馆,在一扇房门前停下,微笑着敲门!两声,没人答应,三声,没人答应! <br> 一个男人走过来,帮她敲门!轻敲,没人答应,捶门,没人答应!<br> 她有些着急,赶忙找到房东,拿钥匙开门。<br> 门开了,她捂住嘴,摊倒在地。<br> 简陋的屋子,沉静如死,一个男人悬挂在窗台前,脖子套着一条皮带,眼睛紧闭,一头金黄的柔软的卷发,清秀隽永的面容,健壮的体格。<br> “上帝呀!”女人大叫,“这是怎么了!”<br> 死者被人抱下来,已经僵硬,一根手指破了,上面血浆凝固。人们在书桌上发现用血写下的文字:<br> 再见吧,我的朋友,再见吧。<br> 你永铭于我的心中,我亲爱的朋友。<br> 即将来临的永远<br> 意味着我们来世的聚首。<br> 再见吧,我的朋友,<br> 不必话别也勿须握手,别难过,别悲戚,<br> —— 在我们的生活中,死不算惊奇<br> 可是活着,也不见得新鲜。<br> 这个男人的死亡惊动了整个彼得堡,作家、诗人、演员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来到他告别人间的旅馆。<br> 之后,他的尸体被转送到彼得堡的风唐卡大街作家协会,人们在他的身上撒满鲜花。无数的彼得堡的青年、少女聚集在作家协会门外哭泣、张望,手里拿着他的画像和诗歌。作家协会派出专门人员维持秩序,可是场面依旧失控。<br> 他的尸体被装上车辆,开往火车站。无数的人跟在车辆后面,哭泣着飞奔,大声呼喊。<br> 他的尸体被运往莫斯科,无数的人又爬上随后的火车,跟着到了莫斯科。<br> 火车到达莫斯科车站,站口汇聚着哭泣的人群,手里拿着鲜花。当他的灵柩被抬出的瞬间,淹没在人群中,道路被挤得水泄不通。<br> 他的尸体停唁在莫斯科的几天,无数的人们到来,为他送上鲜花。<br> 送葬的那天,人们跟着他的运棺车,走了一路又一路。尸体在普希金广场绕着普希金的铜像转了三圈,人们分不清楚是在送他,还是在送普希金。<br> 他在瓦甘科夫斯基墓地入土,无数的人为他送上花圈、蜡烛,久久不愿意离开。<br> 他死后一年,一个女子在漆黑的夜晚来到他的坟墓前。为他献上鲜花、美酒和眼泪,然后,朝自己的胸膛开枪。在烟盒纸上留下这样的语言:<br> “对我来说,一切最珍贵的东西都在这坟墓里,能够埋骨在这座坟茔里,是梦寐以求的事情。”<br> 这是怎样一个男人?他让所有俄罗斯人对他爱,爱得义无返顾,爱得沉醉不醒。<br> 谢尔盖?叶塞宁!那一年他将自己的头颅放进自己的皮带,那一年他刚刚30岁!那一年,他从莫斯科来到彼得堡,他对朋友说,他不会再回莫斯科,他要在彼得堡寻找新生,他要戒酒。他是来寻找新生的,缘何又要自杀?他的新生就是死亡!死亡让他挣脱,死亡是新生之上的新生。<br> 人们这样描述他的平躺在旅馆里的尸体:一只手微微上扬,仿佛要抓住什么东西;脸色浮肿。<br> 他要抓住什么?抓住新生?他的脸色浮肿,侵蚀了他的容颜,但是不能销毁他的俊美和忧郁,俊美和忧郁让俄罗斯人一世倾倒。<br> 后人无数次地问:他为什么要自杀?<br> 爱伦破在《人?岁月?生活》里遗忘了这点。三个自杀而亡的俄罗斯诗人里,他说,茨维“作为诗人而生,作为人而死”,马雅“作为人而生,作为诗人而死”。那么叶塞宁呢?<br> 给他下个定义:生为诗人,死为诗人。<br> 隐层的含义是:因为要成为诗人而生,因为成为了诗人而死。<br> 他的出现不像茨维一样为了所有世纪,所有世界;他的出现不像马雅一样为了一个世纪,一个世界;他的出现是为了俄罗斯,完整的俄罗斯,像普希金一样。<br> 标准的忧郁,是无暇的蓝宝石;极度的幻想,是浩瀚的天空;绝对的敏感,是某种触角动物;纯粹的浪漫,是大海上飘扬的风;永远的放浪形骸,是无法熔化的纤维;完全的俄罗斯民族,是新的偶像图腾。<br> 或者说他是存在于现代当中的古典,存在于喧哗当中的质朴,存在于抽象当中的实体,存在于钢筋中的泥土,存在于殷红的俄罗斯当中的另一个俄罗斯。<br> 所以,人们说他是令一个普希金,普希金的另一种延续。<br> 包括他的爱情都和普希金都是同一种基调:永远的运动,永远的不能停歇,他不愿意也不可能静止于某处,只能奔跑,静止则意味着危险。<br> 更微妙的比喻是:他是俄罗斯的李白,是整个世界的现代的李白。<br> 我无论如何<br> 也不会<br> 拿李白这样的生活<br> 去换<br> 其它生活<br> 他这样宣言!同样,他一次次兴致高昂地在酒劲下向人们讲述天上的李白,讲李白怎样捕获月亮。这位中国盛唐的诗人仿佛活在他的灵魂里。美酒、月亮同样是他的标尺,成为他的伴侣。烂醉如泥地在水池里捞月亮,他能做得出来。他不觉得失礼,反而很美。<br> 啊,月旁的大海<br> 闪着亮光,——令人欲投进水中。<br> 在这样湛蓝的天空下<br> 我不想让心儿平静。<br> 啊,月旁的大海<br> 闪着亮光,——令人欲投进水中。<br> 结果,他像李白一样风靡于俄罗斯当时代,同样风靡于俄罗斯所有时代,让人们心甘情愿地追逐。<br> 但是,他无法逃脱时代的命运,就像李白一样。<br> 北岛先生在谈曼德尔施塔姆时说,1925年叶塞宁的自缢,1930的马雅可夫斯基吞枪是某种相同的预兆。<br> 这是否意味着叶塞宁和马雅可夫斯基是一样的?<br> 首先,叶塞宁和四大诗人的材料不同,这是无疑的;但是,他也不能与马雅可夫斯基画等号,虽然帕斯捷尔纳克曾经指出:叶塞宁是马雅可夫斯基在人民领域的唯一竞争者和比肩者。叶塞宁终究不是马雅式的“时代的代言”。他首先是自己的,其次是民族的,归根结底他是自己的。<br> 可是,他终究又与马雅可夫斯基都是茨维所言的“那里的”,他们有着同源。不同的是,时代影射在叶塞宁身上,通过他的生活、爱情、诗歌得到反应,他还是一个独立个体,是自己的,没有消失于“那里”;而时代则是住在马雅那里,和他一起运转,他不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整体,是他人的,“他”这个概念消失了。<br> 所以,首先承认,他们的死不约而同又不可避免地宣告那个时代入魔了!<br> 然后承认,同样是“作为诗人而死”,他的“诗人之死”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人之死”的截然不同。<br> 他的死是自己的,对时代“入魔”的弹性的流动的反应,是挣扎,是预言!<br> 马雅可夫斯基的死则是整体的,是面对时代“入魔”的刚性的反应,是断裂,是宣言!<br> 正因为他没有丢失自己,没有丢失个体存在于整体中的姿态,所以,他没有像马雅一样被雕刻到历史的墙壁上,成为一个符号,永远被钉在那里。<br> 他活了下来,流淌下来,人们永远热爱与辍饮他的忧郁的浪漫。<br> 人们解开捆住他的绳索,送他进入那永恒的天国之门!<br> 二、梦幻年代<br> “我是一个农民诗人。”这句话温暖得像麦子,质朴得像泥土!请记住这句话,这是叶塞宁给自己的定位。<br> 1895年10月3日,叶赛宁生于梁赞省柯兹敏乡康斯坦丁诺沃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祖辈都是跑船的,手掌粗糙,手臂有力,体格健壮,性格粗犷,大开大合。<br> 一个标准的农民的孩子,他将演绎一场童话,怎样从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农村丫子攀登上俄罗斯诗歌王子宝座的童话。<br> 他没有任何财富,所拥有的就是农民的身份,这个身份他一生都没有摆脱,他不愿意摆脱,这个身份住在他的灵魂里,恰恰成为他的权杖,以农民的身份像种麦子一样种诗歌,他的诗歌的本质就是麦子,就是农村!<br> 是的,农村是他最大的财富,最富有的财富,因为在那里,他拥有所有梦幻,诗歌的梦幻,拥有浪漫的源泉,拥有纯洁的忧郁的湿润的蓝色底版。<br> 碧绿的草场,无边的麦田,温暖的阳光,神秘的树林,美丽的朝霞,清澈的露珠,沉郁的奥卡河,幽静的夜晚,干净的天空,永远温润的大月亮,还有喝不完的乡村酿酒。<br> 一切都可以入诗,一切都是诗歌。<br> 比如,“天上悬挂着一个大圆面包,那是月儿被歪曲了的形象。”<br> 比如,“在新犁的田野那一边,一株槟藜树花开红透。一颗闪光的星像熟透了的李子,悬挂在云树的枝头。”<br> 比如,“柔丝般的草儿垂着头颈,含香脂的松树吐出芬芳”<br> 这就是他的材料,也是他的方式,他自己的,独特的。<br> 浪漫在质朴里生成,梦幻在回忆里净化。不懂浪漫的人不会懂得他的诗,没有梦幻的人更不会懂得他的诗。<br> 他刚出生,父亲就跑到几百里外的莫斯科做猪肉生意,从不回家。老爹不在,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母亲却是顶好的女子,温柔贤惠,自学诗书,并且把普希金灌输给小叶塞宁。<br> 外祖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叶塞宁牵着她的小布裙子走路,靠着一本破旧的《圣经》识字。而外祖父费奥多尔更是远近闻名的船夫,性格豪爽粗犷。<br> “小谢尔盖,等你长大了也要是个大个子,不然我可不认你这个外孙——丢人” <br> 费奥多尔总是这样拍着他的小脑袋说,仰天大笑,满口鱼腥。<br> “好的,我一定长得又高又壮,比外公还健壮”他调皮地回答。<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