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雅典人有关优秀音乐的首要标准,比其原先看来(或者说是比它脱离为酒会辩护的背景时的样子)显得更加宽松,因此,我们发现,通过音乐进行教育的城邦中存在许多诱惑。因而,雅典人现在必须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第二个难题:陶冶情操的音乐与取悦于表演者的音乐之间可能不成比例。
在卷一讨论的基础上,我们起初可能会猜想,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依靠羞耻来控制这种危险。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不需要我们强迫音乐教育与美德教育完全同化:在音乐教育巾,我们能够更多地关注好的技巧,而较少去发展表演者对快乐的恰当内心体验。音乐教育纯粹成为基于羞耻的美德教育的伴随物,并成为其媒介之一。事实上,这似乎就是克勒尼阿斯最初的思路,正如在其回答中表明的那样(656a;参654d)。但是,雅典人并不喜欢这一回答:他严厉斥责了克勒尼阿斯的踌躇不前,并且,对基于羞耻的美德力量,他第一次表达了严肃质疑(656b)。概括来说,雅典人提出,运用音乐并不纯粹是为了弥补羞耻,而且为了培育植根于一种习性的新美德,这种习性逐渐在激情中确立起令人愉快的和谐。看起来,公民会受到教育,由此,在喜爱之事与要赞美之事之间,他们不会在心里感到有冲突。但同时,我们发现,雅典人追溯了这种内在冲突的根源,它不是好习惯与坏习惯之间的紧张,而是“习惯”与“本性”之间的张力(655e-656a)。是否有某种教育或某种习性,能矫正这种“坏的本性”?难道城邦一定不能再继续依靠羞耻,以便至少控制本性坏的人(也许还包括那些有着至善本性之人)?但是,这个对快乐的新的委身,不会侵蚀羞耻的力量吗?
公民对音乐的委身,可能唤醒某些快乐,对于这些快乐,羞耻并不足以控制它们。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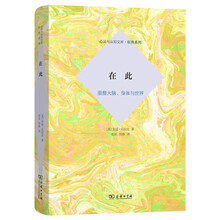





——迈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