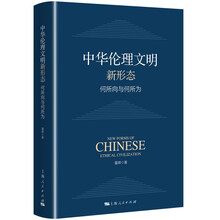可是,最令人类困惑的并非事实问题,而是价值和意义问题——什么是应该(比如自由、平等)的、更美好(比如幸福、公义)的生活。人类在生活的价值目的问题上从来就有深刻的歧见,相互冲突。价值目的问题上的冲突不可能靠复核对经验世界的观察、检查是否正确运用演绎规则得以解决。社会科学的政治学应该知趣,知道自己根本没有碰触到真正的政治问题。
对价值和意义问题,人们不仅不知道答案,甚至不知道如何去寻求解答、不知道什么东西可以成为证明答案正确的证据。哲学就是为对付这样的问题而存在的。这是不是说,哲学具有社会科学本质上不具备的超逾经验理性的知识呢?
并非如此。哲学本质上也是经验理性的:人们从来没有一种“普遍认可的专门知识”,“一旦我们明确了应当怎样着手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似乎就不是这种性质了”(“政治理论还存在吗?”,页409)。这不就是说,无论对于社会科学还是哲学,作为价值问题的政治问题都是不可解决的?既然如此,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哲学就可以甚至应该来对付这些问题?
何谓哲学的问题来了。对伯林来说,哲学本质上是政治的,其含义是:人类不可能避免价值评价这回事情。价值冲突问题就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就是对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应该与不应该作出裁定。既然哲学与社会科学一样,除了归纳和演绎的知识外一无所有,并没有建立一种超逾经验理性的知识的特权,从而凭借这种知识裁决人类在价值问题上的深刻歧见,为什么哲学的命相就是非得与价值问题(等于政治问题)打交道?社会科学可以幸运地“价值中立”,只关心经验事实,哲学为什么就没有这种幸运?
要回答这一问题,还得先搞清楚,价值问题为什么无法解决。
伯林告诉我们说,人类的价值多种多样,而且有不同层次。实现某一价值的手段,与需要实现的这种价值本身相比,就是次要价值。然而,两种价值究竟何者为目的、何者为手段,人类常常无法找到公认更高的价值标准来裁决。比如,个体与社群何者是目的、何者是手段?所谓的终极价值,其实最终都不是绝对的。再有,人类社会视为最高的价值的东西,常常并非一种,而是多种。比如,真、善、美或者爱情与生命相互冲突时,你说该取舍哪个?况且,不同的个人或群体,对于终极价值的理解是不同的。
生活意义上的不圆满和价值目的之间的冲突,是人类生存的无奈本质。哲学并非如社会科学那样是现代才有的。自从人类产生了意义渴求和目的意识,哲学就出现了。毋宁说,哲学是人类生存的无奈本质中生发出来的狂妄想象,现代的社会科学以为可以摆脱这种想象,同样是幻想。
不过,面对人类生存的无奈本质,哲学也可以是精明的智慧。比如,经验主义哲学坦然承认,人类所有的知识不可能超出经验范围,价值观念不过是人所有的一种知识,当然也在经验范围内,因而不可能有什么神圣、绝对的价值。浪漫主义哲学告诉人们,人类所有的价值(或真理)想象都是从历史的民族机体中生发出来的,人类历史地依群而生,价值(或真理)想象不可能相同,冲突因而是自然而然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