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一切都是舒缓的,平和的,宁静的,一如既往的。他们的生活和为人就像正午的阳光照耀下的一片绿叶,通体透明,脉络清晰,色泽柔和而又可爱。不像有些人,生来就是模模糊糊的,到处留下的都是语焉不详的人生片断,把他周围的人,把生活与历史都搅得似是而非。金祥和曾善美是阳光下的绿叶,全钢铁设计院的人都相信这一点儿。他们相信在他们的眼睛里,这片绿叶就连毛细血管都是纤毫毕现的。
辣辣死于一九八九年夏天。
四清是置她于死地的直接因素。从小到大,从读书到高考落选到进工厂当电工,四清都是个波澜不惊的人。平时爱看点儿报纸,私人订了《飞碟》之类的几种科普杂志。人长得高大,见了生人腼腆,衣服穿得整齐。辣辣养了八个儿女,希望一个一个破灭,谈不得!别的孩子都不谈了,四清一定会顺利地娶妻生子,让辣辣好生做几日奶奶的。人生一世,辣辣什么没做过!就剩奶奶没做,就这一个缺憾一个念想了。
四清平日生活极有规律,按钟点上下班,从不随便在外面过夜。忽然几天不回家,辣辣着慌了,央咬金去找弟弟,咬金还说不要紧,这么大一个男孩子还不兴在外面玩玩?结果后来一找全家都吓了一大跳,全沔水镇就没见四清这个人。
又是几日过去。那是傍晚时分,电视里播放着新闻联播,忽然四清在屏幕上出现了。虽然镜头就片刻晃了开去,却也足以让人认出四清。咬金两拳相击,说:“好了,找到了。四清在北京。”
辣辣愣说兴许眼睛花了。直坐着等沔水镇电视台的新闻重播,又实实在在看了一遍。
“这小狗日的!怎么去了北京?”辣辣问咬金。
咬金耸耸肩,说:“别管他了。”
“怎么不管,他虚岁二十五了,该结婚的人了。到北京去干什么?”
辣辣固执地要咬金去找回四清,咬金不干,说人海茫茫,哪儿去找?别土啦巴叽以为北京也是沔水镇。
四清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又在沔水镇传为佳话。人们议论道:不管怎么说,全沔水镇没人上过中央电视台,四清上了,够精彩的了。
此时电视机已覆盖沔水镇,王四清和他父亲当年一样又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辣辣都不敢上街买菜了。许多人公开追着看她,问她儿子去北京的详细情况。辣辣发现如今的人们是多么恬不知耻,不仅没有同情和理解,反而把他们自己的怪想法强加于你。
四清离家半个多月后,辣辣去找了灵姑。灵姑还住在沔水一中后面,老朽得不成人形了。但她的生意空前兴隆,差不多是公开开业,五湖四海都有人寻来,亡灵讲话每次最长三分钟,一次五块钱。老婆子凭这本事盖了五栋三层楼的楼房,不论儿子还是女儿,每人赠送一栋。
辣辣来的目的是想查查四清是否已到阴间。灵姑推搪说:北京太远,人口太多,查不来。”显然灵姑也是每日看电视新闻的,她说:“先和你丈夫说说话吧,他是好义茶楼塌死的不是?你还有个儿子是强奸妇女判了死刑不是?”
后来,灵姑只收了辣辣的半费。辣辣现在有钱了,可灵姑不要,说沔水镇老主顾一律半价。
从灵姑那儿回来,辣辣就倒下了。长年卖血严重地损害了她的肌体。虚胖浮肿使她步履艰难。极度的贫血使她每个重要器官的功能都衰竭了。
辣辣在死之前支开了咬金。等咬金办完事赶回来辣辣已经穿好考究的寿衣躺在床上,脚上蹬着一双时髦的浅口高跟皮鞋——正如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的誓愿那样——皮鞋擦得黑又
亮。辣辣四肢正在变凉,眼睛却极不甘心地睁着,仿佛有话要说,咬金连忙找人请来了姐姐艳春和老朱头。艳春凑到母亲嘴边听了一会儿听不出个所以然。只有老朱头听清了辣辣的话。
他说:“她要找回四清和冬儿。”
辣辣听了老朱头的话,咯儿一声打了个声音很怪的呃,双目一闭,咽了气。
大家忙着辣辣的后事,艳春的儿子发现了得屋的尸体,得屋在自己床上,蚊帐垂着。辣辣给得屋服了超大剂量的安眠药,也换了一身新衣服。得屋安详地躺着,生平第一次整整洁洁,像个人的模样。
有些没经科学证实的怪事并不是人类的臆想,它是事实。就在辣辣一息尚存叨念着冬儿的时候,远在北京的冬儿忽然从噩梦中惊醒。她满头大汗坐起来,说:“我妈死了!”她丈夫开了灯,说:“你不是孤儿吗?”
“不是!”冬儿说。
冬儿害怕吵醒了儿子,她到隔壁房间看了儿子,踏着地毯无声地回到卧室。
丈夫已为她冲了一杯咖啡。她啜着咖啡,在空调机轻微的嗡嗡声中给丈夫讲起她真实的家世。她是在做了母亲之后开始体谅自己母亲的。她一直等待着自己战胜自己的自尊心,然后带儿子回去看望妈妈。
辣辣就在冬儿饱含泪水的回忆中闭上了双眼。这年她五十五岁。
当太阳又升起来的时候,曾善美还是按时起床了。她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非常精心地化了一个淡妆。我们从满面春色在食堂买早点的曾善美身上发现,化妆绝对是女人的魔术。发明它的一定是一个洞悉世事未雨绸缪的女权主义的巫女。
在昨夜里饱受蹂躏的曾善美出现在办公室时的形象犹如一叶含露的青草,娇小、清新、淡雅、芬芳可人。她用干净的抹布将办公室的办公桌一一地擦过。她为窗台上的文竹和吊兰浇了
水。光芒通透而又健康饱满的初升太阳把她为花草整理枯枝败叶的手指勾勒得玲珑剔透,色泽金黄。凡进办公室的人,无不从曾善美美丽的手指上获得无形的暗示:生活是正常的,工作是美好的,你我是平安的。
MORNING?
MORNING!
一连串的早上的问好愉快地回旋在曾善美他们办公室的同事之间。他们喜欢在日常生活的反复琐碎的关节处使用简洁的英语。比如通常他们只说“YES”、“NO"、“GO”、“SHIT”等等。流畅的不费口舌的发音消解着他们生活的复杂。一般只有当谁遇上了问题,无论是来自家庭的还是外界的,他才会无意中不再使用英语。只有中国的复杂语言才能贴切地解释中国的复杂矛盾。但是这一天曾善美还是毫无障碍地对她的同事们打招呼说:“MORNING!”
曾善美今天并没有沉默寡言。她一边工作一边与大家聊天。他们今天谈论的主题是童话王国里的当代新童话,即丹麦王子与具有中国血统的香港姑娘喜结良缘的事。丹麦王子乔基姆现年二十六岁,英俊潇洒,他的婚事一直为大众舆论和新闻传媒所热烈关注,几乎人人都以为他至少要选择一个漂亮的欧洲金发女郎。可他却与曼利小姐定了婚。曼利小姐对乔基姆来说实际上是大姐。她今年已年满三十一岁。她的父系是中国血统,她的祖母和父亲都出生在上海;她的母亲是奥地利人。曼利小姐自己是英国籍,会说一口的广东话。
曾善美们为中国广东话进入丹麦王宫感到高兴。他们断言丹麦王子一定是读安徒生的童话读得太多了。
更加助人谈兴的是电视里面播出了乔基姆和曼利的订婚仪式的场面。全世界的人都看见了紧跟在这对新人后面的一个风度翩翩喜笑颜开的长者,大家以为他必然地是一位皇亲国戚,可
是电视里的播音员严肃地指出,这是一个国际骗子,专门地骗吃骗喝。他是自己坐飞机赶到哥本哈根的,就那么大大咧咧地走进了王宫,还乐呵呵地挤在新人的身边,目的就是想在订婚宴席上大饱口福。当这位乐呵呵和蔼可亲的人还在电视屏幕上向全世界得意微笑的时候,播音员报道的却已经是结果:他已经当场被国际刑警抓获,因为他有混吃混喝的案底。原来他老人家已经是多次出席国际上这一类高规格的宴会了。
这个大胆可爱的没有危害的国际骗子,他一定没有想到,曾善美和她的同事们由于生活中出现了一个他,这一天过得是多么轻松和愉快。
金祥则在他的周围与人大谈北约轰炸波黑塞族的事情,对北约的高技术军事武器十分地入迷。这在一个男人是很正常的事情。大多数男人对战争是非常感兴趣的。
金祥脸很黑,是农民的皮肤,一般不会被别人从表面看出什么蹊跷来。他只是头脑有点儿恍惚,脚底有一些发飘。但他绝对不是一个脆弱的人。他深知现在自己越发要在事业上立住。
他和曾善美是完蛋了。但只要他在事业上发达兴旺,女人和爱情是不用愁的。现在改革开放了,大街上美女如云,大饭店里美腿如林——这是现在的大街向我们再三强调的一个事实。毕竟
时代不同了。人可以活得潇洒一些。面包会有的,孩子也会有的。他还年轻得很呢。只是他一定要在事业上稳住。
这个早晨,当曾善美在她的办公室浇花的时候,金祥也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浇花。后来就办公、喝茶、看报纸、打电话。在电话里与朋友谈妥了兑换八百马克的事情,约好明天中午在蒙娜丽莎餐馆一块儿吃饭办事。其余的时间与同事大谈战争与武器。没有任何人发现金祥的腿发飘。
这是舒缓的、平和的、宁静的、一如既往的一天。金祥和曾善美不约而同地共同制造了这样的一天。就如他们制造的许多个这样的白天。
不过,说他们制造白天似乎容易让人理解出别的一层意思,好像他们对于公开的生活过于精心和刻意地虚饰。其实不是。制造没有别的意思,就是纯粹的制造,就像世界上最完美的名牌小汽车和轩尼诗干邑白兰地,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制造出来的。制造公众习惯的白天的表面的生活是不难的。金祥曾善美都是有一定生活阅历的人了。走到这一步,在一个大城市的国家级
的科研单位里拥有称心而稳定的工作和一套两居室的住房和大家的尊重与喜爱,这是来之不易的。生活早已调教了他们。他们已经习惯了一种白天的生活方式。他们已经无须刻意伪装。因为无论是男人金祥还是女人曾善美,他们都是非常聪明的人。至于有一些人发生了一点儿事情就会产生不分场合的冲动,有到处哭泣和倾诉的欲望,那是幼稚可笑的。是比较不聪明的人。
这种情况绝对不会发生在现年四十二岁的金祥和三十八岁的曾善美身上。他们是中国最沉得住气的一代人。
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人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解铃就得系铃人。你只能自己与自己对话,自己对自己哭泣,自已向自己倾诉。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地强调了金祥曾善美天衣无缝的白天生活。他们的白天真的就是天衣无缝的。因为我们的人群中有着不少的金祥曾善美,所以,逻辑断裂了,理论是形而上的,人类屡屡为短视所束缚。比如永远解释不清楚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就像狗永远怀着疑问追咬自己的尾巴,而我们还在一旁无知地嘲笑狗。所以,时间是能够倒流的,隐秘的空间是可以随意建立的;果完全可以先于因,死也可以先于生。所以,天下发生的事情有许多是找不出答案的。比如那个混进丹麦王子的订婚宴会的老顽童,我们相信仅仅是他飞到丹麦去的机票钱,就足够他饱吃几顿鸡鸭鱼肉。一个人的胃容量能有多大?但他还是做了违背常识的事情。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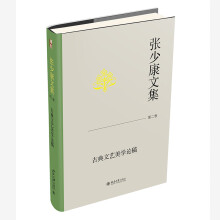
什么才能成为永远的表达
费振钟
世纪之交,出版作者的又一本选集,这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我宁愿简单地相信,它仅仅为喜欢池莉作品的读者提供了又一次阅读的机会。如果这本选集依然能够使读者产生新的阅读热情,那么一切也就不言自明了。像人们已经知道的那样,作家的存在及价值,是靠不停地被阅读而得到证实的,我想,池莉应该高兴地期待每一次被重新阅读的机会。
读者自然应该记得池莉一九八七年在《上海文学》上的那部中篇小说《烦恼人生》。按照我们平庸的看法,一部作品能够成就一个作家,你不能不承认这里面隐含了写作的某种秘密。十二年前,作者还不能完全洞悉的秘密,也许经过时间的保存,现在已经可以坦陈在读者面前。假如有必要,我完全可以引录作者的自述说明事实,然而,难道读者不是早就通过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得出可靠的结论吗?回想起来,《烦恼人生》出现在读者面前的那一二年里,人们经过阅读,已经知道池莉是怎样的作家,她的写作是怎样的写作。而一九八七年前后的文学批评理论,比较成功地解释了池莉的写作经验,仅属巧合,时过境迁,你不会真的以为,那时候池莉因为《烦恼人生》而成为读者关注的作家,是由于理论引导和鼓动吧?清醒一点儿说,再好的理论,也不能代替或僭越读者的阅读感觉和选择标准。过分夸大《烦恼人生》的理论处境,也许就要损伤它的真正的阅读价值。
现在这部小说在作者最新选本中出现,虽然必然,但也反映了作者对于写作过程中最重要环节的深刻回忆。重复体会当时的写作状况,特别从这种重复中进一步确证和延续自己的写作追求,对于今天的池莉来说,既心情愉快,又具有新的求知之意。
那么,回忆的焦点,不用说就是“烦恼”一词。这个词语出现在池莉的写作视角里,起初也许很平常很通俗,可是一旦作者开始赋予它以当代生活意味,这个词语立即变得意绪纷纭丰富生动起来了。它在指向当代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内心状态时,不仅表明池莉感知现实世界的个人能力,而且主要还表明她在小说叙述上获得了关键的语词。于是,“烦恼”从具体的生活内容和人物情节中浮升出来,成为一种形式,一种可以让作者能够顺利完成叙事的表达方式。可以想见,直至现在,池莉都有理由为那一年初春在《烦恼人生》的写作中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感到满意。也许这部小说从写作到发表,曾有过不少曲折和艰难,但那是可以完全忽略的,需要记住的一点儿,是读者对池莉的接受和理解,恰恰表现为对她的小说表达方式的认同。即使他们模糊了其中的故事和人物,却忘不了这部小说的表达,是如此之深地触及到了他们的人生真实和疲弱之处,触及到了在世俗生活表象之下的生存之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