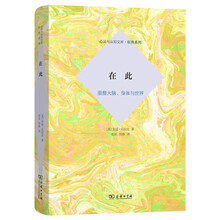席勒出身于德国西南部符腾堡公国一个普通劳动者家庭。由于父亲的工作关系,他从孩提时代起就进了欧根公爵开办的“军事植物学校”。但这所所谓的“学校”完全按照封建统治者的专制思维和严酷纪律来扼杀青少年的自由天性,进而使他们成为统治者所需要的顺民和奴才,所以被弗兰茨·梅林称为“奴隶培训所”。然而,这时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启蒙运动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正方兴未艾。天性爱好自由的小席勒对启蒙运动思想家如卢梭的天赋人权思想钦佩不已。他不但没有被严酷的军事纪律训练成为驯服工具,反而对这种凭恃军事暴力维持政权的制度深恶痛绝。这种情绪的日益积累,使他在20岁左右写出了公然挑战这个落后而残暴的政权的不朽杰作《强盗》,并在公爵管辖不到的曼海姆搬上舞台,轰动全
国,乃至欧洲。舞台是当时最有力的讲台。席勒是怀着对封建贵族统治的强烈痛恨,怀着对民主共和制度的美好憧憬,才创作这个剧本的。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到来之前,他第一个在德国提出“把德意志建成一个共和国”的要求,这不啻是在这个分裂和敝陋的国度竖起一面号召战斗而且指引方向的旗帜。难怪恩格斯在评价三年后他写的《阴谋与爱情》时,指出这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性的戏剧”。如果概括一下席勒早期也就是18世纪80年代写的四部戏剧,包括尚未提及的《菲爱斯科》与《唐·卡洛斯》,尽管题材各异,但总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反抗暴政,争取自由。他的这一政治态度与法国大革命的思潮完全合拍,所以1792年,席勒与美国国父华盛顿一道,同时获得法国国民议会颁发的“法国荣誉公民证书”。这无疑是一项殊荣。
凡是民族英雄,都有鸿雁之志。席勒明白,要把德意志民族从落后而暴虐的可耻状态下解救出来,需要什么样的精神准备和人格力量。因此席勒借《强盗》中的主人公卡尔·穆尔之口说:“他们要让我把我的身体压缩在女人的紧身衣里,把我的意志压缩在法律里。法律只会把雄鹰的飞翔变成蜗牛的爬行。法律从没有产生过伟大人物,然而自由才造成巨人和英雄。”正是怀着这样崇高的使命意识,席勒在踏上征途的第一步,就以雄鹰的视野,战士的姿态,不畏风险,毅然逃离了欧根公爵的控制,及时挣脱了那个像女人紧身衣般束缚着他的生存环境,宁愿在朋友间过着东躲西藏的“炼狱”生活。不难理解,这时期席勒的作品,从其政治倾向、思想高度和人格精神方面,都要超出狂飙突进时期的其他作家,甚至包括歌德。因此如果说,席勒由于年轻十几岁,没有能在狂飙突进的高潮中推波助澜,那么席勒这几个剧作的问世,却使狂飙突进的余波又掀起几个巨浪,因而使这一运动又往前推进好几年。
一个人的雄心壮志如果离开崇高的目的是不会有什么成就的。席勒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始终把他的伟大抱负与国家前途和民族团结乃至全人类的友爱和平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并不因为这个国家被少数专制而腐朽的王公贵族所统治,而厌弃这个国家和民族,甚至一走了事。不!在他看来目前状况只不过是暂时现象,祖国的命运与前途,绝不会取决于这一堆历史垃圾。在《德意志的伟大》一诗中,他明确地写道:“德意志帝国与德意志民族是两回事。”他的这一概念在下面这一节诗句中表达得还要完整:“德意志的崇高和荣誉/并不寄托在王侯们的头顶/纵使德意志帝国在战火中灭亡/德意志的伟大依然长存。”
席勒的不寻常之处是,他不像一般的骚人墨客,对一种真实而高尚的情怀仅仅停留在文字抒发上,他是要身体力行,切实去实践自己理想的,他的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他积极争取与歌德的合作,并在合作中取得极大的成功。这一事件的背景是,德国由于长期公侯割据,严重阻碍了德国的发展和强大,社会上的市侩习气弥漫,以致马克思曾经说了这样愤激的语句:这个民族连清除自己院子里的一堆垃圾的力量都没有!德国的新兴资产阶级没有能够像法国资产阶级那样形成一种足以推翻贵族阶级统治的强大政治力量,甚至当法国大革命进一步深入时,德国许多知识精英包括歌德和席勒,对法国大革命都由原来的欢迎转为畏惧和厌恶了!德国的知识精英们既然在政治上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他们就把聪明才智投入到文化或文学方面来,就像前面恩格斯说的那样。但这一时期的德国文学也是令人忧虑的,也就是说它是不独立的:在启蒙运动以前,它一味模仿法国已趋僵化的古典主义;启蒙运动以后,又转向了英国。总之没有自己的民族圭臬。席勒是个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力的人,就在《德意志的伟大》那首诗中,他呼吁德意志人“昂起头来,怀着自信跻人世界民族之林”!为了振兴德国的民族文学,他决心以古代希腊罗马文学为榜样,以纯洁的语言,优美的形式,注入人道主义的内容,创造出德意志文学自己的风貌来。但他觉得单枪匹马难成气候,必须有志向相同而又实力雄厚的人与他合作。为此他首先看中了歌德,虽然歌德资格比他老,地位也比他高,在1787年开始认识的头6、7年里,歌德一直对他比较冷淡,席勒对此曾经也曾颇为不快。但为了远大目标,席勒克服了自己的感受,而以一封封热情而诚恳的信相邀,歌德最终被他1794年8月23日的那封长信所打动。席勒之所以如此需要歌德的合作,并不是由于他认为他与歌德之间处处都会想法一致,配合默契。相反,他认为,有差别才有结合的必要。这样,“每个人都可以给另一个人以对方所缺少的东西,并且从对方接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1793年9月1日致科尔纳的信)事实上,歌德是个天才的感性诗人,而席勒则是善于推理的思想家;一个侧重于现实主义,一个倾向于浪漫主义;一个重客观,一个重主观。然而正因为这样,二者的结合,就能1加1大于2,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歌德之所以最后被席勒的信所打动,正是因为席勒透辟地分析了歌德的特点以及他与歌德之间的异与同,指出,天才的创作出于他的天性,而不是他的自觉。因此天才对他自己来说始终是个秘密。歌德感到席勒的分析鞭辟人里。从此,直到1805年席勒逝世的整整十年中,两位巨人为了进行“伟大的、有价值的创作”,在求同存异中,或者促膝交谈,或者书信往来;互相勉励,互相切磋,“两人如同一人”(歌德语)。席勒凭着他较年轻、热情、敏锐,不时进发思想火花,常常激发出歌德的创作灵感,使他那被多年政务拖疲惫了的创作情绪重新勃发起来。他自己曾以感激的口吻对席勒说:“您给予我第二次青春,当我差不多已经完全停止创作的时候,您又使我成为诗人。”在这良好的气氛下,两人互写犀利的讽刺短诗,名日“赠辞”,对社会上的市侩习气和文艺界的恶俗风气大加针砭,以净化国民的精神面貌。接着两人又竞写叙事谣曲,使1798年成为“叙事诗年”。歌德一方面经常接受席勒的建议,努力写作自己的重要作品,首先把中断了的《浮士德》第一部继续写完。同时完成长篇小
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赫尔曼与窦绿台》等,使他的创作生涯出现第二个高峰。一方面他也积极参与和帮助席勒的创作,尤其是席勒花费心血最多的戏剧巨著《华伦施坦》三部曲以及他的晚年不朽名剧《威廉·退尔》。后者的素材都是歌德提供给席勒的。为此他放弃了自己写一部叙事长诗的计划。真说得上是无私的奉献。这类事例在诗歌创作中还要普遍,正如歌德自己所说:“关于某些个别思想,很难说哪些是他的,哪些是我的。许多诗句是咱俩在一起合作的,有时意思是我想出的,而诗是他写的,有时情况正相反,有时他作第一句,我作第二句,这里怎么能有你我之分呢?”难怪席勒死后,歌德感到深沉的悲痛,说等于他“失去生命的一半”。
席勒和歌德合作的另一个共同目标是振兴民族戏剧,建立民族剧院。歌德从意大利回来以后,什么官职都不要,只保留一个戏剧主管的职务,说明他对德国戏剧事业的重视程度。席勒最后几年也把主要精力重新放在戏剧上。提高德国戏剧的原创品格,建立像样的民族剧院,从而在这一领域摆脱对外国的依赖,树立国家的文化形象,这是席勒和歌德的共同追求。迄今依然耸立在魏玛市中心的那座庄重而雅致的民族剧院,就是两人心血的结晶。耸立在剧院前面的那尊宏伟的歌德、席勒铜铸塑像,是德国戏剧走向独立的丰碑,也是歌德与席勒亲密合作,从而把德国文学推向高峰,进而使德国跻人世界文学大国之林的标志。而他们在魏玛的合葬墓,则是两位伟人永恒友谊的象征。两人生前往还的1005封书信,可看作世界上最长的墓志铭。
这十年合作的成功,完全证实了席勒的远见卓识。它不仅有文学上的意义,而且有文化和伦理上的意义。这意义就在于,它至少解构了两句中国成语。一句叫作“一山不容二虎”。魏玛这座小山居然容下了二只“巨虎”,他们不仅没有彼此相斗,而是亲密合作。另一句成语也是人所共知的,叫“文人相轻”。歌德和席勒的十年实践,把“轻”改成另一个“亲”。从而创造了一段世界文学史上值得千古传诵的佳话。这是席勒那“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思想的生动体现。这在我们努力创造“和谐社会”的今天,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