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从来没有使用不当的手段来追求权力,他也从来没有被迫逢迎他们,相反,由于他享有崇高的威望,以致他敢于提出相反的意见,甚至向他们发怒。每当他看到他们过分得意的时候,他都会说服他们想到自己的危险。另外一方面,如果他们由于恐慌而丧失勇气的时候,他会马上恢复他们的自信心。一言以蔽之,雅典虽名义上是民主制,但事实上权力掌握在第一公民手中。他的继任者们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们彼此之间大都处于平等地位,而每个人都想力争居于首要地位,最终他们竞准备靠牺牲整个城邦的利益来迎合民众的幻想。①
但是现代学者的分析告诉我们事情要复杂得多。康福德就说,在与民众的博弈中即使是伯里克利最终也处于被动的下风,不得不“牺牲整个城邦的利益来迎合民众的幻想”。当时雅典民主的一个重镇是新商业中心——比雷艾夫港。大量外邦人移居此地,他们主要是工商业人口。在雅典沿海地区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政策最初来自梭伦:“他看到阿提卡土地贫瘠,而海上经商者也决不会为那些没有东西交换的人输入货物,因此他将公民的注意力引向手工艺”,“他规定商业应该被视为一项光荣的事业”。梭伦的外邦人归化法规定:全家迁入雅典从事手工业的人可以归化为雅典公民。后来虽然由于害怕外邦血统的大量渗透,雅典收紧了公民权的授予条件,但是,为了保护手工业,居住在比雷艾夫港的未归化的外邦人仍然像公民那样自由,并且受到法律保护。内战开始之前,他们已经大约有9000人,连同家属,组成了3万人的外邦人口。这些富裕外邦人相同的社会阶级和共同的利益使他们形成了一个目标明确的坚实集团。他们与雅典土生土长的公民们没有共同的传统,也没有共同的利益。乡下人鄙视他们为“航海的贱民”,“没有修养、粗俗的乌合之众”。伯里克利的“葬礼讲话”也许希望辨析和安抚双方的利益。雅典的农民忙于耕作,不愿意花时间进城参政议政,这些拥有长期居留权的港口富人却可以让自己雇佣的大量自由工匠,即公民去投票通过有利于自己的国策。这些人通常是伯里克利民主的主要支持者。但是这些独立自主的人民渐渐会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感到自己能决定伯里克利的沉浮。伯里克利此时必须站在人民的前列,否则就会被踩在脚下。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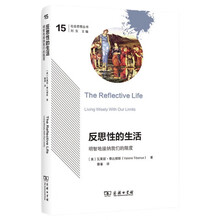

——赫拉克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