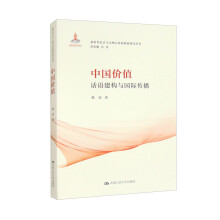古籍中的人名、官名、地名、国名、族名等等译名,通通分别换成索伦语、满洲语、蒙古语的汉字音译①。这样一来,《四库全书》对古书的妄改妄删不计其数,有的书改得面目全非。昔陈垣先生曾以四库馆臣所辑《旧五代史》的几种版本以及《册府元龟》互校,摘出其中因民族问题之忌讳而改窜原文的例子194条,写成《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三卷。其中归纳为忌虏、忌戎、忌胡、忌夷狄、忌犬戎、忌蕃、忌酋、忌伪、忌贼、忌犯阙、忌汉等类,可见其禁忌之严密而荒谬。光绪三十四年许涵度得修四库时用作底本之《三朝北盟会编》旧抄本,据以刻印,并将四库馆臣删改之处附注於有关字句之下,读者从此本便可看到修《四库全书》时篡改古籍之形形色色及其良苦用心。由於在上者的无理提倡,在下者不敢不遵,造就给清代的古籍整理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直到清代後期,此风才逐渐松弛。
第三节校勘的方法(上)
古今学者所用、所说的校勘方法很多,其中以陈垣先生校《元典章》总结的“校法四例”最为全面、最为精辟(见《元典章校补释例》卷六《校例》或《校勘学释例》)。原文仅数百字,今节引於下,并略加发挥。
对校
一为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
处,则注於其旁。……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後再用其他校法。
按所谓对校法,也就是版本校。这是最基本的校勘方法。正如陈先生所说:“有非对校决不知其误者,以其文义表面上无误可疑也”,如《元典章》元刻本“延佑四年闰正月”,沈刻本讹作“延佑四年正月”,表面上并没有错,若不校元刻本,决不可能知道漏了“闰”字。又“有知其误,非对校无以知为何误者”,如沈刻本“每月五十五日”,显然有误,但若不校元刻本,谁也不可能知道为“每五月十五日”之误。
但陈先生把对校法等同於“只校异同,不校是非”的“死校”,似乎不妥。对校与下面说的本校、他校,在校了之後,都可以有两种作法:一种是列出异同就算完成任务,而不判断是
非;一种是既列出异同,又判断是非。所以“对校”不等於“死校”。
只校异同、不校是非的“死校”,其长处短处陈先生已说得很清楚。这种校法还是需要的,特别是一些重要的、版本很多的古籍,客观地列出各本的异同,提供给别人研究,让别人来判断是非,这是一种慎重的态度;而且学者得此校本,等於是看到了很多版本,非常方便。像清李调元辑《函海》本之校《华阳国志}、日本学者山井鼎之《七经孟子考文》、民国间章钮的《胡刻通监正文校宋记》,对进一步整理与研究这些书都很有用处。但是我们更提倡既校异同、又校是非。因为校勘的根本任务就在於通过比较异同来判断谁是谁非、谁真谁伪,以便恢复古书的本来面目。对校各本,列出异同,这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在作版本校之前,要对所校之书曾有的和现有的各种版本及其版本源流进行过细的调查研究。弄清着者或编者的生平,本书着作、编纂的缘起和经过,最早版本的情况,後来有过哪些版本,现今还有哪些版本,各本的大概情况如何,各本之间的关系如何,前人对各本有何评论,等等。搞清楚这些问题,有助於我们初步确定工作底本,寻求校本,不致造成重大的失误与遣漏;也有助於在校勘的过程中正确地判断各本文字的是非、优劣与真伪。
用於对校的版本自然是多多益善。因为版本越多,校勘的准确性也就会越大。如果没有条件遍校各种版本,则应该参考版本目录或按照学者的一般看法先求善本。但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第三节已经指出的,版本之善与不善,还是要校过才知道,目录书上说的或学者说的不一定靠得住。别人说是善本的不一定就善,别人忽视甚至贬低的也不一定就不善。而且任何一种善本也免不了有谬误;相反,再劣的本子也往往会有一二可取之处。校勘者应当树立一条座右铭:不迷信任何版本!
陈垣先生说对校法“最稳当”,这是相对而言,有时也不是很稳当。我们前边谈到了种种妄改古书的花样,其中有一些隐蔽的花样,如不保持警惕,就会上当。比如妄补缺字,就是一个陷阱,要特别小心。某书的某些文字,其他本子包括较早的本子都缺,只有某本不缺,当然也可能它别有所据,但也很可能并无所据,而是率意妄补,这种地方就不能轻易信以为真。《四库全书》就经常如此。某些文字,各种本子都相同,也许各种本子都错了;各种本子都不同,也不一定有一种是对的。所以必须仔细地、全面地考察。
本校
二为本校法。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後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此法於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
按本校法,.即刘向所谓“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是也。以本书前後互证,主要有以下方面:
以目录与本书互校:例如《华阳国志》目录有“卷九李特雄期寿势志”,则原书本有《李势志》,而今本正文无此志,可知有脱文。
以标题与正文互校:例如四部丛刊影印宋刻本《豫章黄先生文集》卷27有《跋东坡画石》一篇,而其文乃全论介之推逃赏事,与画石了不相涉,则可知文与题必有一误。核之《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192、《苏门六君子文粹》卷39,二书亦全载其文,而题作《跋(晋世家)後》,与文相合,可证本集之误。乾隆、光绪刻本《山谷全书》未经校勘,不以文不对题而致疑,反而加按大谈介之推逃赏与画石之关系,殊为可笑。由此也可见本校法的作用。
以正文与注文互校:例如《礼记.檀弓》:“望反诸幽,求诸鬼神之道也。”孔颖达《正义》云:“复魄之时,冀望魂神於幽处而来,所以望诸幽者,求诸鬼神之道也。”据此可知,今本正文“反”字为衍文。一一这是以注文校正文。《穆天子传》:“道里悠远,山川谏之。”今本郭璞注:“间音谏。”按正文无“间”字,不应如此注,原注应作“谏音间”,意即“谏”为“间”的假借字,今本误倒。一一这是以正文校注文。清代学者校勘经籍,最善於使用此法。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