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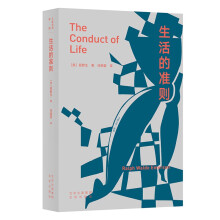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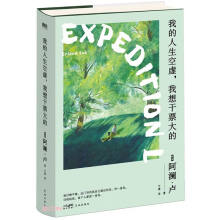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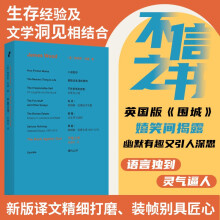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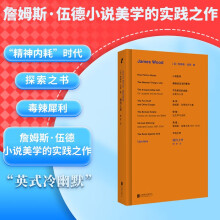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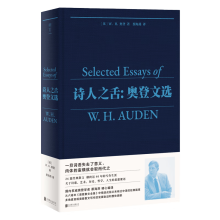





“我们的动作伴随着我们,就像磷光从属于磷一样;
不错,它们使我们受到了耗损,但也构成了我们的光辉。”
二十八岁的纪德,游历北非、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南部,在崭新的天地间写下《地粮》。
他狂热地表达生命的能量,想摆脱文学界的矫揉造作,宣称要让文学“赤脚踩在地上”。
六十六岁的纪德,用一生的思想食粮回应少作,时隔半生,再度谈论爱情、孤独、自由、欲望,
凝结成一段段沉思中的美丽箴言,命名为《新粮》。
拿塔纳埃勒,对于许多美好的事物,我耗尽了我的爱。这些事物的光辉来自我为之不断燃烧着的爱。我无法使自己厌倦。任何热忱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爱的耗损,一种美妙的耗损。
那些怪僻的意见,那些思想上的极端迂回曲折,那些分歧不一,永远吸引着我——异端分子中的异端分子。每一种思想,只有在它不同于别的思想时,才能使我感兴趣。因此,我排斥了同情。在同情之中,我看到的只是承认一种共同的感情。
拿塔纳埃勒,爱根本不是同情。
行动吧,别去判断这是好是歹。去爱吧,别担心这是善是恶。
拿塔纳埃勒,我要教给你热忱。
拿塔纳埃勒;宁可要一种悲怆的生存,也不要那种安宁。除了那死亡的长眠,我不需要其他的安息。我担心,在我一生中没有得到满足的种种欲望和精力,会继续存在而使我极度痛苦。我希望,在把压积在我胸中的一切情愫都表露在人间以后,我能心满意足而又万念俱寂地死去。
拿塔纳埃勒,爱根本不是同情。你明白,这两者并不一样,不是吗?有时,只是由于害怕失去爱,我才会对忧愁、烦恼、痛苦产生同情;否则,我是很难忍受它们的。要让各人自己去关心生活。
(今天我不能撰写,因为谷仓中有一个轮子在转动。我昨天就见到它了。它在打油菜。屑粒飞舞着,油菜籽纷纷滚落在地上。灰尘使人窒息。一个妇女在推磨子。两个可爱的男孩,赤着脚,在收油菜籽。
我哭了,因为我没有什么别的话好说。
我知道,在你没有什么话好说的时候,就不动笔。可是我却写下来了,对同一题材我还要写些别的东西。)
*
拿塔纳埃勒,我喜欢给你一种任何人还没有给过你的快乐。我不知道怎样给你这种快乐。可是,我确实拥有它。我想比任何别的人都更亲昵地和你谈话。我想在黑夜到达,那时你接连不断地展开和合上许多书本,在每本书中,寻找比以往所得到的更多的启示;那时你的热忱由于感受不到支持,即将变成忧愁。我只为你而写,我只为你的这些时刻而写。我要写一本这样的书,那里面任何思想,任何个人的感情对你都好像不复存在,你会觉得你在那里面看到的只是自己的热忱的投影。我愿意靠近你,并愿你爱我。
伤感只是消沉的热忱。
任何人都能赤身裸体,任何感情都能饱满充溢。
我的感情开放了,犹如一种宗教。你能领悟这一点吗?任何感觉都是一种无穷尽的存在。
拿塔纳埃勒,我来教给你热忱。
我们的动作伴随着我们,就像磷光从属于磷一样;不错,它们使我们受到了耗损,但也构成了我们的光辉。
如果说我们的灵魂能有若干价值,那是因为它比别的一些东西燃烧得更炽烈。
我看见你们了,沉浸在乳白曙色中的广阔的田野;点点青色的湖啊,我沐浴在你们的波浪之中——欢乐空气的每一次爱抚使我绽唇微笑,拿塔纳埃勒,我要反复告诉你的就是这点。我要教给你热忱。
倘使我曾经知道过有什么更美的东西,那我告诉你的肯定便是那一些,而不是别的什么。
梅纳克,你不曾教我智慧。不是智慧,而是爱。
拿塔纳埃勒,对于梅纳克,我的感情曾超过了友谊,几乎等于爱情。我曾像爱一个兄弟那样爱他。
梅纳克是危险人物,你得怕他!他受到明智者的谴责,但他和孩子们却相处得很好。他教孩子们不要再只爱他们的家庭。他慢慢地教他们离开家庭。他使得他们的心灵一味梦想得到野生的酸果,并且念念不忘奇特的爱情。啊,梅纳克,我当时真想跟你继续共赴前程!可是你憎恨懦弱,并且教导我离开你。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有着许多奇异的可能性。假如过去不在现在之中投下往事的影子,现在就将装满种种未来。但是可惜,一种唯一的过去只能描绘一种唯一的未来——未来被投射在我们的前方,正像一座无限长的桥梁被投射在太空一样。
我们可以肯定,我们所做的,永远只是我们所无法理解的事。理解,这就是觉得自己有能力去做。尽最大可能去担当人性,这才是正道。
形形色色的生活啊,你们都曾使我觉得美好。(我在这儿对你们说的,是梅纳克过去告诉我的。)
我希望我已彻底了解所有的情欲和所有的罪恶;我至少曾给过它们方便。我整个的生命曾扑向多种信仰。某些夜晚,我如此疯狂,我几乎信奉起我的灵魂来了。我感觉到我的灵魂很快就要离开我的躯体——这些话仍然是梅纳克对我说的。
于是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面前,就像这个斟满冰水的杯子。这个冰凉的杯子被一个高烧病人拿在手中,想喝。他明知应该等待,但水是这样冰凉,高烧又使他如此口渴,他再不能把这爽口的杯子从他的唇边推开。他把这杯冰水一饮而尽。
人的幸福和人生意义的书简——《地粮·新粮》导读
地 粮
新 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