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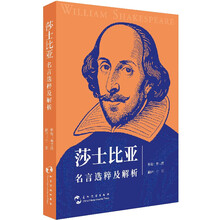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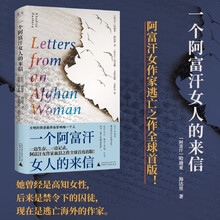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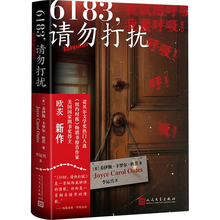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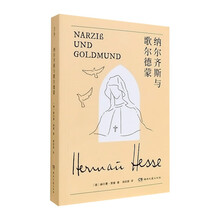

本书是当今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詹姆斯·伍德的小说首作。批评家写小说,自有与众不同之处。书中主人公身为延毕文学博士生,表达了伍德对学界众生相的观察和调侃。他与朋友、妻子、父母的关系又勾连起更大的社会脉络和思想空间。整体基调幽默易读,具有伍德标志性的敏锐和机智;其中对文学、信仰等主题的讨论又富有深意,体现了学者的博识。读者可以在阅读趣味和思想性方面都有所收获。
写不出的博士论文,忍不住下笔的个人写作项目,岌岌可危的经济状况,濒临破碎的婚姻,原生家庭的变故……
一个青年博士的学术挣扎和感情生活的困顿,在詹姆斯·伍德这部小说中得到了生动、犀利、风趣的展现。本书是他多年来真实生存经验及文学洞见的结合之作。由于自身的评论家特质,伍德在刻画这群英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群像之时,也用自己那种特有的柔情、优雅的品格,宽恕了他们的失常和冒犯,并为读者带来了这种社会较量以外的慰藉和情感力量。本书语言独到,灵气逼人,不仅是一本优秀的当代人物小说,更是对知识界身份的一种自我质询。
第一章
我三次不认我父亲,两次在他去世之前,一次在他去世之后。
第一次不认归咎于 《 泰晤士报》的讣告编辑。 那是差不多 两年前的事情了,那会儿我还和妻子简·谢里丹住在一起,但 我们总在争吵。我在伦敦大学学院教哲学,在学生眼中,我的形象总是带有一些浪漫色彩,甚至有点可怜。我的资历不太够格,教的课虽然也印在课程手册上——但用的是和主修课程颜色不同的墨水,不情不愿似的。 更侮辱人的是,大学竟然按小时付我薪水! 在其他教授眼里我跟死人没区别,在学生眼里我活得勉强,说到底二者也没什么不同。
我们陷入债务泥潭时,发小马克斯·瑟洛主动伸出援手。他现在是《泰晤士报》成功的专栏作家——那种一提笔就要援引塔西佗或穆勒的人——称其腹笥便便绝不为过。 他知道报社会提前准备好大人物的讣告,并且大部分都是自由撰稿人写的。因此,马克斯把我推荐给讣告编辑拉尔夫·海格利,建议他让我来写哲学家和知识分子的讣告。海格利遂邀请我共进午餐。我们在科文特花园一家高级餐馆碰面,这家意大利餐馆价格不菲,铺着雪白整洁的桌布,像蒸汽浴室里一样安静,奶酪堆得仿佛庞贝古城的废墟,手推车推着经过时悄无声息——我们坐在靠窗的一桌。成列的车停在窗外的街上,一个交通协管员从一辆车走到另一辆,手里拿着纸笔,俨然一位在餐馆里等客人点菜的服务员。海格利人到中年,脑袋奇大无比,脸色苍白,有一种病态的阴郁。他穿了一套像塑身衣一样厚的双排扣西装, 一条华丽的丝质领带打成鼓鼓囊囊的结。奇怪的是他脚上的鞋却异常孩子气——像拖鞋一样柔软而有弹性。 “我的脚不太好。”他注意到我下移的视线,解释道。
“如果你不介意,容我来帮你点菜吧,”他说,“这家餐厅的菜单还是有讲究的,我花了好几年才搞清楚这里头的名堂。”他一边说一边环顾四周,露出奇怪的轻蔑。
海格利说,自由撰稿人会提前为某些“候选人”写好讣告。他尤其关注那些公认身体欠佳,或年老体衰的哲学家。他一边不耐烦地鼓捣裤兜里的钥匙串,一边报出一连串名字。
“阿尔都塞怎么样? 他快不行了,是吧? 可能快轮到他了。还有另外一个住在巴黎的老兄,那个罗马尼亚人,齐奥朗。我听说他现在也不太好,罗马尼亚人的基因啊……有没有美国人? 我们总是会漏掉美国人,他们一旦挂了,我们就得加班赶工。我不喜欢赶工。其他报纸才这么做,对不对? 哦,我们需要找人更新一下波普尔那篇了,稍微润润色。我听说他好像有点病恹恹的。”
我心领神会。但由于对哲学家的健康状况一无所知,我只能现编一些。
“据说,”我说,“几个伦敦大学学院的同事都跟我说过,伽达默尔的情况不太乐观。”
“好极了! 把他加到名单上。”一如既往,我在撒谎时感到浑身燥热,一阵晕眩。
“众所周知,德里达也一直病病歪歪的。”
“是吗?那我们可得锁定他,在他……自我解构之前——这不是他的原话吗? ”
午餐结束,我带着四项委托任务离开— ——齐奥朗,波普 尔,伽达默尔,德里达——每篇两百镑。
但我一篇也没写。别的事情妨碍了我。七年来,我一直想要写完我的博士毕业论文,但我好像总是不喜欢把事情做完。最近我就为一本名为 《虚无笔记》的个人写作而冷落了博士论文。在这本书中,我选摘了一些宗教和反宗教引文,由此展开一套关于神学和哲学问题的个人阐述。我已经不知不觉写了满满四大本笔记本,对我个人而言,它好像真成了我毕生的工作。每当我准备着手写那几篇该死的讣告时,总是恰好迸发出对那本书至关重要的灵感,那一天我就会完全沉浸在神学和反神学的思绪中。
终于,海格利厌倦了等待,写了一封语气激烈的信给我。他在信中抱怨自己已经白等了三个月,却什么也没有收到。 他是否还应该视我为拟发讣告的撰稿人? 我一向不能很好地应付压力。我很想留在海格利的订货单上。突然间我意识到,要解释拖延的原因,得到海格利的同情,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他知道,最近我一直在处理一篇最为迫在眉睫的讣告:我告诉他, 我的父亲在一个月前去世了,悲痛中我无法处理手头的各种事务。海格利回信表示哀悼。于是乎我想拖多久就可以拖多久了。
这个办法如此奏效,以至于当我在一个月后收到税务局的来信,列出了我多年来从事各种兼职工作的未缴税款时,我又故技重演了一回。通常我都直接忽略这类信件,但这封信以咄咄逼人的气势逼视着我。不知何故,我的名字是用加粗的大写字母打印的:托马斯·邦汀。我打开它,发现自己被传唤去温 布利出席一个“听证会”。我要在那里接受政府审计人员的“评估”。如果有任何情有可原的理由导致我迟迟未缴税,我应该提交一份书面说明,并在听证会上宣读这份说明,作为自我辩护。
这就是为何三个星期后,我坐在一张办公室常见的,泛着人造光泽的焦糖色桌子旁——对面坐着四个穿西装的男人,其中一人在朗读我的信。我在信里解释道,由于我父亲最近去世,处理遗产相关的事务十分繁琐,导致我没能及时纳税。我对目前的状况感到十分抱歉,但过去三个月里本人一直处在悲痛和震惊中,无暇顾及此事,是否可以寄望于评估员对此抱有宽容和同情 (这个词下面加下划线),愿意再宽限我六个月时间补缴税费? 读信的男人瘦骨嶙峋,声音单调乏味,如果闭上眼睛,几乎可以肯定他手上在忙活别的事情。我始终低垂着眼睛,竭力表现出悲恸欲绝的样子。
延期缴税被批准了。当然,我父亲那会儿还活着。我算准了这种极端措施会奏效。但如果我知道父亲在我写完这封信后一年内就去世了,我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们无法计划谎言的后果。
第三次“不认”发生在我父亲去世后,这并不是谎言,但那时却感觉像谎言。今年夏天,我在哈罗德百货公司的地下搬运部打工,我告诉部门经理吉米·马德罗斯,我父亲刚刚去世,因此无法继续在这里工作。我说的是实话,但感觉却像在撒谎,因为我立刻看出他并不真的相信我说的话。我感到很委屈——我没有撒谎,难道不该为此得到表扬?正如《塔木德》里的一句箴言所说,“没机会下手的贼还觉得自己是一个诚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