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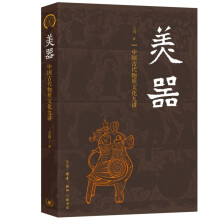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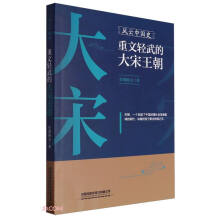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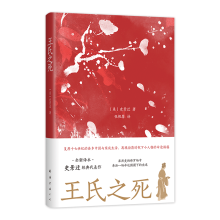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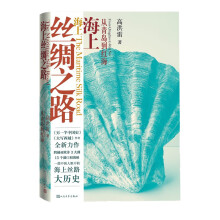
1. 大学问“实践社会科学系列”017号,一部法律史领域研究中国妇女财产继承问题的经典之作。柏清韵、伊佩霞、步德茂等知名学者曾撰文评论英文原版,《亚洲研究杂志》《太平洋事务》等顶尖学术期刊刊登书评,“它的出现,给学界重新思考妇女与财产关系以及整个的中国财产继承制度提供了富有新意的参考”;
2. 从妇女史视角出发,聚焦女儿、寡妇、妾等不同群体,展现中国妇女财产权利的演变过程。以往研究多从男性角度研究中国的财产继承,本书则转变视角,考察当一个家庭中的男性子嗣缺席时,女性的财产权利会发生什么变化,并厘清了前人研究中对妇女财产权利的误解;
3. 从法律层面窥视妇女与财产继承的关系。作者以引起冲突而闹到官府的财产继承案例为研究对象,以法庭判词和档案材料为研究凭据,以特殊见一般,带领我们从法律的层面窥视了妇女与财产继承的关系;
4. 考察了宋代至民国的妇女财产权利变化,使我们对于近千年来的家庭财产分配制度有了更加丰富、感性的认识与理解;
5. 史料丰富翔实。书中运用了判词集、地方官员日记、法庭档案等多样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并且,作者对史料进行了精心编排,让枯燥的法律文本变得具体可感;
6. 案例生动鲜活。如在论证明清寡妇的财产权因贞节崇拜而得以扩张、民国民法对寡媳产生不利影响等观点时,插入了丰富生动的案例,将诸般案件的审批过程娓娓道来,读来引人入胜;
7.语言简洁明快,论述清晰,译文精准流畅,可读性强。
◎编辑推荐一
以往研究对中国家庭中的财产权利多有两个误解:一是认为女性没有继承财产的权利,中国家庭的财产通常由男性子嗣继承;二是由此出发,以男性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历代财产继承权并无变化。白凯老师的《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一书从女性视角切入,通过研究大量案例,说明女儿的财产权利体现为继承权,而妻子或妾的权利体现为对家庭财产的监护权,宗祧继承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围绕这一论题,书中做了许多精彩的论述,如宋代女儿的财产继承权源自国家财政对绝户财产的需要、贞节崇拜对明清强制侄子继嗣法律的冲击、民国时期对妾这一身份的否定导致该群体的分流,等等。该书虽然篇幅简短,但却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作者用语之简洁明快,逻辑之清晰流畅,学术功底之深厚,可见一斑。
书中运用了大量生动的案例,作者将案件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使当事人之间的冲突情形跃然纸上。许多案件经历了多次上诉,特别是在法律变革时期,各级司法机构甚至有可能给出截然相反的判决。作者对其一一解读,展示了看似简单的法律条文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考量,司法活动中产生的判例又受到何种社会观念的影响,如何对既定的法律条文形成修订或补充。清末至民国时期,法律观念与社会惯行之间的冲突表现得尤为明显,发源于西方的财产观念与中国传统的社会现实不相匹配,有的群体从中获益,有的群体则显得无所适从。本书长时段的考察,使我们直观地看到传统法律与近代法律巨大的逻辑差异,从而得以体会新旧交替时期纷繁复杂的社会景象。
◎编辑推荐二
说到财产继承,今天的我们都知道,男女享有平等的继承权。然而,在数千年历史中,男性与女性在财产继承中一直存在巨大差异,甚至可以说,谈到古代社会,恐怕有许多人会认为那时的女性与财产继承无关。其实,女性的财产权利走到今天与男性平等的地位,经历了一条漫长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所需的远不只是法律的改变。而近千年来中国家庭财产继承和妇女财产权利的演变过程,在白凯老师的《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一书中得到了充分展示。
民国时期是社会剧烈转型时期,在法律领域,我们也可以看到强烈的新旧对比。许多女性因为新民法获得了属于现代社会的财产权利,随之而来的便是大城市中急剧增加的财产诉讼。例如,晚清著名实业家盛宣怀的遗产便带来了旷日持久的争执,盛家人前前后后打了至少七场官司,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他的两个未婚女儿盛爱颐、盛方颐相继提起的诉讼,这在当时广受关注,后来甚至被编成了一出名为《小姐争产》的戏剧。在本书所列举的诸多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女儿对家产提出的诉讼,只要符合新民法的时限要求,基本都能胜诉。
但法律的转型还隐藏着更深的冲突:同居共财的社会与财产归个人所有的法律观念简直可说毫不相容,民国女性在财产继承中的劣势基本由此而来。由于财产属于个人,寡妻在与子女分别继承财产后,不再有权置喙属于子女的财产,而从前她们对家庭中的所有财产都拥有监护权;寡媳也不能在分家时获得财产,因为她的丈夫死时尚未得到任何财产,而她也不是自己公公的法定继承人。法律逻辑的转变让来自传统社会的妇女群体显得无所适从,这便是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在此之后,社会中的妇女群体被重塑,守贞寡妇、妾等群体逐渐消失,现实与法律适配,男女的财产权利方才达致真正的平等。
古代中国的女性是否拥有财产继承权?在男子缺席的场景下,女性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当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型时,新的法律观念又如何影响着女性的财产权?
一部法律史领域研究中国妇女财产继承问题的经典之作。本书从妇女史视角切入,聚焦女儿、寡妇、妾等不同群体,以大量复杂而生动的案例,讲述中国女性从宋代至民国的财产权利变动,揭示了近千年来中国家庭财产继承和妇女财产权利的演变。同时,本书从法律的层面窥视妇女与财产继承的关系,检索历代司法资料,观察有关妇女财产权利和财产继承的法律表达与实践,给学界重新思考妇女与财产关系以及整个中国财产继承制度提供了富有新意的参考。
民国民法中的财产和继承概念展现出与传统社会惯行截然不同的逻辑,这对各种妇女群体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对寡媳而言,民国民法中的财产继承原则使她们在家庭中陷入了更为不利的境地,她们(尤其是无子女的寡媳)对家庭财产不再享有任何权利。
——编者按
民国民法中寡媳的继承权
如果说民国的民法对寡妻来说至多只是利弊参半,那么对于寡媳,即那些在数代同堂的家庭里与亡夫父母住在一起的妇女来说,它不啻一个灾难。因为民国民法不仅剥夺了她们在旧法律下所享有的监护权,而且未能给予她们寡妻所享有的继承权。
对寡媳的完全剥夺虽然不是出于民法的本意,却是体现在民法中的截然不同的财产和继承概念的逻辑结果。在帝制后期和民国初年的法律中,财产被认定为家庭的财产,每个儿子都有一份。如果一个儿子死了,他的那一份将在分家时被给予他的男性子嗣。如果他没有男性子嗣,这份财产就由她的寡妻(只要她未再醮)监护。不论他死于他父亲之前或之后,他的寡妻对其在家产中的份额都有此权利。即使她的丈夫死于他父亲之前,她在分家时仍对其丈夫在家产中的份额拥有此权利。
然而在民国民法中,如果一个已婚的儿子在他父亲之前过世,他的寡妻在公公死时就不能得到任何财产。对寡媳继承权的否定是民法中个人财产概念的逻辑结果。由于家庭财产现在被视为父亲个人独占的财产,当父亲活着时,这财产没有儿子的份。因此,如果他死于父亲之前,他就不能得到任何家产以留给他的寡妻。当他父亲死时,他的财产将只分给他的法定继承人(他的寡妻,他健在的子女或孙子女,等等)。一个寡媳对此毫无权利。这与1928年继承编草案中的规定有所不同。草案允许配偶一方在这种情况下继承另一方的法定份额,就像子女可以继承父母的份额,如果父母死于祖父母之前的话。(张虚白,1930:80)这一规定后来修改为只有直系后代可以享受这样的权利。
这正是北平一个36岁寡媳屠贾静园所遭遇的命运。1941年末,她和14岁的儿子屠桂芬向北平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她的两个姑娘(她公公屠逊庵的女儿),屠宝玫和刘屠宝玢,和她公公的57岁的妾——屠刘氏。诉讼的标的是对屠逊庵财产的分割。屠逊庵是一个前清官僚,在长期的官宦生涯中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于两年前去世。寡媳屠贾静园争论说她公公的财产应分作五份,一份归她,一份给她的儿子,两个姑娘各得一份,还有一份给屠的寡妾养老。
北平地方法院判决寡媳败诉。因为她的丈夫比她公公早死十年,所以她对她公公的财产没有任何权利。和她公公的寡妾一样,她所能得到的最多只是一笔赡养费(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讨论)。法官命令将屠逊庵的遗产分成三份,屠贾静园的儿子(屠逊庵的孙子)得到一份,其余两份则分给两个姑娘。(北京地方法院:1942-556)
为了凸显法律中的这个漏洞,让我们来假设屠贾静园的丈夫死于他父亲之后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当屠逊庵死时,他的财产将在他的三个子女,即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之间均分。然后当儿子死时,他的那份财产将由他的寡妻和儿子桂芬来均分。这样,屠贾静园作为寡妻将得到屠逊庵财产的六分之一(她与她的儿子分享她丈夫所得的三分之一家产)。但是现在,仅仅是因为她的丈夫死于其父亲之前,屠贾静园什么也得不到。
在最高法院1932年审理的一个上诉案中,寡媳权利在旧法律和新法律之间的不同暴露得淋漓尽致。在这个案例中,家住江西南昌的寡妇柯魏氏对她亡夫的两个兄弟和另一个兄弟的寡妻就分割死去公公的财产提起诉讼。她争论说作为一个无子女的守贞寡妇,她有权得到她丈夫应得之家产的一份。她的姻亲则争论说因为她的丈夫死在其父亲之前,所以她对这财产没有任何权利。对审理上诉的最高法院的法官来说,案情的关键是寡妇公公去世的日期。如果他死于新民法颁行之前,那么他的寡媳柯魏氏就有权得到她亡夫应得之家产的一份,正如她所要求的那样。如果他死于新法颁行之后,那么柯魏氏就没有这样的权利,就像她的姻亲所强调的那样。结果法官们确认了她的公公死于新民法颁行之前,于是根据旧法律判给她其亡夫应得的家产。但他们也明确告诉她,如果她的公公死于新民法颁行之后,她就什么也得不到。(《最高法院判例汇编》,1929—1937,13:21—24)
有子女的寡媳要比没有子女的寡媳的处境好得多。如前述屠寡媳的情况,虽然她们本人没有继承的权利,但她们的子女,作为死去公公的孙子女有继承的权利。所以她们至少是幸运的,因为有子女可成为她们生活的依靠。
无子女的寡媳甚至连这样的后路也没有。根据民国民法的规定,她们不能通过过继来得到她们公公的财产。如前所述,一个妻子在丈夫死后所过继的任何子女都不被认作丈夫的子女和他的法定继承人。据此,他们也不被视为她公公的孙子女,因此对她公公的财产没有任何权利。(《司法院解释例全文》,1946:第851号)
根据民国民法,寡媳所能要求的最多只是她夫家对她的继续赡养,即使这一点也是有条件的。如前一章所解释的,民法第1114条规定四类人有相互扶养的义务:1.直系血亲;2.夫妻之一方,与他方之父母同居者;3.兄弟姐妹;4.家长和家属。寡媳的扶养属于上述的第二类和第四类。这两类的共同要求是受扶养者必须与扶养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因此寡媳能否从她公婆那里得到扶养的权利(属第二类),或当公婆已死时从她亡夫的兄弟那里得到扶养的权利(属第四类),就完全取决于她是否仍和他们住在一起。若她因任何理由而迁出别居,他们的扶养义务就终止了。
最高法院在1933年的一个判决中对这一点表达得很明确。江苏仪征县26岁的年轻寡妇向本曹对她现居湖北汉阳的公公和姻兄弟提出诉讼,状告他们的各种虐待和侮辱,并要求法庭判决他们提供扶养费让她别居他处。最高法院拒绝了她的要求,指出公公对寡媳、叔伯对寡嫂和寡弟媳的扶养义务只限于双方住在一起。“若不同居则不问其原因如何皆不得有请求扶养之权利”。(《最高法院判例汇编》,1929—1937,27:12—14)
在1933年的另一个判例中,最高法院走得更远,认为寡媳即便被其姻亲赶出家门,也不能要求他们扶养。在这种情况下,恰当的做法是由寡妇提出同居的诉讼,迫使她的姻亲让她返回他们的家。一旦实现了这一点,他们当然就有法律义务来扶养她。(《最高法院判例汇编》,1929—1937,21:105—107)
民法中这一同居的要求对寡媳来说是雪上加霜。因为在过去,如果她们搬出别居,只要法庭认为她们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她们就可以期望从姻亲那里得到扶养。例如陕西咸宁县知县樊增祥在1890年代对寡媳翁车氏做出了有利的判决。翁车氏要求法庭允许她和两个女儿搬出她公公翁慎修的家。樊增祥认为寡媳和她的姻亲间关系已经如此恶劣,若强迫他们继续住在一起,只会产生更多麻烦。他因此命令翁慎修拿出十分之三的家产,让其寡媳和她的女儿自立门户。他还特别说明寡媳翁车氏只能用这份家产的利息来生活,而无权出售、典当这份财产,也不能在女儿出嫁或她本人过世时把它传给她们。(樊增祥,1897:43—44)
民国初年的法律和清律一样,给寡媳留下了一定的法律活动空间(《大理院判决例全书》,1933:254)。在1920年代中,新寡的马张氏用了基本相同的理由从她十分不情愿的公公马邻翼手里得到了价值13 500元的扶养费。京师地方审判厅、京师高等审判厅和大理院都认定由于几年前她与丈夫马骞之间的一场恶性的离婚官司,马张氏无法在夫家住下去。这场离婚诉讼由马骞提起,但被判败诉,事后马骞和马邻翼一直拒绝马张氏搬回居住。现在马邻翼称他愿意让寡媳住回来,并争论说公公没有义务扶养不住在一起的媳妇。京师高等审判厅在其判决中提醒他说,扶养的义务取决于一个人的身份。马张氏仍是马骞的妻子、马邻翼的媳妇,只要她仍旧持有这双重的身份,她就有权得到扶养,而不论她住在哪里。(京师高等审判厅:239-7956;北京地方法院:65-5-369-385,65-5-458-463)
一旦同居成为寡媳有权得到扶养的唯一条件,法官甚至不必再去探讨分居的原因或评估诉讼双方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例如,在1942年北平的一个扶养案例中,30岁的寡媳邓李秀葵状告她的公公和其妾对他们夫妇如何虐待和凶狠,以致她的丈夫得病而死。她害怕自己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因此跑回在通县的娘家。她的姻亲对她提出反诉来加以报复,指控是她泼悍刁横气死了丈夫;还指控她不守寡妇本分,经常穿着光鲜离家外宿。对审案的法官来说,所有这些控词真实与否无关紧要,寡妇和她姻亲之间的明显仇视也与断案无涉,唯一重要的是她已不再与他们住在一起。因此根据法律,他否决了她提出的扶养要求。(北京地方法院:1942-6931,1942-7097)
对寡媳的这个新的要求是民国民法对扶养权利重新规定的结果。在过去的法律中,一个人受扶养的权利不仅仅基于亲属关系或同居关系,而且是建立在“同居共财”的集体成员资格之上的。作为该集体的成员,他或她有权得到家产的扶养。与民国民法中的用法相对照,“同居”并不能按其字面意义仅仅理解为住在同一个居所。如大理院曾经在另一场合解释过的,与同居相对的不仅仅是“异居”,而是“分财异居”。(《大理院判决例全书》,1933:209;并参见仁井田,1942:350—352;滋賀,1978:111—112)只要家产还未分析,一个人无论住在哪里都被看作家庭中的一份子,作为同居共财集体中的一员,他或她就因此对这个集体享有充分的权利和义务。正是根据这个逻辑,寡媳在过去的法律中享有受扶养的权利,即使她已不再与夫家姻亲住在一起。除非她重回娘家并与娘家同财共居,或再嫁到另外的家庭,她仍是她夫家的成员,并因此有权得到夫家财产的扶养。
但是一旦家庭财产成为父亲的个人财产,扶养的权利就与财产脱钩,而只与人相关。民国民法关于扶养的两个要件,亲属关系和共同居住,都体现了这种特征。因此当扶养是基于亲属关系时,一个无力养活自己的人有权得到他兄弟的扶养。这一权利针对的是他兄弟本人,而不是他兄弟所拥有的财产。从民国民法的立场来看,这两人是否同属一个同居共财的家庭,或他们是否已经分家建立了各自的同居共财的家庭,是无关紧要的。
同样的,当扶养是基于共同居住时,家属有权得到家长的扶养,这一权利针对的也是家长本人,而不是他或她所拥有的财产。不仅如此,“同居”在民国民法中指的也只是共同居住;它绝不是同居共财的简称。正因为如此,一旦同居终止,家长提供扶养的义务也就相应终止。正是根据这一逻辑,在民国民法中,寡媳只有在继续住在夫家时才有权得到夫家的扶养。
与立法者们所声称的相反,民国民法给予寡妇的权利并不一定比她在“封建的”过去所享有的多。确实,新的民法继承编赋予了寡妻得到一份她丈夫遗产的权利,但其代价是她丧失了对所有家产的监护权。贯穿着西方财产逻辑的民法与过去的法律不同,它没有给寡妇留下监护家庭财产的任何特殊权力。家庭财产现在被看作她丈夫的个人财产,她对这财产所可能有的权利不比任何其他法定继承人多出分毫。
同样,以西方逻辑为基础的民法也没有给寡媳留下任何财产权利。以前她可以继承她丈夫在家产中之份额,即便她丈夫死于其父亲之前。而将家产重新定义为她公公的个人财产意味着现在她对这财产没有任何法定的继承权利。由此她完全丧失了在旧的法律制度下所享有的监护权,却没有得到寡妻从新民法中所得到的继承权。同样地,根据重新定义的扶养权,她从夫家得到扶养的权利被严格限定在同居的范围内。因此寡媳在民国民法中遭受了双重的损失。
——选自[美]白凯著、刘昶译《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7月
导言
第一章 宋代至清代女儿的继承权
第二章 宋代至清代寡妇的继承权
第三章 寡妇与民国初期的宗祧继承
第四章 民国民法中的财产继承
第五章 民国民法中寡妇的继承权
第六章 民国民法中女儿的继承权
第七章 帝制和民国时期妾的财产权利
结论
引用书刊书目
索引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