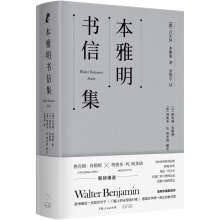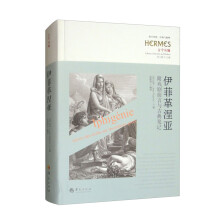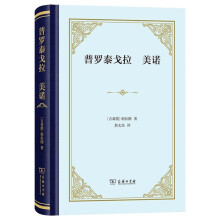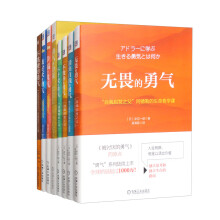反对自我的思想
我们所有的发明几乎都归功于我们的暴力,我们不稳定的加剧。即便上帝,袍令人好奇,我们领悟袍,也不是在自我的最深处,而是在狂热的外限处,正是在那里,我们的愤怒,在面对袍时,产生一次冲撞,既毁灭袍,也毁灭我们的一次相遇。诅咒随行,令人发疯,暴力者本性上是一个侵略者,怒不可遏就会故态复萌,听凭自己的冒险心,因此惩罚他们就是煽动他们。每一部作品都会和它的作者反目成仇:诗歌会让诗人郁郁寡欢,哲学会让哲人精神崩溃,事件会让活动家身败名裂。任何回应感召的人、履行天职的人、在历史之内奋斗的人,必自取灭亡。唯有放弃全部天赋才干,方可自保。唯有摆脱人性,方能慵懒地躺在存在之中。如果我有志于一种形而上学的职业,我将无法保留我的个性,即便不惜一切:我所剩余的,无论是什么,我都会将其清除;相反,如果我肩负一个历史使命,我会责无旁贷地激增我的才智,直至和它们同归于尽。人总是毁于人所假定的自我:承担一个名字就是宣告一种确切的死亡方式。
暴力者,忠于其表,败而不馁,虽能重整旗鼓,但刚愎自用。为何他会猛烈地毁灭他人?那是为了迂回地毁灭自己。在他的自信下,在他的夸夸其谈下,他所隐藏的是一种幸灾乐祸。因此暴力者的敌人就是他们自己。我们都是暴力者——愤怒之人,我们丢失了保持清静的关键,只能去往撕心的秘境。
为了不让时间消磨我们,最好的办法是超越它,将我们的瞬间加入它的瞬间。此新的时间是对旧时间的移花接木,此时问虽精心策划,但不久会露出它的阴毒:此客体化的时间,将成为历史,成为一头我们召唤出的反对我们自己的怪兽,一场我们无法逃避的命运,即便求消极药,问智慧方。
我们将尝试一种无效的治疗;沉思那些道家老祖,沉思他们的弃世之道、放任之道,沉思“不在”的至高之道;如他们一般,去追随这种意识过程,当它停止与世界争斗,并像他们所钟爱的元素水那样与万物交融时——我们则永远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他们既鄙斥我们的好奇心,也鄙斥我们的痛苦欲望,这是他们有别于神秘主义者,尤其是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的地方,后者善于向我们推荐刚毛衬衣、铁刺皮鞭、失眠、饥肠、呻吟,并视之为美德。
“强梁不道”,老子教诲道,如果真的存在老子这么个普通人的话。但我们都是自笞者的后裔,借由精炼自己的肉体痛苦,我们获得了“自我”意识。宗教日薄西山了?我们使它的谬行永垂不朽,因为我们念念不忘它的苦行及斗室中的哀鸣,我们的受难意志与全盛时期僧侣们的旗鼓相当。或许教会不再享有地狱的专利权,但它已让我们叹息连连,膜拜神意,摧毁欢乐,狂喜绝望,不能自拔。
精神、肉体同样,都将为“强”付出代价。尼采、波德莱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技艺精湛、反对自我的思想大师都曾教导我们要将希望寄托于我们的危难,要拓宽我们疾病的范围,要用划分我们的生命来获得存在。在伟大的中国人看来,那些都是衰败的象征、瑕疵的练习;对我们来说,那些构成了我们掌握自己、接触自己的唯一方式。
“人无情,则无伤。”(庄子的观点)箴言,总是深刻的,也总是无用的。冷漠至极,如何达到?当我们麻木不仁时,是紧张,是冲突,是攻击?我们的祖先中没有圣人,有的是满腹牢骚之人、游戏人问之徒、狂热盲目之辈,他们令人失望,放纵无度,我们将步其后尘。
P1-4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