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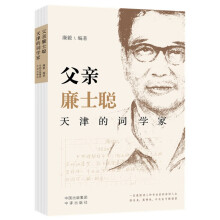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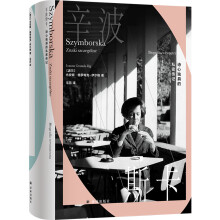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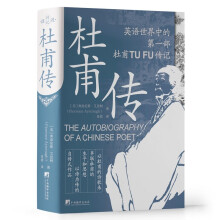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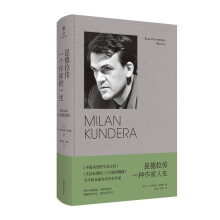
刘小川“品中国文人”系列全新力作,讲述“我的邻居”苏东坡之全才全能、身心灵动、好吃好玩与好学,重现千古文人的低沸点人生。
【千古罕见的热血智者】
苏东坡一生坎坷,颠沛流离,他的人生可谓大起大落:曾官至翰林学士,也曾入狱成为阶下囚,居庙堂之高,又处江湖之远。数次被贬,在汴梁、眉州、密州、徐州、黄州、金陵、惠州、儋州、常州等地频繁奔走。
这一切最终造就了“强大的普通人”苏东坡:既有强者特质,又有艺术家的自觉;既能以灵感照亮自己,又能兼爱身边的朋友和陌生人。
【鱼鸟之性的生活大师】
东坡居士天性乐观,走到哪,吃到哪,写到哪——东坡肉、东坡羹、烤羊脊骨、河豚、烧笋……
“万人如海一身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一蓑烟雨任平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颗旷达之心,一种鱼鸟之性,成就快乐通透的苏东坡的一生。
【人生的低沸点欣悦】
庄子齐生死,齐荣辱,齐万物,乃得身心大自由,六十年居陋巷,与百工相善,与劳动者为伍,维系了低沸点之欣悦。
陶渊明四次投耒,出门去做官,四十多岁彻底归园田,朝夕与素心人相处,将低沸点的欣悦发挥到极致。
苏东坡跃入生活的万顷波浪,遍尝人间烟火,逐渐领悟了那些旷野一般朦朦胧胧的欣悦——诗意地生活,不去算计天地,这就是人生的低沸点欣悦了。
的邻居苏东坡
眉山地处成都平原的南端。苏洵说:“古人居之富者众。”
两宋三百余年,仅一个眉山县就出了九百零九个进士,高居全国州县之首。成都(当时叫益州)不能比的。苏东坡考进士乃是事实上的状元,制科殿试又拿了百年第一,所以我称他是宋代唯一的“双料状元”。
这个状元后来干了很多大事,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小时候我不知道苏东坡厉害,他的家和我的家相隔一百多米。他的家八十几亩地,我的家二十几平米。他一天到晚坐在大殿里,看上去委实有些阴森森哩,大殿外还有一口苏家的井。那井水我喝了不少,甜丝丝的,凉浸浸的。井边一棵光秃秃的千年黄荆树,据说苏洵用黄荆条打得小苏轼双脚跳。我是眉山下西街出了名的调皮捣蛋的费头子(孩子王),但凡听到苏东坡挨打,就乐得咯咯笑。苏东坡也属于下西街嘛,论板眼儿(戏耍花样)肯定不如我。他挨打的次数也不如我,差远了。当时我在城关一小上学,课余练武功正起劲,崇拜豹子头林冲,认为区区苏东坡不值一提。林冲雪夜上梁山,苏东坡连峨眉山都没爬过。武松醉打蒋门神,苏东坡在乌台监狱里挨几下就痛得遭不住,真是不经打。他酒量差,当然我的酒量也不行。他下棋不行,我下棋还可以。他下河游泳一般般,我九岁那一年就横渡了岷江,弄潮拍浪一千五百多米,浪高一尺啊。他在书房南轩看书,摇头晃脑念子曰诗云,我家没书房,我在后院的柚子树的树杈上躺着看书,看了四大古典名著,看了《铁道游击队》,看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别林斯基、莎士比亚……
从小学到高中,我跟那个名叫苏东坡的人较劲。
每当爸爸找不到我的时候,妈妈就会说:到三苏公园去看看。
哦,妈妈。现在是二〇二一年的深秋了,妈妈在哪儿?
三苏公园啊,下西街文化馆,工农兵球场,电影院,招待所,我何止去过三千回。一年四季,同学们伙起,一个个勾肩搭背东耍西耍,淋坝坝雨,淋阵雨、偏东雨,享受大风中的那种近乎窒息的感觉。爬高高树,跳高高墙,比高高尿,呆望永远神秘的高高的夜空。男孩子打架,梁山好汉不打不相识嘛,打出了友谊,也打宽了雄性渠道,学校哪有小鲜肉的市场?通通靠边站。
话说硬汉海明威,倒提小鲜肉扔进了汪洋大海。
我在说什么呢?说灵动,身心的灵动。
拙作《品中国文人》(五卷),写了历代五十个大文豪,发现早年的释放天性乃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天性不能释放,创造性是要大打折扣的。学自然科学的学生也不例外。
苏东坡小时候是个“三好”学生,好吃,好玩,好学。他的母亲程夫人,他的乳娘任采莲,平日里做菜变着花样,苏东坡就成了好吃嘴,后来自创了东坡肉,东坡饼,东坡鱼,东坡羹,东坡泡菜……他又把眉山的美食带到江浙一带。我吃上海、杭州的东坡肘子,觉得还是眉山的好。
四川人都好吃,川菜很精细,单是肉丝肉片就有十几种。苏东坡出息了,出川做了大官,牛羊鱼吃得多,猪肉吃得少。四十多岁贬到黄州后,他开始研究猪肉,写下打油诗《猪肉颂》。他对水果也有研究,在汴京南园栽石榴树,在江苏宜兴栽橘树三百棵,在广东惠州尝试栽荔枝、桂圆。他写诗给堂弟说:“我时与子皆儿童,狂走从人觅梨栗。”我抓住这两句,发现少年苏轼的狂走。他上树上房摘别人家的梨子板栗么?杜甫诗云:“忆昔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八月庭前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当年我在三苏公园里游荡,惦记着人道是苏东坡栽下的荔枝树,丹荔挂满了枝头,一颗颗的馋人。嗖嗖嗖上树去也,拨开交叉的绿叶,摘了丹荔,剥了皮,一个劲儿往嘴里塞。眉山人叫吃得包嘴儿包嘴儿。要赶紧的,要眼观八方耳听六路,防着公园的干部或园丁。那一年的夏天,那个爽啊,树干上爽歪歪,吃了很久很久,剥了很多很多:大约三十三颗饱满欲滴的红荔枝。左右枝头吃光了,再往上爬,寻思摘它一书包,夜里占营时分给下西街的小伙伴们。忽然间,头皮顶了一团软软的东西,我心里叫声不好,撞上了吓人的野蜂窝。一群细腰蜂在头顶上散开,摆出攻击的扇形,这扇形我见过的。野孩子到处野,天上都是脚板印。刹那间我纵身跃下五米高的荔枝树,细腰蜂群闻风而动,嗡嗡嗡倒栽下来,有几只直扑我的寸头。大约五六只细腰蜂同时攻击我,头皮痛麻木了,旋即肿了半厘米,像戴了一项不想戴的皮帽子。我落下地发足狂奔,奔向三百米外的无限温暖的家……妈妈用邻居送来的乳汁揉我的头皮,揉了好久。
街灯初亮时,我又满大街疯去了。第二天晚上疯完了,照例往井台边一站,倒提满满的一桶井水,哗啦啦冲凉。
一九七〇年代的男孩子,在挫折中茁壮成长。
苏东坡诗云:“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
苏东坡词云:“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东坡小时候顽皮不如我,这个毋庸置疑。他家原是五亩园,后来被别人弄到近百亩。我念书的城关一小与三苏公园只隔了一堵青砖墙,翻来翻去很方便。记不清翻墙跳园子多少次,爬树摘鲜果多少次,弹弓射鸟、竹竿钓鱼,更不在话下。
苏东坡显然是我的好邻居,我去他家千百次。当初我有点瞧不起他,现在我尊敬他,我上班的单位研究他。
《品中国文人》写了那么多文人,平均三万字,唯独苏东坡占了五万字。当时我对出版社说:苏东坡是我邻居,能不能多写几页?出版社答复:苏东坡是十一世纪的集大成的天才,又是你的乡贤,你还吃过他家的三十多颗荔枝,多写苏东坡完全可以!
2021年冬改于眉山之忘言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