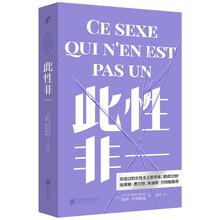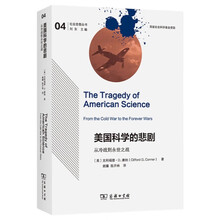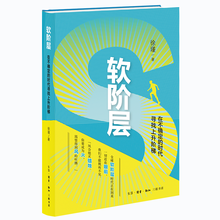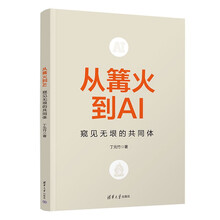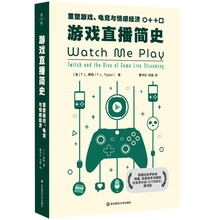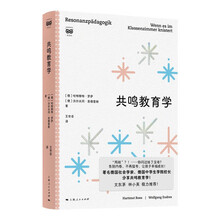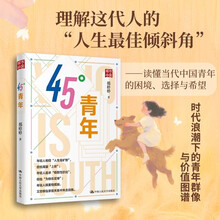《当代中国群团组织研究(2000-2021)》:
县委统战部对乡贤工作极为重视,要求全县每个乡镇、街道都要建立乡贤理事会,吸纳本地出身的政界、企业界、文化界精英,乡镇、街道担任业务主管单位,并且在民政登记注册为社会组织。镇里的乡贤有很多在外地做生意,甚至有几个乡贤在外创办了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平日里,这些乡贤都会进行捐赠,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筹措的款项用来协助镇政府开展助老、助残、助学、助困、修路等工作。
群团改革开始以后,MT镇致力于“群团共建”。“群团共建”,就是进行机构调整,集中镇工会、共青团、妇联的人力和资源,整合成立镇党群办,由其负责一体化开展群团工作。“群团共建”之后,MT镇由组织委员协助副书记开展群团工作。组织委员与分管统战工作的人武部长是高中同学,一直就有较好的私交。这层私交消弭了组织委员和乡贤理事会的距离。于是,在组织委员和人武部长的共同引导下,有乡贤在2017年的捐赠中,将捐赠资金投向了镇里的群团工作。例如,镇党群办打算在妇联工作中针对本镇留守儿童和随务工人员进城的本镇儿童开展教育帮扶工作。该项工作预算资金是12万元,但镇妇联本身的工作经费极其有限,这12万元资金完全是缺口。为此,在组织委员和人武部长的努力下,争取到了本镇乡贤王某的12万元捐赠。
镇党群办引入乡贤捐赠,旨在推动镇群团工作,这项工作的具体内容是对本镇的户籍儿童进行关爱,进而实现对本镇户籍人口的引领。在组织委员看来,“乡镇群团工作一怕没思路,二怕没资金。没资金比没思路更头疼。没思路可以主动走出去学,没资金就只能到处化缘了。”(笔者对组织委员的访谈,2017年3月,下同)按照MT镇的计划,这12万元被分成4万元和8万元两个部分。其中的8万元由乡贤王某直接捐给本镇乡贤理事会,然后由乡贤理事会在过年的时候对本镇有子女的家庭进行慰问。首先由各村挨家挨户分别进行统计。统计发现,该镇目前随在外务工父母的未成年人共有354人。然后在过年期间,由镇党群办和乡贤理事会一同为每名未成年子女送上200元的教育慰问金。另外的4万元,由乡贤王某捐给一家从事未成年人培训的教育类社会组织。这家社会组织由MT镇党群办从上海引入,在该镇专职对留守儿童进行心理辅导以及传统文化、书法、英语等培训。经统计,全镇共有留守儿童152名。针对8-18岁的学龄留守儿童,这家社会组织主要对其进行心理辅导以及书法、传统文化培训。针对6-8岁的非学龄留守儿童,主要对其进行英语培训。
对于乡贤王某而言,积极捐赠一方面是出于“在乡里乡亲中有面子”(笔者对乡贤王某的访谈,2017年3月,下同);另一方面基于一个背景,王某所在村的村书记在这届任期结束之后就要卸任。乡贤王某表示,“我是从村里走出去的,现在开公司赚了点钱,也想为村里做点事”。潜台词是,王某希望能够在老书记任期结束之后担任村书记。因此近一两年来,王某和镇里多个领导走得很近。村里的人和笔者谈起王某,“他这两年也给乡贤理事会捐了不少钱,好像每年都有,去年的钱用来修路了,今年就投到教小孩上了”。(笔者对村民的访谈,2017年3月)在访谈中王某表示,“我也不懂什么什么儿童,反正镇里(笔者注:指组织委员和人武部长)让我捐我就捐了”。王某追随组织委员和人武部长的建议把捐赠投向群团工作,就是为了拉近和镇领导的关系,从而实现自身的目标。
不管对党群办而言,还是对王某来说,募捐和捐赠都不是一个制度化行为,缺乏法律、法规层面的制度支持。它依赖镇领导和乡贤在特殊时期建立的临时关系。所谓临时关系,就是说关系建立依赖于特殊背景下的诉求,随着时间的推进,乡贤会因为个人诉求实现减弱捐赠意愿,关系将会逐步解体。这层关系并不受到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度性保障。组织委员说,“乡镇工作很难的,难就难在没有抓手。要推工作,不能没有抓手。没抓手,只好自己找抓手。”在组织委员的亲自介入下,妇联的这项工作顺利推开了。但推工作并不是因为法律、法规、政策赋予了可以利用的条件。在组织委员看来,这些具体做法都是临时性的,不稳定。“很多乡贤虽然有钱,但也不一定愿意拿出来,王某正好有这么一个背景,那就让他多参与一点镇里和村里的事务,他也愿意。”但同时,组织委员也坦承,“以后就不好说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