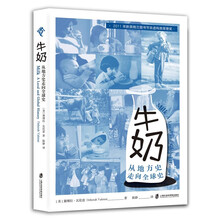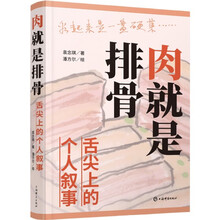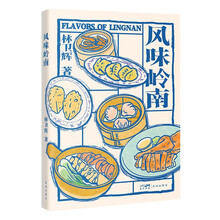牛肉锅
从柳絮先生的文章里,得知上海市上司盖阿盖名称的变化,很有意思。司盖阿盖原是日本语,其实直接的说还不只是牛肉锅么,虽然这在生意经上不很合适,因为太平凡了,不足以资号召。本来在日本这也是一种新的吃法,在明治维新以前是没有的,因为那时他们不吃牛肉,到维新时代大家模仿西洋,于是觉得面包牛奶非吃不可,牛肉也流行起来了。热血青年短发敞衣,喝酒烧牛肉吃,扼腕谈天下事,当时这便叫做“开化锅”的。司盖阿盖的原意是说把“薄切”的肉浸了酱油“烤”了来吃,实际与叉烧差不多少,后来才转变为用黄油甜酒酱油做底子,加人牛肉片以及葱和芹菜等,已经不是烤而近于炒与煮了。日本食物中蛋糕名贺须底罗,又以面粉包虾鱼蔬菜油煎食之,如北京所谓高丽什么的,名天麸罗,都从西班牙语转来,也至近世才有。中国称为高丽不知何故,北京且用作动词,如云把这去高丽一下子,但别处似无此语,大抵只说是面拖油炸罢了。
1950年12月29日载《亦报》烤越鸡且居先生说我们住在北方的绍兴人,再过一年,一定可必吃得到越鸡。这预约是十分可感谢的,不过说精通南北之味,那可使我很是惶恐,因为我也是只喜欢谈谈乡下吃食而已,那里够得上说通呢?诚然如孟子所说,鱼与熊掌都曾经吃过,或者可以说是有口福的了,可是熊掌并不好吃,只像是泡淡了的火腿皮,这固然是细条,但这种味道即使整方的咬了吃,也未必及得红炖肘子吧。猩唇豹胎,连看也没有看过,怎么会有资格可谈食味呢。我所觉得喜欢的还是几样家常菜,而且越人安越,这又多是从小时候吃惯了的东西。腌菜笋片汤、白鲞虾米汤、干菜肉、鲞冻肉,都是好的,说到鸡则如且居先生的意见一样,白鸡以及糟鸡,齐公所鼓吹的虾油鸡一定也很好,因为我们东陶坊没有这做法,所以不能加在里边。上坟时节的烧鹅,我也是很喜欢吃的,但烤鸡怎么样,那就很难说,锅烧鸡也不过是那么样罢,只是假如挂炉烧的,比煮的可能多保存些鲜昧。老实说,我对于烤鸭本不爱好,鸭并不好吃(腊鸭除外),其不能列于三牲之林,或者正非无故吧。(我的祖母,不吃扁嘴的,连鹅也不吃,那大概又是别一个理由。)1951年2月27日载《亦报》吃烧鹅春天来了,一眨眼就是春分清明,又是扫墓时节了。小时候扫墓采杜鹃花的乐趣到了成年便已消失,至今还记忆着的只有烧鹅的味道,因为北方没有这东西,所以特别不能忘记也未可知。在乡下的上坟酒席中,一定有一味烧鹅,称为熏鹅,制法与北京的烧鸭子一样,不过他并不以皮为重,乃是连肉一起,蘸了酱油醋吃,肉理较粗,可是我觉得很好吃,比鸭子还好。烧鹅之外,还有糟鹅和白鲞扣鹅,也都是很好的。北京有鹅却并不吃,只是在结婚仪式上用洋红染了颜色,当作礼物,随后又卖给店里,等别的人家使用,我们旁观者看它就是这样的养老了,实在有点可惜。大概这还是奠雁的遗意,雁捉不到,便把鹅来替代,反正雁也就是野鹅,鹅的样子颇不寒碜,的确可以替代得过。相传王羲之爱鹅,大抵也是赏识他的神气,陆农师在《埤雅》中说,鹅善转旋其项,古之学书者法以动腕,羲之好鹅者以此,乃是十足乡下人的话,未免有点可笑。羲之旧宅在蕺山下,后来舍宅为寺,颜日戒珠,后人望文生义,便造出传说来,云有珠为鹅所吞,疑人窃去,未几鹅死剖腹得珠,乃大恨悔,遂舍宅而称以戒珠云。案戒珠本佛教成语,谓戒如璎珞珠,如云以珠为戒,反为不词,至于鹅吞珠事见于《贤愚因缘经》,赞颂梵志的守戒与穿珠师的忏悔,反复唱说,是绝好一篇弹词,与羲之自无关系,惟以鹅故而被牵连说及,则亦不能说全没有因缘也。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