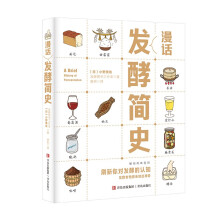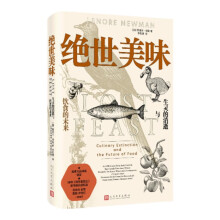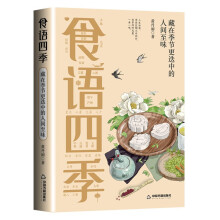艺术饭
我的朋友巫昂搬去了宋庄,租了一个大房子,三层楼,有大画室,有大院子可以种菜,顶层有露台可以做“仰望星空状”,能养狗,能养猫,冬天有地暖,工作台有好几个,早上在东边,迎着朝霞,下午在西边,送走晚霞,房租便宜,也就是在城里租个两居室的价钱,还不能是精装的那种。
我去找她玩,顺便观摩一下宋庄的艺术产业,满眼的艺术馆,造型各异的房子,壮观场面快赶上“大跃进”时候的大炼钢铁的小高炉了。满大街都能见到艺术家模样的人,他们或者光头,或者长发,或者穿着个性,其醒目程度超过一盘宫保鸡丁里的鸡丁,小炒肉里的肉片。
据说常年在此驻扎的各类艺术家诗人有3000人,有人想到这3000人的作品能卖多少钱,我想的是:得有多少餐馆才能满足这3000个挑剔的胃呀。依据我的经验,艺术家扎堆的地方必然是吃货扎堆的地方,艺术家走南闯北,吃吃喝喝,艺术有优劣,吃货无真伪,我寻思着,这群艺术家聚会聊天的主题也无非是:吃喝、挣钱、姑娘……
巫昂进庄半年,俨然已经是庄内人了,她知道哪里好吃,哪里蒙事。宋庄虽小,也阶级分明,小堡村相当于富人区,许多有名的艺术家居住在此,对于外地刚来宋庄的新人来说,这里就是“革命圣地”,方力钧、栗宪庭的住处就相当于杨家岭。而在餐馆吃饭,能去米娜餐厅,苹果树下吃大餐喝咖啡的,也已经事业小有成,而刚来的落魄分子,只能和批发画板画布的打工仔混迹在驴肉火烧、桂林米粉处填饱肚子。
米娜餐厅开了不少年了,算是宋庄情调餐厅的元老级别,这里的老板是一对艺术家夫妇,米娜是老板娘的名字,一个简朴的院子,弄得有情有调,有菜地,有竹林,一个玻璃做的大屋顶,阳光可以洒下来。服务员是聋哑人,点菜的时候只需用手指指点点即可,他们都聪明能干。许多造型各异的艺术人士中午来,吃一碗燃面,再悄然远走。这里做川菜,地道的川菜,巫昂和我推荐这里的毛血旺,我觉得孜然焗兔腿更妙,口感筋道,上面洒满花生碎,辣,但是过瘾。麻辣水人参,其实就是泥鳅。在中国的西南片区,做泥鳅是厨师的拿手菜,肥硕的泥鳅,去头,混以仔姜,泡菜,辣椒,再用黄瓜片打底,泥鳅入味,肉质细滑,也可以尝尝里面的姜片,是一种动情的酸辣,有点冲,好吃;打底的黄瓜微微脆,其实我觉得如果在里面再加入一点魔芋也是不错。
好吃,但是总觉得太“宋庄”了。类似“宋庄style”的馆子还有苹果树下,艺术的劲头太足了,有点像放了鸡精的汤,鲜是鲜,吃多了容易口渴。我想找的是那种“给你一下子”的小馆子。
看电影我喜欢看“全片无尿点”的那种,吃小馆子我喜欢吃“菜单可以点一本”的那种,我又偏好重口味,巫昂跟我很对路,马上领着我去了另外一家,叫湘菜香。有点不好找,小馆子旁边都是卖画框画布的小店,算是艺术家们的配套工种。巫昂还在一家装裱店停了一下,原来她是取自己的画。原来这个女诗人、专栏作家、笔迹分析者、心灵鸡汤调配师,现在又多了一个职业——画家。
小馆不大,生意火爆,晚上要是晚来一会儿,排队是注定的。具体来说,这里的菜是湖南浏阳菜,出品貌似粗糙,一份份盛放在瓷碗里,实则锅气十足。北京有太多注重盘式的“瞎讲究菜”,这里的犹如在土地上野蛮生长的植物,带着烟火气。
真的几乎每一道都好吃,简简单单一款煎豆腐,已经灭掉大多数餐厅的豆腐菜,浑然味厚,里面软嫩,吃完这口豆腐,玛丽莲·梦露的豆腐我都不想吃。最妙的是金钱蛋炒拆骨肉,金钱蛋算是湖南乡间的做法,把鸡蛋蒸熟,裹上一点糊,炸至金黄。拆骨肉则是骨头上踢下来的肉,貌似散碎,其实最香。两者合一,几乎平趟宋庄。人说湘女多情,这道菜也如湘女,浓烈、香艳、下酒、下饭。据说宋庄许多餐馆现在都有金钱蛋,毫无疑问,这是溯源地,是宋庄的“庄蛋”。
在“庄蛋”的映衬下,巫昂也显露出吃货本色。她边吃边四处寻找,我问她在找什么。她说在找一个服务员。“是一个臭脸服务员,对客人冷嘲热讽,如秋风扫落叶般无情,每次来都得她拌嘴,几天不见还真想。”
我说,是不是嫁给艺术家了,有的艺术家也属于这种“受型人格”,喜欢这个套路。巫昂怅然说:“没有这个臭脸服务员,我都觉得这顿饭吃的有点寡味。”她说着挑起一片金钱蛋。这勾起了我对臭脸服务员的万千联想:她需要多么粗壮的灵魂,才能绝然面对3000名艺术家,面对5000名打工仔,300名美发学院的学生?我准备过两天再来一次宋庄,不为“庄蛋”,只为“装蒜”。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