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母亲去世前的一段漫长时光里,我的故事原本可能更加悲惨。我父亲本可能变成酒鬼,或是染上毒瘾,抑或沉迷于女人,抛下我们姐弟俩,任我们自生自灭——或者比这更糟——把我们丢进纽约市儿童服务中心,父亲说过,凡是被送去那里的孩子大都没有好结局。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所谓悲剧,不在于当下,而在于回忆。
如果那时就听了爵士乐,我们的人生是否会变得跟现在不一样?如果早就知道我们的故事是一曲回旋往复的蓝调,不断重复同一段副歌,我们是否会抬头,对彼此一遍又一遍地说“这就是记忆”,直到生活变得有意义?如果早就知道那疯狂的青春里嵌着一段旋律,现在的我们又会在哪里?当年呀,西尔维亚、安吉拉、琪琪还有我,四个女孩聚在一起,像极了爵士乐的即兴演奏—头几个音符试探着相互靠拢,渐渐地,乐队找到了相同的步调,音乐随即自然而然地流淌起来—可惜,我们当时还不知道爵士乐,也无从知道自己就像一首爵士乐歌曲。20 世纪70 年代排行榜那前四十首歌曲都在试图诉说我们的故事,却从未真正把我们说清。
十五岁那年夏天,父亲把我带到了一个女人面前。那女人是他在伊斯兰民族组织1 的兄弟介绍认识的。他说,这位女士受过教育,我有什么话都可以跟她说,因为那时候,我几乎总是缄默不语。在那之前,曾经口齿伶俐的我突然变得沉默,像是被夺走了呼吸,陷入了一种令家人不解的忧愁之中。
索尼娅女士瘦瘦的,她棕色的脸蛋严严实实地遮掩在黑色的头巾下。从那以后,这个戴着头巾、手指纤细、黑色眼眸里闪烁着疑问的女人就成了我的治疗师。但那时,也许已经太迟了。
“谁还没经历过一些沟沟坎坎呢?”索尼娅女士经常这样问我,似乎理解了人类的苦难是如何之深、如何无所不在就足以将我拉出自己的泥沼。
不知何故,我和弟弟的童年有一半都是在没有母亲的环境中度过的。弟弟有父亲传承给他的信仰,而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和西尔维亚、安吉拉、琪琪一起分担着在布鲁克林成长的女孩们的重负。它沉甸甸的,仿佛一袋重石,当我们无法承受时便互相传递,说着:“来,帮我背一下。”
转眼间,那段童年时光已逝去二十年了。今天早晨,我和弟弟安葬了父亲。我们肩并肩,站在墓地里,四周的柳条低垂着,积雪融化,仿佛在泣泪,在冰雪的映衬下显得光秃秃的。清真寺的兄弟姊妹围绕在我们身边。在清晨的银光下,弟弟伸出手来,握住了我戴着手套的手。
之后,我们来到新泽西州林登市路边的一个小餐馆里。弟弟脱下了黑色外套,里面是黑色高领毛衣和黑色羊毛西裤。他头戴妻子织的黑色小圆帽,帽边正好抵到眉梢。
餐馆里散发着咖啡、面包和漂白剂的味道。霓虹灯闪烁着明亮的绿光,打出“欢迎惠顾”的字样,下面垂挂着积满灰尘的银色彩条。圣诞节那天我是在医院度过的,看到父亲呻吟着要止痛药,而护士却迟迟不来。
一位服务员为弟弟的薄荷茶续了些热水。我挑挑拣拣地吃了几口鸡蛋和温热的家常炸薯条,故意慢慢地咀嚼着嘴里的肉逗他。
“你还挺得住吗,老姐?” 他问道,深沉的声音有点颤抖。
“我很好。”
“一切都好?”
“一切都好。”
“哦,我懂了,你还在吃‘魔鬼’的食物。”
“什么都吃,不带一点咕噜声。”
我们大笑起来,这是一个老笑话—从前,我常常跟闺密们在下午一起偷偷溜去街角的杂货铺,去买我在家里不准吃的食物。
“知道吗?你还是可以过来跟我和阿拉菲亚一起住的。睡几个晚上可不会传染。”
“我在公寓里住得挺好,”我说,“有很多事情要做,要整理爸爸所有的遗物……阿拉菲亚还好吗?”
“她会没事的。医生说得好像她一站起来宝宝就会马上从肚子里掉出来一样。一切都很好,宝宝也会平安无事的。”
七月三十日,我开始了进入这个世界的征程,然而直到八月我才真正降临人间。我的母亲饱受漫长分娩的折磨,当她问今天是几号时,父亲回答说:“八月了,现在八月了。”“嘘—亲爱的,”他低声说,“我们的奥古斯特出生了。”
“你害怕吗?”我问弟弟,握住了他放在桌上的手。脑海里刹那浮现出我们在甜蜜林小镇的一张合影:我把刚出生不久的弟弟抱在大腿上,自己也还是个小女孩,冲着镜头微笑,神气十足。
“有一点儿。但我知道,有真主安拉在,一切皆有可能。”
我们安静地待着。周围都是白人老夫妇,他们小口喝着咖啡,两眼放空。我听到身后有人用西班牙语说笑着。
“我才这么年轻就要当姑姑了。”
“你要是再不着急,就会老到当不成妈妈了。”弟弟咧着嘴笑,“我可没有批评你的意思。”
“没批评才怪。”
“我只是想说,你该停止研究死人,回来跟你活生生的老弟混了。我认识个男的……”
“别跟我提这个。”
我试图不让自己去想即将独自一人回到父亲公寓的事,那伴随死亡而来的如释重负以及深深的恐惧。要把衣服捐出去,把过期的食物扔掉,把照片收起来,可这都是为了什么?为了谁?
在印度,印度教徒把逝者火化,将骨灰撒在恒河的水面上;巴厘岛附近的加比德尼奥人把死人放进树干里;父亲则要求我们把他土葬。他的灵柩躺在土坑里,一堆颜色深深浅浅的黄土静候在一旁。我们没有站在一边,看着这堆黄土被铲到他身上。我总是忍不住去想,父亲会突然醒来,在柔软无形的缎衣中挣扎,就像其他成百上000个人一样—在深度昏迷中被埋葬,醒来恐惧地发现自己已身在地下。
“你打算在美国待一段时间吗?”
“就一小段时间,”我说,“但是我很快就会回来看宝宝的。我不会错过宝宝的出生。”
小时候,我并不知道“人类学”这个词,也不知道有个组织叫“常春藤联盟”。我更不知道有人可以生活在飞机上,穿梭在世界各地,研究死亡,目睹前世今生的未解之谜……*终获得了解答。我曾在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在毛里塔尼亚和蒙古见过丧葬习俗。我见过马达加斯加人从墓穴中挖出用棉布包裹着的先人尸骨,给它们喷上香水,请求这些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的先人告诉他们过去的故事,祈求他们的保佑和祝福。我曾在家待了一个月,目睹了父亲的死亡。死亡并没有吓倒我,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然而,布鲁克林于我却似骨鲠在喉。
“你应该快点来阿斯托里亚吃顿饭,吃顿干净的饭。阿拉菲亚可以坐下来一起吃,只是不能站在炉灶旁做饭。我会安排好的。一切都没问题。”
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想念爸爸,也想你了。”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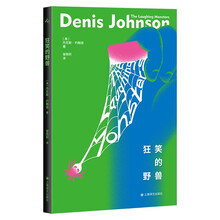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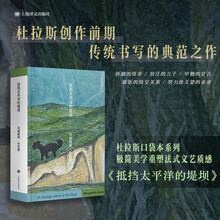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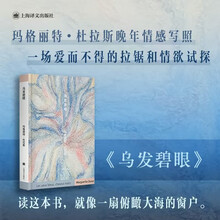





——Bookreporter.com
这部小说丰富的内涵远远*了它薄薄的页数。在她那诗意的散文中,伍德森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不断纠结于过去的奥古斯特是如何努力地延缓成长的脚步、躲避背叛青春的痛苦,还探究了我们是如何梦想着与现实不同的另一重人生。
——《书单》杂志|星级书评
优美、诗意……一段段往事与回忆,通过不同的地方、时间和爱交织在一起……伍德森描绘了一群黑人女孩眼中20世纪70年代的纽约,鲜有文学或其他艺术形式的作品会将这一群人放在聚光灯下。
——《观察者》
这部紧凑而感人的小说,有着极具魅力的核心主题,而这主题正是取材于真实的个人经历。
——《纽约时报》
这是一本韵律优美的散文小说。
——《华尔街日报》
伍德森试图铭记那些无法被载入档案的过往,试图暗示那些无法言说的故事。《另一个布鲁克林》优美如诗。
——《华盛顿邮报》
杰奎琳·伍德森的这部小说如乐声高昂、富有诗意的合唱……四个青春密友……在20世纪70年代的布鲁克林,面临着危机四伏的青春期、破败不堪的街区和萦绕心头的梦靥,她们一边艰难前行,一边梦想着逃离。
——《名利场》
这是一个多线交织的成长故事——缺失的母亲、负伤的老兵、摇头晃脑的瘾君子、险象丛生的街景——具有突出的现实主义色彩,又充满纯粹诗性的瞬间。
——《ELLE》
“在这部优雅动人的小说中,杰奎琳·伍德森刻画了一位令人难忘的叙述者,透过她的眼睛,探究了那些成长在20世纪70年代布鲁克林的女孩拥有的美丽、肩负的重担。奥古斯特与闺密之间,那些确信不疑的希望和低声说出的恐惧,让我在读完小说之后,开始思考友谊所带来的正反两面。《另一个布鲁克林》充满了悲伤、感恩与奇妙的瞬间,展现了杰奎琳·伍德森高超的叙事技巧。”
——安吉拉·弗卢努瓦, 美国国家图书奖入围作品《特纳之家》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