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巴黎人物:密杭德的风流事
跟她们亲嘴,就像用吸管喝薄荷甜酒一样。
两餐之间,密杭德的生活也一样精彩。他享受女人带来的欢愉。当下的欢愉与女人互不兼容,既对立又相斥,宛如汽水和威士忌。密杭德也带给女人欢愉,许多女人从他身上获得乐趣。但是那已不再被视为公平或诚实的交换,女人憎恨自己被当成取悦别人的个体,她们认为那是男性沙文主义的看法,她们希望被严肃对待,即使没人爱也无所谓。
如果我对当代作家的了解还算正确的话,性的功能对男女双方都很无聊。
自由地描写性关系变得稀松平常,不过态度要严肃。你可以高尚地描写你的初夜,假如那是场灾难。霍尔顿?考尔菲德 从来不上邮局,亨利?米勒可以把自己放浪形骸的生活写成交织人性的杰作,因为他的狂喜很庄严(他39岁时抵达巴黎,当他描写婚礼时,仿佛是一个很晚才发现香蕉船的男孩)。《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之所以为人接受,就因为它是一部“严肃”的艺术作品。没有最好的理由可以证明它是艺术作品,不过要用大家都能接受的话语来说明它是严肃的作品却很容易。欢乐的艺术作品仍然被排除在外,这绝对不是该死的玩笑。
那些教人如何做的二流书,意图严肃,笔触庄严,我们很快就开始DIY起来。
人们不再书写这项迷人的消遣娱乐,或者即使写了也无法出版,但它仍然是最有趣、饶富教育意义又最不具伤害性的人类活动。法国也发生类似的情况,而且经常惹恼密杭德。
“如果我是同性恋,不写男女私通的剧目而是写乱伦,我20年前就是法兰西学院的成员了。”他曾经这么告诉我。
法兰西学院在他死后做了补偿,遴选密杭德的好友兼弟子马塞尔?阿沙尔 为永久院士。阿沙尔也是喜剧作家,他继承了密杭德永远不会在国家图书馆展出的图书。
不过,密杭德很虔诚。他每个周日的早上会去教堂望弥撒,每个周日的下午会去赛马场。我想布莱恩先生 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露水情缘
密杭德的风流史里有一则动人的往事,他在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和他卖座大戏的首席女演员有段露水情缘。当时他有租附带豪华家具公寓的习惯,而且常常被锁在门外。靠着在巴黎林荫大道每季演出三四出戏码,他可以大赚一票,不过收入不太固定,而且他品味奢华,一赌千金。他总是把房东留到最后一个才付账,因为他很讨厌他们。
有一天快破晓前,密杭德从马克西姆餐厅回来,他发现那个心眼最坏的房东选在那一晚诉诸法律把他赶出门。当时密杭德身上穿着晚礼服却无处可脱,他从一家通宵营业的夜店打电话给那个女演员,问她可不可以去她的住处歇一晚?幸运的是,她只有一个人,她说很欢迎他去,于是他就跟她一起度过那晚剩下的时光以及翌日的上半天。她家没有客房。
中午过后不久,他们被女演员的女佣吵醒。她非常激动,抱歉打扰了他们,不过她说事态紧急:有个男人正在客厅里,他说如果女主人付不出积欠的房租,他将搬走全部家具。她同时拿出一份看起来蛮正式的账单,上面还贴了邮票。
这是她们的拿手戏,会在初次上门过夜的富豪公子哥儿面前表演。女演员接着会嚎啕大哭,责备自己愚昧、挥霍无度,央求她的追求者伸出援手,挽救她的名誉(这个剧情给了密杭德第一幕的点子)。
但是这一次,那个女演员却轻蔑地看着她的女佣。
“蠢婆娘!”她叫道,“你看不出这是我的作家吗?”
想敲诈作家这种想法显然很愚昧,那位女佣没搭腔。
“还有,那个信封太旧了,下次记得准备换上新道具。你走吧。”
密杭德爱死了这种场景。他很欣赏那位女演员,她靠演戏维持好气色,即使只有晚场没有日场。
他应该不能理解两性战争,他认为生命是两性温柔的合作。当密杭德还是刚从拉尼翁来到巴黎的17岁男孩时,那些20多岁就半守寡的妇女就跟他做爱并教导他。当他成为成熟的男人后,他懂得还这份人情:他跟比较年轻的女孩做爱。
密杭德很爱吹嘘自己的持久力。他60岁老当益壮时曾远征好莱坞,带着许多猎物凯旋。80岁,就在G女士结束餐厅之前,他开始筹划另一波大入侵。
“我们法国人用脑筋做爱。”他告诉我。
“我们其他人使用传统的工具。”我说。那是我唯一占上风的一次。
当我在《纽约客》发表第一篇和密杭德相关的文章后,读者的回响很热烈,我收到至少有12封信,全是这位伟大人物的英语系仰慕者,这些读者的追忆大大地提高了他的地位。
“毕竟,他曾经是色情片女优的情夫。”一位女性读者写信告诉我,“那可不简单。”
“我有次问他怎么跟那个女优做爱,”她继续写,“他说:‘她像怀孕的母猫一样淫荡。’”
阿沙尔告诉我密杭德就像许多多产作家一样懒散。他在兑现合约前大量接受各方订金,直到第一次排演前夕才开始动笔。经验带给他自信,当他需要时,就能想到好点子。
“有次他等了一整天,带着一叠纸来到排演现场,但他不准别人看,他说他的字迹太潦草,只有他自己才看得懂。接着他从标题开始写起,很顺利地写好了一出剧本,那出戏很成功,名为《朋友之妻》,你可以想见剧情,他是个天才。”
阿沙尔先生看出来我觉得他的形容有点夸大,于是解释他的意思。
“你知道什么是天才吗?”他问,“雅克?德瓦尔 曾说:‘天才是不会只写票房毒药的作家。’”
“密杭德有次告诉我,他跟上流社会的女人无法享受真正的鱼水之欢。”他说,转回到我们这位老朋友的另一项才华。“他说跟她们亲嘴,就像用吸管喝薄荷甜酒一样。”
遇见安洁拉
安洁拉闯进我的意识,终止了这些白日梦,她说我需要有人陪我回家。去年夏天在杜尔,有个女孩曾做了类似的提议,却把我交给两个半路杀出的盗匪。为人正直的安洁拉和我一起回到旅馆,第二天早晨,我们多聊了一些,竟然发现我们几乎是邻居。她住在大学旅馆,位于哈辛街与医学院街交叉口,就在与圣米歇尔大道的接壤处。而我的房间(那是我一生中最美丽的房间之一)在五楼,就在圣皮耶埃旅馆的正面,地址是医学院街四号,隔壁是一家附有舞厅的中国餐厅。晚上我读书时,舞池的音乐飘到窗边,我一边分神跟着旋律唱起来,一面试图阅读莫利斯?普胡的《外省资料手稿》。其中有一首歌曲不断重复着“哦,草莓和覆盆子,还有我们喝下的美酒”,这是密杭德红极一时的歌曲“三位裸少女”。
这种气氛不太适合研读中世纪历史,而我正是因为要学习中世纪历史而住在拉丁区。
安洁拉不只白天跟我住同一条街,夜里也和我光顾一样的咖啡馆:苏佛莱酒馆、泉源咖啡馆、阿库咖啡馆,都在圣米歇尔大道上。她的总部设在阿库咖啡馆,在那里她不太有机会注意到我,她说。“她有太多朋友了,”她解释道,随时都会有人吸引她的注意。
我说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苏佛莱酒馆,酒馆老板是我房东的好朋友。不过从此以后,只要我想看她,就会去阿库咖啡馆。如果我在那里请她喝一杯,对她的地位会带来正面的效果,不过如果我带她到苏佛莱酒馆,却不能提升我的身份。如果她不在座位上,服务生会传话,他也会提醒她冬天穿暖和一些、别弄湿双脚、多吃一点以保持体力,还有别被打手模样的顾客给骗了,以他老练的眼光看来,他们八成在替妓院找妓女。这种关系我在纽约已经很熟悉:服务生是许多女孩的保姆。
当我们知道彼此出入的场所如此雷同之后,安洁拉和我都觉得我们会在距离圣米歇尔大道50公尺的吉卜赛酒吧相遇很不可思议。听起来有点像两个纽约人,住在同一栋公寓却在地中海的马约卡岛初次邂逅。
从此以后,我们出双入对。我不知道她是否心地善良,不过她有一种我多年后才得知的治疗型人格,她让你感到很自在。
夜晚我带她出门,有时离开拉丁区,就好像带着曼哈顿的小孩到纽约最大的布隆克斯动物园一样。那些女孩并不常在巴黎市游走,她们有固定区域的顾客,生活习惯也因此固定下来。蒙帕拿斯区虽离拉丁区不远,却充满异国特质,语言也是。
光顾蒙帕拿斯区咖啡馆的客人都说英语、美语或德语,那里的女孩至少要会说两种语言。在拉丁区,除了说法语外,也说越南语、西班牙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不过来自这些国家的人都会说一点法语,所以女孩只说一种语言也通。顾客都是学生或假学生,那是“小协约国”时期 ,法国是东欧国家的文化与军事典范,而现在这些东欧国家都活在铁幕之后 。罗马尼亚的学生自由来到法国,也可以自由打工。
巴黎大学最杰出的地方,在于它延续中世纪时期的优良传统。从奥匈和土耳其帝国手中救出的各种部落都齐聚一堂: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埃及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另外还有海地人、韩国人、委内瑞拉人以及阿根廷人等,当然还有北非人。巴黎本来可以成为巩固各国友谊的伟大地方,对往后几年的动荡冲突有所帮助。但是我想,如果我好好地想一想,各个地方的动荡冲突都可追溯到安色尔体 或战马甲胄的古老时代。
对法国来说,我们都是外国人,因此说起法语时,比和法国人说法语时更有自信。我刚到拉丁区时,法语说得不比白俄人或捷克人差劲,后来随着法语逐渐进步,我循序渐进地被误认为匈牙利人、德国瑞士人、阿尔萨斯人、比利时法兰德斯人。至此,我不再进步,除了有一次在阿尔及利亚,我被误认为外籍兵团里的一名老囚犯,他的口音南腔北调,令人听不出来自何地。
安洁拉并不喜欢蒙帕拿斯区,我也不喜欢。在家乡,我到海边游泳时,总会游离海滩,一直游到暗礁之外。然后,我才开始偷懒,徜徉在海面上,轻轻划水,只要能继续浮在水面上就好,然后弯起膝盖顶着下巴,觉得怡然自得。我到法国也是一样。蒙帕拿斯区的美国人坐在乐赛列克特咖啡馆前谈天,让我想起伐木舟上的一群猴子,他们不下水。我想我不喜欢他们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每个人都希望成为作家、画家、雕刻家,而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住在圣皮耶埃旅馆时,还不曾听说过葛楚?史坦,但是我读了《尤利西斯》,我马上就知道访问此书的作者将像访问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一样困难。
安洁拉不喜欢蒙帕拿斯区,因为那里的人看起来既富裕又奇怪,她说,美国女人看起来不像法国女人,法国女人也不像其他地区的法国女人;这里也没有堆满博士论文和向已故学者致意的学术书店(她本身不爱看书,不过很喜欢活在学术环境里)。外表快乐的家伙大概吃了镇静剂,服务生傲慢无礼而且是意大利人,消费昂贵,到处都是美女妖精,而且用很奇怪的眼光看她。她要她们放心,她不会跟她们竞争。我们在丁香园结束旅程,它是边界的岗哨,位于蒙帕拿斯大道和我们的圣米歇尔大道交接处。岗哨被蒙帕拿斯区的人占领,因为它的消费价格太高,拉丁区的人负担不起。我请她喝了威士忌,不过她说喝起来有臭虫的味道,但如今每个法国人都喝威士忌。
安洁拉迫不及待回去阿库咖啡馆,不过一旦到了那里,她又很高兴说有了这趟旅行,说得好像刚刚才结束一趟国外旅行一样。不过当我们到蒙马特时,她才真的是得意非凡。以前她不断提起蒙马特的不眠之夜,却不曾身入其境。我们去杰莉斯酒吧喝了几瓶香槟,安洁拉的酒量很好,胃口也很大,床笫间,她是样样全包的内野手,她央求我买下别人替我们拍的六张照片和香槟酒瓶,就像捕鱼人与旗鱼的照片一样,好让她向友人描述我们的冒险故事。她的房间位于船形房子的船首,只容得下一张单人床,我只去过一次,那是在1927年9月时,当时她生了一场病。房间里一半的镜子上张贴着我们在杰莉斯的照片。
她说我“还过得去”,这句话包裹着我的自尊,仿佛是在防弹衣上镶了晶钻,除了这句话之外,我不想公开小安洁拉说的话。还有另外一件轶事可以说,因为她描述得如此生动,有时候让我有亲眼看见的错觉。
安洁拉告诉我,有天上午几位同事到她的住处打牌,有些女孩坐在床上,有些坐在桌子上,有个A女孩坐在唯一的一张椅子上,另一位B女孩则坐在她的大腿上,这个时候A女孩脱掉鞋子。
过了片刻,B女孩说话了:“我闻到臭脚丫的味道。”A女孩说:“你要是再说一遍,我就叫你去跟管理员问好。”
“你听懂了吗?”安洁拉说,“管理员住在一楼,我们在六楼,A女孩的意思是她会把她扔下楼。”
不久B女孩又说:“我闻到臭脚丫的味道。”
于是A女孩抓起B女孩把她拖到楼梯口,两人大打出手,一起滚下楼。到了五楼,有两位法律系的男学生暂停温习功课,拉开她们。接下来三天,两个女孩都无法工作。
那位拉开A女孩的男学生偏袒A女孩,而拉开B女孩的男学生则袒护B女孩。现在两位男学生也闹翻了,臭脚丫的A女孩和其中一位男学生搬到大学里,另一位男学生则和鼻子灵敏的B女孩一起同居,最后造就了两段罗曼史。
拉丁区的生活,是一部散发臭脚丫味的罗曼史。
我担心自己无法充分描绘安洁拉的迷人性格,妄想着靠片段的回忆描写一个女人,那就像想用几根骨头重建一只可爱的小动物一般。其中有几块骨头甚至一点用都没有。我的手臂试着记起她的体重,应该有118磅(约莫有两磅的误差)。
现在的我,不太敢回想当时她经常用头撞我腹部的情景,我们两人都认为这是一种亲密的表示。随着我的肌肉越来越松弛,我的看法也变了。
她依然存在。证据是我的前房东沛荷斯先生也对她记忆犹新。我偶尔会在巴黎一家叫阿尔萨斯的啤酒屋遇到他,店老板是沛荷斯先生的老朋友,他以前是苏佛莱酒馆的老板,苏佛莱酒馆在1931年时结束营业,因为老板娘不想管事(指望店老板管事是天方夜谭)。现在,赫伯先生(36年来我跟他寒暄时,一直都不知道他姓什么)有一位很杰出到不需要管事的老婆。啤酒屋生意兴旺。
在二次大战爆发后不久结束圣皮耶埃旅馆的沛荷斯先生,还是继续住在拉丁区,他说住在拉丁区能保持年轻。我先前提到1926年刚刚住在他的屋檐下时,他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展现过人的勇气,获颁骑士勋章,最近又荣获法国荣誉军团军官勋章。我一直怀疑他撒谎,事实上如果他是因为发现亚拉姆语 的不及物动词或胆囊的机能而获得这个勋章,当他邻居的我会更与有荣焉。他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步兵上尉,1951年再度受封。
“这有点教我难堪,”当我向他道贺获得蔷薇结勋章时,他说:“我升官升得很慢,70岁高龄的大学教授只有彩带加持其实只能算是高不成低不就。不过这个迟来的奖励和我经营的事业有关,法国荣誉军团办事处对于颁给旅馆老板更高阶的奖章格外小心,因为担心他经营的不是旅馆而是妓院。我一宣布退休不干,蔷薇结勋章就如囊中之物了。”
经营的30年之间,沛荷斯先生在圣皮耶埃旅馆接待过无数学生,让他自觉像一位大家长。“今天有个家伙在议会里提出信用的问题,”当你遇见他,他可能会提到某个议员在学生时代曾经住在圣皮耶埃旅馆。“我万万没想到他这么厉害”,或是“还有个人现在是王子门医院的内科医生主任,我上个礼拜拿到他的名片”,或者“有个现在是耶路撒冷大学中世纪的历史教授,他好像发表了一份受人瞩目的专题论文,探讨亚克拉丁王国 的世俗法律。你离去之后,他就在你的房间住了十年左右。他呀,起码他的时间都花在学业上。”沛荷斯先生认为我只爱嬉笑吃喝,无所事事。因为我们经常趁他老婆心情不好的时候,偷偷跑到苏佛莱酒馆喝一杯。
圣皮耶埃旅馆的前室友聚会是我唯一想参加的“毕业校友会”,不幸地,这个聚会并不存在。如果当真存在,当然还得附带邀请各个室友的女伴,那个和楼下韩国人同居的女孩、楼上唐的情妇、安洁拉,以及安洁拉之前和安洁拉之后的女孩。还有两位来自达克斯的年轻女佣露西安和安特弯,她们将要求洗澡的客人带到三楼浴室,她们会逗留一会儿,和客人亢奋地扭打一番。
沛荷斯先生对安洁拉印象深刻,仿佛她是秘鲁著名的比较动物学家。
她死于1927年至1928年的冬季,不是因为心碎而死,而是因为流行性感冒。那时我已经不在巴黎,而在普洛威顿斯的罗得岛,我回到美国在《普洛威顿斯报》和《夜间告示》工作。沛荷斯先生写了封信给我,提到她病逝的消息和其他室友的近况。
“她是那么的风趣,”30年后有一天他说,“有一天她告诉我:‘废墟王,你能够从这些分隔的小房间敲诈多少钱呢?’她完全没有伤人的意思,真是可惜,她死了,看起来那么强壮的人!”他说,像是最后的祝福。
“她还过得去。”我说。
我看得出来沛荷斯先生认为我有点无情,不过他不知道“还过得去”对我有多么珍贵。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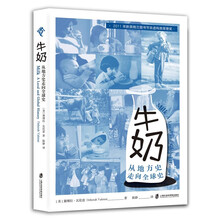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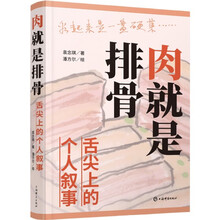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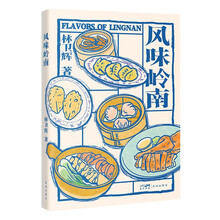



★尽管李伯龄自认是饕客而非美食家,然而一如与他同代的美国饮食文学天后M.F.K.费雪,这位纽约作家、记者亦是20世纪深富人文精神的美食家典范,可叹的是,他们历经的时代、体现的风范,如今俱已往矣。所幸还留下了著作。《在巴黎餐桌上》不光只是一本简单的巴黎美食书,李伯龄在书中以简洁轻松但精准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写人、写饮食、写巴黎,他写得是那么栩栩如绘、那么“好看”,叫人一捧起书来读便舍不得放下。记得当初读到本书的原文版时,才看完第一章就想:“要是这本书能翻译成中文,让更多人看到,那该有多好!”欣见本书中文版终于问市。
——韩良忆
★这本书虽然不是小说,却同样扣人心弦,有对话、人物、描述,以及一位杰出作家独树一格的笔触:篇篇信手拈来,风格清新隽永,足以媲美海明威《流动的盛宴》。
——美国艺术文学院院士詹姆斯?索特(JamesSalter)
★追忆巴黎的欢喜与流金岁月。
──《纽约客》作家大卫·雷尼克(1999年获《广告杂志》选为年度风云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