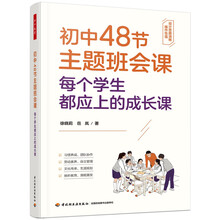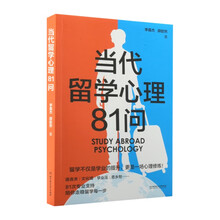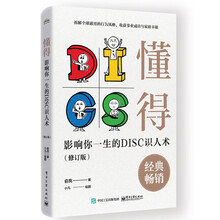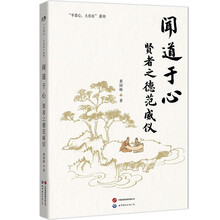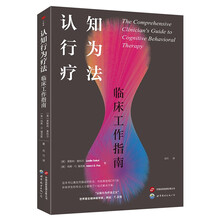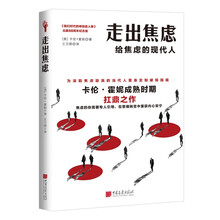第一章 翻译心理学概论
第一节 我国译者心理研究概况
一、译者的地位
翻译理论研究中两个最大研究途径是语言学途径和文学途径,这两种途径分别形成了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和文艺学派的翻译理论。语言学派主要是借助于语言学理论来研究翻译。我们知道,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和语言规律的科学,而翻译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活动。因此,翻译自然就成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正如卡特福德(1991:VI)所说“由于翻译与语言有关,因此分析和描述翻译过程时,必须充分使用语言描述中已确立的各种范畴。换言之,必须采用一种语言学理论,即普通语言学理论。”这样,把语言学理论运用到翻译研究之中也就理所当然。我国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可以说一直受到奈达早期翻译思想的影响。影响之大已经到了谈及翻译,“言必称奈达”的局面。无论是翻译理论者还是翻译教师,甚或学生也必以奈达的理论来衡量译文的好坏。语言学派的最大弊端在于会给人以误导,以为“学好语言学就可以翻译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张今(1987:16)认为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要害是“把艺术事实还原为语言事实,把美学问题还原为逻辑问题。”语言学派的目的,正如张南峰先生(1995:16)指出的那样,旨在“把翻译视为一门精确的科学,集中研究语言系统的差异、语言形式的转换,从而归纳出一些诸如语态转换、词性转换、增词减词之类的所谓翻译规则,企图以这些机械化的手段达到最大限度的对等——字与字、句与句的对等,却回避了文化差异、翻译动机、译文用途等重要问题。”如果此种假设真的能够成立,只要组织语言学家和计算机专家共同设计出翻译软件就可以了。然而,在软件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没有任何翻译软件能够代替人工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因此,语言学派所期冀的目标,最终结果就可想而知了,那就是“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张南峰 1995:16)。难怪奈达的翻译思想一旦发生转变,语言学派的翻译者便甚感困惑与不解,“至少会在心理上造成一次巨大的震撼。同时给我们正在积极兴建的翻译学科构成一次不小的冲击”(刘四龙 2001:9)。张今一针见血地指出,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致命弱点是只注重原语与译语在语言层次上的对等和等值,而忽略了译者及其翻译过程中的心理活动。
翻译文艺学派主要强调翻译中文学属性的转换,文学属性的转换主要体现在形式(译文的形式)和内容(原文的内容)的关系,原文风格与译文风格的关系,译者的风格与作者的风格的关系,翻译的再创造等方方面面。
关于译者在翻译中的地位,翻译文艺派自身内部不太统一。有持“背叛”论者、有持“一仆二主”论者、有持“隐形人”论者(方梦之 1998)以及有持“创造叛离”论者(谢天振 1999)。
“背叛”二字往往给译者带来极大的恐惧和不安,同时也使翻译研究者或想从事翻译的人产生一种矛盾的心理:既然是背叛,翻译又有何用;“一仆二主”又让译者无所适从:作者不满意,读者不买账;“隐形论”要求译者全身心地融于原著之中,译者又全没了个性;“创造性叛离”让译者自身也无从把握,何谓创造性?自以为是创造性,却招致了一个“乱译”的名声。总之,一个字——难。以上四派中,不论哪一派都十分强调文学属性的翻译。文学属性包括译文的形式、译文的真实性,原文风格的再现和译者的再创造等诸多因素。而文学属性的翻译又依赖于译者的个人能力和修养,其中包括译者的生活经历、知识、审美情趣、艺术修养和天赋。然而,翻译文艺学派的主张在指导翻译实践时的可操作性不是很强,往往都是翻译家自身的经验之谈。文艺学派有一个心知肚明而又不成文的默契,那就是“诗人译诗,小说家译小说。”罗新璋(1994)认为“译本的优劣,关键在于译者,在于译者的译才,在于译者的译才是否得到充分的施展。”一方面,它的确道出了文学翻译的艰难性和译者必须具备高素质的艺术修养甚或天才,正如德莱顿(Dryden 1992:20)所说“诗,非诗才兼精通双语者不能译”。但另一方面,这个不成文的默契又不知让多少想从事文学翻译的人望而却步。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从事语言学翻译研究的人比从事文艺翻译的人多这一现象。同时,文艺学派似乎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有一种“绝对排斥”(许钧 1997:5)的态度。这不仅仅不利于我国翻译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对其自身来说也是致命的,它将跟语言学派翻译研究一样,“同样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张南峰 1995:16)。
二、我国学者对译者心理研究情况概述
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语言学派翻译理论旨在“把翻译建立成一门精确的科学”(张南峰 1995:15),它要寻求的是一种可以定性、定量的转换规律,而译者的心理活动又是无法定性、定量的,译者的心理活动自然就被语言学派所忽略。文艺学派的翻译理论强调文学属性的迻译,而文学属性的迻译与译者自身的文学修养有很大关系,因此,文艺学派的翻译理论要研究译者的心理,但大都是局限于译者的经验性论述。杨武能用自己的翻译实践分析了译者在翻译状态中的心理活动。他说“文学翻译家的工作被正确地归结为一种艺术再创造。这个‘再’字不仅仅意味着语言形式的转换,信息的传达,一件作为完整有机体的艺术作品的重构和复制、再现等。这个‘再’字还意味限制。而限制与创造,恰恰形成一对矛盾:限制要求翻译家克制和否定自我,创造则相反,要求他发挥个性,张扬自我。处于这一矛盾中的翻译家,他工作时的心理特征表现为不断地在自我的否定与张扬之间进行转换,寻求平衡,克服文学翻译的上述固有矛盾所必然造成的尴尬——一仆二主的尴尬”(杨武能 1998:264)。他把翻译家放在作家、原著、译著和读者的中间,认为“真正的‘大师’必须兢兢业业,必须自觉地认识和把握规律,包括认识和把握自己在进行再创造时的心理活动规律,才能变尴尬为自由、自如,才能以平衡冷静的心态,悠游于双重限制留下的狭窄空间里,获得创造的乐趣(杨武能 1998)。”他把翻译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理解和表达。这两个阶段始终伴随着译者的判断和选择,所以文学翻译就是“一种判断和选择的艺术”(杨武能 1998:265)。判断和选择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既有市场需要,读者接受,也包括原著本身的文学属性。他认为“译家在理解阶段的心理特征为克服自我。 但是克服自我不等于消极被动;恰恰相反,它必须有译家自觉努力和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实现”(杨武能1998:267~268)。在表达阶段“译家又要相对克制自我”(杨武能 1998:268) 。同时他还分析了译者的社会心理,要求译家加强自我修养,要克服社会对译家的偏见,和傲慢与偏见作斗争。“自卑不可取,傲慢也一样。文学翻译家有必要经常进行克服自卑和傲慢,树立不卑不亢的内外形象的努力,以实现平衡,保持心理健康”(杨武能 1998:270)。
方梦之(1997)在谈到翻译学学科建设的方法论时,也从心理学的角度概述了翻译过程中的译者的心理状态。
张成柱(1998)认为文学翻译最根本的问题是情感移植的问题,情感移植的前提是“化为我有”。王彬彬(1998)从作家的立场谈了对翻译的看法,他认为翻译需要热情,需要激情,所谓激情就是翻译冲动。沈素琴(1998)谈到了翻译中的灵感。姜秋霞和权晓辉(2000)二者合作,运用格式塔审美心理模式对文学翻译的审美过程进行了动态的研究。
以上研究者仅仅研究了译者翻译活动中心理因素的某一个侧面。虽然未纳入学科范畴加以系统论述,但毕竟开始意识到译者在翻译活动的决定性作用。从学科建设角度,主张对译者心理活动进行研究的学者并不多见。
颜林海(2001)主张从学科建设上对译者的心理活动加以系统的科学研究,即建立翻译心理学。他(颜林海2007)认为翻译心理学是研究译者的认知心理活动、审美心理活动和文化心理活动特征和规律的科学,并对翻译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作出了论证。
第二节 西方译者心理研究概况
翻译过程中,译者大脑活动到底是怎样进行的?译者想的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也无法直接观察。虽然翻译涉及其他许多因素如文化、 意识形态等,但就翻译操作过程而言,翻译在某种程度上属个人行为,译者的所思所想对原文的理解和译文的处理极为关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过程的客观实证描述已成了翻译研究的重点(Bernardini 2001)。洛舍(L?rscher 1991b, 2005)也认为只有用过程分析法对翻译行为进行研究才有可能对译者大脑活动做出种种假设。因此,要对译者的心理活动进行描述性研究,就必须借助于认知心理学的理论成果和方法。
一、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的理论基础
认知心理学是以信息加工为核心的心理学,其主要研究范围包括注意、感知觉、学习和记忆等认知过程和结构。认知心理学家把大脑比拟为计算机的信息加工系统,认为大脑就是一个“中央处理器(CPU)”。布儒宁(Bruning 1995:1)认为,“认知心理学是以人类感知觉、思维和记忆为研究核心的理论观点。它把学习者比拟成主动的信息处理器”。洛舍(L?rscher 1991b, 2005)把人类的认知看做信息加工。因此,认知心理学的主要理论架构是信息加工模式。这个模式视人类为主动的信息加工者,探讨人类凭感官在接受信息、贮存信息以及提取、运用信息等不同阶段时所发生的事,所以认知心理学也常被称做“信息加工心理学”。
什么是翻译?凡是翻译研究者似乎就必然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然而,迄今为止,很难找到一个真正权威的定义,因为不同的学者对翻译有不同的理解,正如索尔(S?lle)所说:“翻译理论的历史可以说是探讨‘翻译’多义性的历史”(见Wilss 2001)。的确,无论是英语的“translation”,还是汉语的“翻译”二者都是多义词,都有贝尔(Bell 2001:13)认为的三种含义:①指翻译过程;②指是翻译结果;③ 既指翻译结果又指翻译过程的抽象概念。
翻译的不同含义导致了翻译研究的不同侧重点。贝尔认为“翻译过程论”要求对信息处理进行研究,研究论题包括知觉、记忆、信息编码和解码,其研究途径为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翻译译品论”强调对译本进行研究,其研究途径为语言学,包括句法学、语义学、文体学、语篇学和话语分析;“翻译综合论”要求既要对翻译结果进行研究,又要对翻译过程进行研究。
贝尔很赞同对“翻译过程”进行描述性研究。杜布瓦(Dubois)曾经把翻译定义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原语)语篇所表达的东西用第二种语言(译语)重新表达出来,尽量保持语义与文体方面的等值”(Bell 2001:5)。贝尔对此提出了批评,具体地说,对杜布瓦的“保持语义与文体方面的等值”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完全等值的理想是愚蠢无聊的幻想,因为语言之间彼此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形式上就是它们各自有不同的符号及其语言符号组合规则,同时这些形式具有不同的意义(Bell 2001:6)。”
贝尔对翻译过程的研究是建立在信息论原理基础上的,因此,他比较赞同翻译就是交际,交际也是翻译的观点。他引用斯坦纳(Steiner)的话来印证此观点的正确性。斯坦纳(Steiner 2001:47)认为“任何模式的交际同时都是一种翻译:即意义或纵或横地在某一个层面上的转移。没有哪两个历史时代,哪两个社会阶层,哪两个地方使用词汇和句法来精确地表示相同的东西。 也没有哪两个人可以做到这一点。”
这里的“或纵或横”是指意义具有多重性,但任何交际或翻译都只能传达其中的部分意义,有些意义在交际或翻译过程中损失掉了。到底是取“纵”舍“横”还是取“横”舍“纵”,这完全取决于译者本人。因此,对译者翻译过程中的大脑活动或心理活动的研究是关键。取舍的因素可以大致分为内外因素。外在因素包括:译者的知识(包括意识形态,诗学观等)、经验和生活环境。内在因素是指译者的大脑活动(如记忆)或心理活动。
虽然贝尔用信息论原理对译者的内在因素即心理活动做过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但也仅仅停留在假设层面,未能进行实验研究或论证。
而认知途径的翻译研究者认为,翻译研究的注意力应该放在翻译过程的客观描述上,对译者的大脑活动进行认知研究(L?rscher 1991b,2005)。在他们看来,翻译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信息加工的过程。而认知心理学主要探讨人的信息加工过程和加工模式,因此,译者翻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