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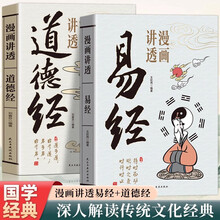








本书是关于道家学说的观念史的研究作品,分上下两编。上编集中于对道家形而上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的探索,包括“道”、“德”、“有无之辨”、“自然”、“无为”、“天”“、命”、“人”、“化”等重要术语以及生死观。下编则主要探讨道家一些的基本思想,涉及的问题有关于道家政治思维的起源和奥义的,有关于道家诠释传统中的创造性转化和颠覆性改装的,也有关于道家心灵和精神世界新展开的。本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国学论丛:道家学说的观念史研究》:
中国传统道家本体不可言说之思想,在中国现代哲学中,继续成为形而上学话语中的一个部分。由于中国现代哲学家的哲学来源,已不局限于传统,而增加了西方哲学的新渠道,因而其观念表现出中西结合的特点。在金岳霖的形而上学中,一方面,他接受了道家庄子万物齐一、无形无相的思想,认为从元学的对象看,“万物齐一,孰短孰长,超形脱相,无人无我,生有自来,死而不已”。另一方面,他接受了维特根斯特所说的本体不可言说思想,认为说不得的东西当然说不得。他说:“治哲学总会到一说不得的阶段。说不得的东西就是普通所谓名言所不能达的东西。有些哲学家说,说不得的东西根本不成其为东西。如果我们一定要谈到这样的东西,我们不过是说些废话而已。这种主张也对。说不得的东西当然说不得。若勉强而说之,所说的话也与普通的话两样。”②冯友兰更具有浓厚的形上学兴趣,并自认他自己的形而上学最纯粹。他提出四个形而上学观念:气、道体、大全和理。他认为其中的气、道体和大全,不可思议,不可言说。气不可言说,是因为气没有任何性质,不是什么,不能名之。道体和大全,不可言说,是因为道体是一切的流行,大全包括了一切。而言说就是一流行,就是一事态。但我们言说道体和大全这一流行和事态,都不在道体和大全之中,因而所说的道体和大全,就不是道体和大全本身。与此不同,理可以思议,可以言说。这样一来,在形而上学本体与语言的关系上,冯友兰就具有了复杂的情形。对于他,我们不能笼统地说语言能够言说形上本体,或者不能够言说形上本体,只能具体而论。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肯定,在形上本体与语言的关系上,道家的观念是语言无法言说本体,无力承载本体。但是,道家本身拥有形而上学,还把它留给了我们,这本身所表明的非但不是不能言说,实际上恰恰是言说。如何解释判断与事实之间的这种悖论呢?一种说法认为,“不可言说”本身就是一种“言说”,即“不可言说”之“言说”。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的问题和理解,也许就可以取消。诚然,在有的哲学家(如王弼和冯友兰)那里,所谓“不可言说”,就有“不可名”即是“名”,“不可说”即是“说”的说法。但是,我们却无法直接否认,他们所谓的“不可名”、“不可言说”,仍主要是指本体不可言说,不是指对本体的一种言说。正如我们说“不知某物”,并不意味着对某物有所知一样,说“某事不可形容”,就是对某事进行了“具体”形容一样。不承认这一点,就难以理解道家形而上学对语言应用范围所作的划界,也难以理解又设法去言说形上本体。既然“不可说”即是“说”,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再想别的办法去说呢?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道家拥有的是一种“道言观”,道家说本体不可言说,是就某一种“语言”而说的。道家主张的是真正的言说——“道言”和“大言”,即自道自言,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本身在言说”一样。这种说法认为以往对道家“言说观”的理解都不恰当:“自王弼以来流行的‘道本无言’的说法就是这类困境的一种表现,而且是相当平板化的表现,并必然陷入言道死结。在这些解释者看来,言或名只能是概念或表象的,所以只能与形而下者或‘有’打交道;对于形而上的道体或‘无’,就只能‘无言’。然而,不仅《老》、《庄》和一切后人的解释,就这‘无言’二字也都是言。于是,他们只好这样解释:道本不可言,但又不得不去言之;所以只能暂且地、勉强地去言它,以便通过这言去达到无言自悟的道境。……但这种说法中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弊病和死结,即:如果道毕竟不可言,那么你如何能通过言说它而得其意呢?”在我们看来,“不可言”而“勉强去言”,并非解释者强加给道家的东西,道家老子有最清楚的话。实际上“不可言”,最终还能言说并且言说,实际上恰恰是道家在本体与语言关系上自身就有的一个矛盾。我们不能无视大量的文献,而想方设法消解道家的这一矛盾,甚至走得更远,说道家主张什么不言之言的“道言”,而且与海德格尔的说法类似。
……
★我期待,借由此套丛书的付樟,以探索民族文化艰苦历程中的延续性,找寻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生命力,整合并推动中国文化中坚力量的持续发展,使传统学术在多元世界中展开新的气象。
——陈鼓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