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是否应当对人民讲真话》:
触觉的伦理
对某人做出判断,通常依靠眼睛甚于双手。因为每一个人皆可看到你,却很少有人能够接触你,每一个都看到你的外表,但很少人摸透你的真相……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哲学之谜来自他者的凝视。主体之诞生便是与他者目光之邂逅,在目光的相互遭遇中领会他人对我的意义,献身于对象,委身于对象,才看到自己。他人目光在场,不仅无声细说我的到来,实现对我的见证,引发自我意识,我亦被他人的目光所规定。经由他人的显现,“我才能像对一个对象做判断那样对我本身作判断”。[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版,第292页。]我可以不理会他人的在场,但不可能不与之共处。我不打算介入他人,故不愿惊动对方,可是,对方只需一个暧昧眼神,我就被搅扰了,强迫介入对方设定的视觉场,因为目光寻求反应,无论是消极回应、积极回应,甚至不回应,皆为一种回应。
万物统摄于我的凝视,我亦遭受四周目光的压迫,被咄咄逼人的凝视所包裹,挟持为目光的人质,他人的注视将我“置于他的视觉场,夺去了我的一部分存在”[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50页。],尤其不怀好意的目光审问,时时逼我作答,引发莫明恐惧。这是一种难以承载的目光重负——攫取、捕获、占有、吞噬了我。总之,目光的闪射,导使“每个人都被他人的目光客观化”。
2004年德里达辞世,吕克·南希撰写《德里达,向你致敬,向要成为的盲者致敬》:
你把我们置于黑暗之前,在这个黑暗中你消失了。但是:向黑暗致敬!向这个形象和图形的抹消致敬。也向我们要成为的盲者致敬,这是你偏爱的主题:向不取决于形式和理念、而任凭各种力量所触摸的视像致敬!……你努力要成为盲者,为了更能拯救只有黑暗才拥有的光明:它是在视线之外并且遮盖秘密的光明。不是隐藏的秘密,而是明见性,存在秘密的显现、生/死秘密的显现。向你守护的秘密致敬!
转向触觉主义立场的晚年德里达,为何滞留于黑暗?又为何“努力要成为盲者”?他究竟守护了怎样的秘密?
光之暴力
“光”是观看实践的基本前提,亦是抹除黑暗的先决条件,没有光的朗照,万物遁迹潜行,浸入无尽的阴森之境,仿佛置于死寂的坟茔。倘若不再有光的介入,在黑暗中沉睡的事物缺失苏醒的可能。唯有光的逼近,方可将事物从黑暗中拽出,使之复活,重现生机。
探寻光明是人类古老冲动之一,因为光之投射,万物均被摊开,可予以精准表象或正确造型,还世界以有序面目,从中获致一定程度的可控感,由可控感生出安全感。光之不及,便属不可猜度、无法把握的黑暗国度,黑暗中的事物难以命名,从而含糊、混乱、暧昧、模棱两端、莫可名状。那么,光之闪现,不仅视域一览无余,且万象尽收眼底,世界因被纳入光明的轨道而清晰通透,启人疑窦,轻松逃离光明布控的不确定之物或未知之物被迫现身,露出真实模样。
光的作用是临近、照耀,驱逐黑暗,使事物裸出、亮相,便于捕获、逮捉。无论字面意思还是隐喻层次,革命与光明有关,与视觉有关(影片《艳阳天》《金光大道》,典型的光之表达;再如艾青书写《光的赞歌》予以称颂;又如丁玲的名著《太阳照在桑亁河上》,首版书名《桑亁河上》,并无“太阳”与“照在”两词),光的从容到来,解放拘禁于黑暗之中受苦受难的被压迫者,将其带入光明国度,神秘而诡异的非理性世界亦为之一扫。
若阙失真光,世界便被黑暗权势辖制。黑暗中的事物无法辨认或识别,种种邪恶力量趁机横冲直闯,快速入侵,将有毒因子播进世人肉身,然后吞食其魂灵,最终掐断人性向善的可能,阻其走进早已预制好了的同志社会。面对魔鬼盘踞的黑暗世界,革命不容商量、不由分说地倾泻大量光明——“照到哪里哪里亮”(《东方红》)。为营造通体透亮的光明之城,甚至不惜制定“太阳节”……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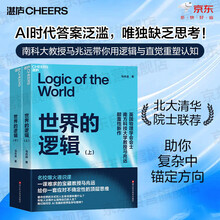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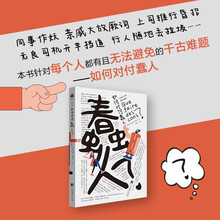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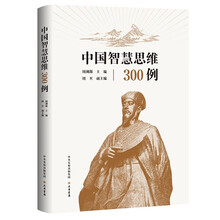

★谢宏声在书写与绘画、感性与知性之间,高度敏感、富有才华。并能轻易发挥而予以平衡。他对当代艺术的严肃理解远远超过他的同代人,而在把握影像、捉笔创作时,他只听从自己的内心:纯净、欲念、叛逆、阴郁,这是当代艺术的真髓。谢宏声的领悟既来自理知,又发自内心。
──陈丹青(艺术家、作家、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