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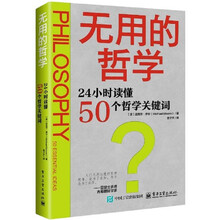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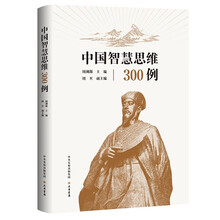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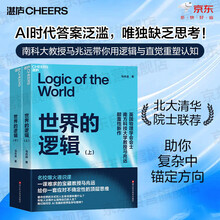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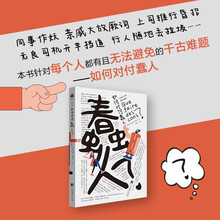

过去五十年里,科技哲学界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当属托马斯 库恩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重在建构一个“范式”,难免宽泛且有欠周全的地方,《结构之后的路》则对《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被质疑较多的地方进行了针对性的阐述。
在本书中可以看出库恩思想晚期的发展,他的核心概念从“范式”的转换,变成了不同语言之间的解释学问题,因此他显得更像一位分析哲学家。
伽伏罗格鲁:让我们从你的学生时代开始谈起吧,特别是你感兴趣的课程,你讨厌的课程,你遇到的老师,等等。
库恩:我在纽约曼哈顿开始我的学生生涯——或者说开始上学,这是另一个问题了。我在那里的改良派学校progressiveschool里上了几年学,从幼儿园一直上到五年级。一方面,改良派学校鼓励独立思考能力;另一方面,它又不大教什么科目。我记得那时我可能已经上二年级了,我父母觉得非常沮丧,因为我好像不会阅读;父亲就教我识字,很快我就学会了。后来,当我读到六年级的时候,我们全家搬到了离纽约大约四五十英里外的一个乡村,哈得逊河边的克罗登镇。
在那里,我进了一个叫黑森山学校(the Hessian Hills School的小改良派学校上学。这个学校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它出色地教会了我独立思考。这是一个很左的学校,主要创办者是一位女士,名叫伊丽莎白·牧斯。她是威廉·雷明顿的岳母。你们可能知道这个人,他就是那个由于当了共产主义情报员而最终被关进监狱的人,这是麦卡锡时代的事了。所以,学校里到处都是各种各样激动的左派教师,不过我们都被鼓励做一个和平主义者。那里没有马克思主义教育或其他这类教育;我们只是听父母说这是所激进的学校,但我们自己并没有看到它有什么激进之处。在那里,有一个老师对我产生了影响。我有过好几位对我产生影响的老师,但数学老师只有这么一位,他叫利昂西亚奇。人人都深深地敬爱他,他的数学教得特别好。我主要向他学初等代数,不过我总是……也不算很差,但在算术上只是普普通通,我总是算错,我做加法,可连续两天就是得不出相同答案我会背乘法表,可是我从来都没有真的会算超过9乘以9的乘法。但是,当突然转向更为抽象的计算,使用变量以后,我的数学在他的手上活起来了。我喜欢数学,十分擅长数学,这真是一个相当特殊的经历。
我想我的其他功课也学得相当好。……学校不进行评分,所以当我被证明学得特别好时,我相当惊奇——我毫不知情。我在那里上了六年级、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一共四年。我有一个很好的社会研究老师。在他那里,这个学校的激进性就表现得多一点了——我们一起阅读比尔德的《美国宪法的经济学解释》的主要章节,并且进行讨论。我们班上有六到七个同学;这是一种手把手的教育;手把手教育为的是放手教育。我认为它对我的思想之独立起了主要作用。
巴尔塔斯:能不能再跟我们详细讲讲关于改良派学校的概念: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学校吗?
库恩::不是。改良派教育是一种运动,就我所知,它实际上发源于约翰?杜威的一些提议。它不太强调科目,更强调思想独立,强调能够使用自己思想的信心。所以说,它不教拼写很正常——几乎没什么反复的练习。我们后来开始上法语课;上了三年我仍然记不住一个法语单词——就有这样的事。但是我渐渐变得聪明起来。我不能确定黑森山学校是一所小规模教育的、学科设置很少的学校,还是一所独立进行大量研究的学校,或者是一所人们想到什么就独立做什么的学校,但我确实认为它对我有着重要影响。有一件事我想说一下,我刚到MIT时,发现很多学生一直到快要毕业了还从来没有写过一篇10到12页的论文,那种我准备布置下去的论文。我在读六年级或七年级时,至少写过一篇25页的论文。还有更多那样的事。我想,那种研究的滋味,那种鼓舞的滋味对我后来发生的事情尤为重要。那个学校只到九年级。实际上,它常常只能读到八年级;但对我们那个年级的人,它一直让我们读到九年级,之后我上了寄宿学校。我父母担心我难以适应变化,便把我送进了一所小学校。
伽伏罗格鲁:学校里有许多左派,或者说整个风气都是左的,这种情况在那个时期是被人瞧不起呢,还是说在一些特定人群中被看成是好的?
库恩:我相信在有些圈子里它是被瞧不起的;我比我父母激进,但他们并没有瞧不起它。另一方面,它值得我再多说一点。这是一个时代和一个时代的人,那时人们开始加入一个叫美国学生联合会(the American Student Union的组织。成为美国学生联合会成员的前提条件是愿意签署牛津誓言。这个誓言的内容是你不能打斗,即使是为了你的国家。我记得我就此与我父亲进行过讨论,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不喜欢说我不会为我的国家而战。
我既想成为学生联合会成员,又不确信能恪守誓言。我记得我父亲对我说:“我签署过许多誓言,后来又违反了。但我想,我从没有在签署誓言的时候就想我将会违反它。”我很认真地考虑了他的话,没有加入那个学生联合会。另一方面,我的学校曾经召开过一次来自许多改良派学校的学生会议,我不记得我们讨论了些什么,正式主题是什么,但令我激动的是这次会议被纽约一家报纸报道。我不知道它的标题是什么,但当时站起来发言的人就是我,我说:“谁从我们的国家财产中获利?不是你,也不是我,而是那些资本家。放菲律宾人走吧!”这些事情别有一番滋味。
编者导言
第一部分
重审科学革命
第一章 什么是科学革命
第二章 可通约性、可比较性、可交流性
第三章 科学史中的可能世界
第四章 《结构》之后的路
第五章 历史的科学哲学之困扰
第二部分
评论与答复
第六章 回应我的批评者
第七章 作为结构变化的理论变化:对斯尼德形式主义的评论
第八章科学中的隐喻
第九章合理性与理论选择
第十章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
第十一章后记
第三部分
与托马斯·库恩的讨论
托马斯·库恩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