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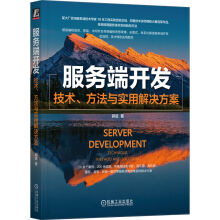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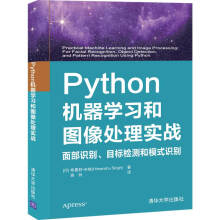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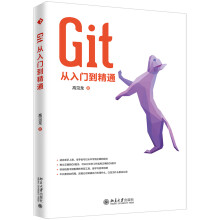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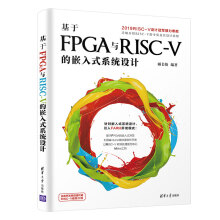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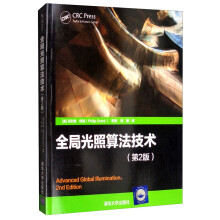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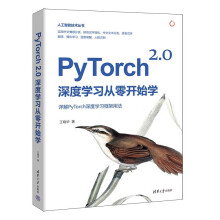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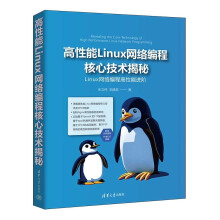
对于曾经生活于揭开了现代哲学之序幕的天才的世纪中的所有思想家来说,没有哪一个人的心智生活像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那样丰富多彩。接受法学教育,先后被聘为法律顾问、图书管理员等,他却在逻辑学、数学、物理学以及形而上学领域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即便如此,莱布尼茨却将自己的终极志向看做是伦理的和神学的;他还将这些理论上的关切同政治、外交以及范围同样广泛的实践方面的改革结合在了一起,这些改革的领域包括:司法、经济、行政、技术、医学以及基督教。玛丽亚?罗莎?安托内萨这部具有开创性的传记作品不仅从广度和深度上全面考察了这些理论兴趣和实践活动,而且也首次将它们整合为一幅由这位独特的思想家及其所经世事交织而成的统一的画像。在莱布尼茨看似杂乱而又涉及广泛的思想生活的中心,安托内萨揭示出将他的异乎多样的工作统一起来的主轴。穷其变动的一生,莱布尼茨都在执著地追求对全部科学的系统的改革和推进之梦,并且,这个梦想是要在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统治者的支持下作为一项合作性的事业来实行的。理论的诉求转而落脚于一个实践的目的:人类境况的改善以及对上帝创世荣耀的赞美。
导言
1717年11月13日,巴黎皇家科学院秘书长冯特奈尔(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向他的巴黎同僚们呈递了一篇悼念莱布尼茨的文章,此时距离莱布尼茨去世已一年零一天。冯特奈尔与这位德国哲学家在很多场合都有过信件往来,他的这篇悼文也借鉴了由莱布尼茨的秘书艾克哈(Johann Georg Eckhart)所提供的传记纲要。根据这些私人的了解,这位法国学者在一开始就很自然地想到了他的这位悼文主人最值得称赞的方面,那就是莱布尼茨智力成果的极其广泛的范围。“就像古人能够同时驾驭八匹马,”他以在巴黎学圈中风行依旧的古典式口吻评论道,“莱布尼茨能够同时驾驭所有学科”。可如此广泛的智力范围让冯特奈尔在意图陈述一篇能让人理解的传记梗概的时候遇到了几乎不可逾越的困难。冯特奈尔慨叹道:“莱布尼茨在同样的数年之间撰写了不同的课题……这场几乎从没有停止过的混乱,没有在莱布尼茨的思想中造成丝毫困惑,这些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的突然而频繁的转换,也没有给他带来任何麻烦,但它们却最终会困扰并迷惑这段历史本身。”[1]为了防止让八条强大而又相互纠缠的思想发展的脉络变得毫指望地相互混淆,冯特奈尔放弃了通常的编年史的次序,而改用分列主题的方法来撰写这篇悼文。
在莱布尼茨去世后的三个世纪里,冯特奈尔最先遇到的问题已变得越来越复杂。连莱布尼茨本人也曾向另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坦承,那些仅从已出版的著作来认识他的人其实一点也不了解他。[2]堆积成山的私人文稿——甚至在他死后的那天夜晚,在遗体从他位于施密德斯特拉斯(Schmiedestrae)的家中搬出之前,这些文稿仍旧不为人知——最终表明供冯特奈尔使用的已出版的著作仅仅是莱布尼茨智力成果中极小的一部分。所留下的档案资料规模巨大:成千上万封信件,数百部论文草稿、残篇、纲要、笔记。它们曾被柏林科学院收集并连续出版,并最终扩充为由八个序列(其中三个为书信,另外五个为其他著作)[3]组成的大约120卷的四开本文库。同样引人瞩目的是,与数量相比它们的质量毫不逊色。莱布尼茨没有将自己的观点胡乱发布,而是将很多极深刻的想法和不寻常的结论留给了自己以及少数几个最信赖的朋友。他的文稿被完好地保存于汉诺威皇家图书馆(最近改名为莱布尼茨图书馆);就像一股由未发表著作中的新作品以及残缺版本所组成的几乎难以控制的洪流,这些文稿给从莱布尼茨到现在的每一代人都带来了持续不断的智力资源的供应。[4]或许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这些文稿所涉及的主题,从狭义的哲学和数学,扩展到科学的大百科,甚至更多: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植物学、心理学、医学,以及博物学;法学、伦理学、政治哲学;史学、考古学、德语、欧洲各国语言、汉语;语言学、词源学、语文学、诗歌;神学(包括自然神学和启示神学);并全然超越了纯理论,扩展到广泛的实际事物:从法制改革到教会重组,从外交和实用政务到机构改革、技术改进、科学协会的创办、图书馆的建设以及图书贸易。
冯特奈尔感到绝望,他不能将莱布尼茨的智识生涯中的诸多路径整合为一个单纯的、按照年代顺序来记述的故事,因此他决定“分解他,或者,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分析他”。正如一句古典式的类比再一次表明的:“古人用好几个赫尔克里士(Hercules)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大力士。本书页下注皆为译者注。来制造一个人,而我们从莱布尼茨可以制造出好几个学者。”实际上,在莱布尼茨死后的一年之内,其理论系统就被拆分为几个独立的领域,他对这些领域的贡献也被逐一表述。在处理这样一批数量庞大的文稿和出版物时所遇到的文字上的困难,再加上要理解这样复杂而广博的思想所面临的技术挑战,对莱布尼茨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就成了专家的领地。他的全部作品被临床式地肢解,被分配给专家做进一步的研究;莱布尼茨经过长期并艰难的工作所创造的那个连续一贯的思维世界,在一大批跨及科学大百科的各个学科的学者中间被粗鲁地分解、割裂。
似乎这种“思维的肢解”的破坏力尚显不足,变本加厉的是,并非所有学科都以同等的敬重来历史地对待他们从莱布尼茨遗产中所分得的份额。莱布尼茨对数学的不朽贡献从来不缺少仰慕者。他在逻辑学上的卓越创新和在形而上学中的显著成果甚至吸引了更多的注意。然而在别的很多学科中,莱布尼茨的影响力事实上并未达到这种程度。他作为一个数学家和唯理论者(rationalist)而得以迅速巩固的名声可能转移了人们对他在其他领域中的贡献的注意力,并且这也妨碍了那些不熟悉逻辑学、形而上学和数学等所谓核心领域的专家们来研究他的生活和工作中很多至关重要的内容。不管以下所言究竟有多么精确,它所导致的不平衡却清楚地反映在自莱布尼茨去世以来已逐渐堆积在莱布尼茨已出版和未出版的作品周围的规模庞大的二手文献中。在1980年以前的关于莱布尼茨的标准参考书目中,形而上学与本体论方面的有806条,数学有552条,逻辑学有430条,认识论有282条,物理科学有220条;与此相比,在同一个参考书目中有关伦理学与实践哲学(practical philosophy)的仅有154条;而政治哲学与法学——这是莱布尼茨曾得到正规训练的学科,参考条目仅有135条;可以说在其一生的研究中占据中心位置的神学与宗教哲学仅仅列有122条;莱布尼茨的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仅仅列出98条;史料编纂——这是莱布尼茨后半生的主要职业——以及历史哲学占了微不足道的79条;医学,只有可怜的54条。[5]不管这些数据是否准确地度量了莱布尼茨对这些领域的持久贡献——或者它们的确是在最近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之中被再次调整过的关注重点的指数[6]——它们显然不能代表在莱布尼茨自己的心目中这些领域的重要性,并且也不能代表莱布尼茨为了研究它们所投入的精力。
除此之外,对莱布尼茨理论系统的割裂以及对它的组成部分的关注度的失衡已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误解;其作品的主要特色也使得这种趋势加剧。众所周知,莱布尼茨常常试图用极端微妙的、复杂的方法去调和一些显而易见的对立。同样显著的是,他还与各类同时代的人通信并向不同的人展示他的思想的不同方面。面对在各种著作和信件中明显不同的侧重点,一些学者草率地总结道:莱布尼茨不真诚,是一个随波逐流者,一个朝廷佞臣,他通过扭曲自己的原则来安抚反对派,或者压根就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的确,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目光更加短浅,他们甚至在莱布尼茨在世的时候就得出相似的结论:有人担心他会皈依加尔文教,有人认为他已经转信天主教,还有人认为他私下里是一个神论者。在莱布尼茨死后,这些简单化的刻画(reductionist characterizations)数量激增,从自然神论者和坚定的唯理论者,到卡巴拉主义者(Kabbalist)、炼金术士,或玫瑰十字会成员(Rosicrucian),所论不一而足:这种质疑莱布尼茨的理智和人格的统一性,并把莱布尼茨分割——以冯特奈尔曾隐秘地建议过的方式——为两个完全不同的哲学家的倾向,在也许是迄今为止最知名的哲学家所做的专门针对莱布尼茨的诠释中达到了顶峰。不止伯特兰?罗素一个人认为莱布尼茨的哲学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是坏的、公共的哲学,或者说是用来取悦和供资助他的达官贵人们消遣的“动听的神仙故事”;另一个是好的、私人的哲学,它是以罗素本人非常欣赏的逻辑学和数学中的智力结晶为核心的。[7]
近几十年来,像这样简单化的诠释总体上正在逐渐减少,并且也不大可能每一个严肃的学者都完全赞成罗素对莱布尼茨的哲学著作所做的二元论的说明。莱布尼茨的研究者们不再进行那些对人不对事的刁难,而是渐渐变得善于耐心地梳理各种表面上不同的陈述下所隐藏着的一致性,或者将一些真正的不一致解释为哲学探索与发展之缓慢过程的一部分。像莱布尼茨这样的人,善于观察表面的对立下所隐藏着的和谐,同样也能够通过似乎彼此并不相容的方式来展示其独立而一致的立场;像他那样同时抱有理论及实践诉求的人,常常有充分的理由将自己独立而又一致的立场的不同侧面展示给那些来自神学、哲学或政治的相互对立的阵营中的通信者们。[8]换句话说,使得人们能够前后一贯地解释莱布尼茨的那些纯哲学文本的钥匙,常常要在莱布尼茨非哲学的诉求中,在他更宏大的智力规划中,或者在单独的文本在其中被写就并意图被公开阅读的政治背景中寻找。莱布尼茨的哲学疑有许多不同的面向,其思想生活也同时拥有极度内敛的私人一面,以及积极介入的公共一面;但是二者之间的不同更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并非那张同时暴露真诚的私人哲学和虚假的公共哲学的雅努斯罗马神话中掌管门户出入与水陆交通的神,拥有两副面孔。之面(Janus face)。
总之,近几十年来,通过将文本复原到其所属的思想与历史语境中,莱布尼茨研究在消除误解、纠正失衡,以及找出多种方法来展示莱布尼茨不同思想侧面的相互契合及共同发展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在这个背景下,莱布尼茨那些表面上异质的活动的完整的统一,第一次变得明显。莱布尼茨出生于三十年战争结束前两年,是一个力图综合与和解的人。他坚信知识的统一,坚信经由持续不断的理智的交流和对话所发现的以及从人类千年思想的宝库中所发掘出的真理的普遍价值。同时,莱布尼茨也是一个“海阔天空”的思想者(bluesky thinker),为了在各种不同的领域中提出引人瞩目的新洞见,他总是毫不迟疑地与一般观念分道扬镳。对于他来说,手头上的问题,不论是哲学的、数学的、科学的还是实践的,通通都是作为整部科学大百科全书的所不包的、系统的发展计划中的一部分,并且这个计划也是要经由一个有远见的统治者的公开支持,作为一项合作性事业来加以开展的。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类生存条件的改善以及由此对上帝的创世荣耀(the glory of God in his Creation)的赞美。因此,他的那些有关逻辑学、数学、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和神学的最理论化的沉思最终都服务于生活,致力于人类的幸福。在他为柏林科学协会所写的引人瞩目的格言中,他说他的具有范导性的理想目标(regulative ideal)是促成理论与实践的联姻。的确,为了他的那些逻辑的、数学的和形而上学的高妙的思考,莱布尼茨始终脚踏实地,他认识到相比许多被拔高的沉思来说,政治的稳定、健康与社会安全对人类的幸福更加有益。莱布尼茨就是这样一个人,与其他任何事情相比,他更愿意做原书为斜体,今用黑体,表强调。下同。事。一旦他发觉自己一些炫目的哲学观点会引起纷争及误解而达不到他的主要目的,那么他宁愿将其保留起来不予发表。
尽管莱布尼茨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像一个让人晕头转向的万花筒,但其思想生活的广度、宽度以及深度都聚焦在一项全局式的规划中,这项规划可以为他大多数看上去纷繁芜杂的劳作提供统一性,并且,如果逐一检索,这项规划也提供了线索让人们可以从他那不可计数的、内容广泛的生活片段中提炼出一个前后一贯的中心目标。从根本上说,莱布尼茨穷其一生都怀抱着同一个梦想:把多样的人类知识统一为一个逻辑的、形而上的和可付之教化的整体,这个统一的整体以天主教传统的有神观念为中心并致力于追求公共的善(the common good)。这项规划被表述在一系列描绘了如何改革与提升整个科学大百科的综合计划的概述性文本中。在莱布尼茨年轻之时,这项规划被设想为“天主论证”(Catholic Demonstration);随后,它被表述为一门“一般科学”,并且这门“一般科学”要在一部“明证性的”(demonstrative)百科全书中得到论述;最后,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它又被重申为“普遍哲学与自然神学原理”[9]。如果按照莱布尼茨这包罗万象的计划来解读,其遗作中的大量片段和手稿就会呈现出一种令人惊讶地连贯的形态,并且他在政治介入或制度改革中所做的很多更具体的工作也会与一组核心原则及目标联系起来。
尽管学者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莱布尼茨的广博思想下所潜藏着的统一性,但提纲挈领式的综合陈述仍旧付之阙如。近年来,质量最高的研究已经出现在这幅全景中的某些重要部分中。有人通过将核心的哲学信念归置于大的理论背景,系统地研究了莱布尼茨思想中的某些重要论题。有人跨越莱布尼茨一生中的相当长的时间追溯了他某些思想要素的发展。还有人广泛地——甚至详尽地——叙述了莱布尼茨在某些特殊时期的活动的方方面面,例如在萨克森的青年莱布尼茨,他的巴黎岁月,意大利旅行期间,等等。关于其他重要主题,也出现了非常宝贵的研究作品以及资料汇编。但是,一部能够根据最近的研究来详细地考察莱布尼茨的生活以及思想的真正的概要性作品仍没有出现。1842年由古哈尔(Gottschalk Eduard Guhrauer)所著并由布雷斯劳出版社(Breslan)出版的传记仍是经典之作。[10] 20世纪最重要的作品由数学家艾顿(EJAiton)所作,它更简短,主要在莱布尼茨的科学和数学思想方面对古哈尔做了补充。[11]另外,前段时间赫希(Eike Christian Hirsch)用通俗易懂的文笔向一般大众生动地讲述了莱布尼茨的生活,这也应当被提及。[12]考虑到自冯特奈尔以来就困扰着传记作家们的诸多困难,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该领域中并没有太多关于莱布尼茨的学术性传记;但是现在学者们的视野已经拓宽并深入了,对一部新的概要性作品的需求就变得迫切起来。
同样必要的是用叙事的方法来尝试这种理论上的再次统一。仅常识就可以表明采用叙事方法的必要性。如果莱布尼茨思想的异常多样的领域可在一种一贯的综合性(a coherent synthesis)中相互勾连,那么理所当然的是,这个庞大的体系并不是在一瞬间内形成的,而必定是从一些基本的直觉、猜想或志向开始,并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演化逐渐形成的。再者,对莱布尼茨成熟时期的文本的阅读经验也证实了这种必要。甚至是对像“单子论”这样的莱布尼茨形而上学命题的成熟表述,也常常会使人困惑不已,不仅仅因为它们缺乏用来支持其立论的全面的资料,也因为其论证的过程糅合了他几十年以来同时也是跨越多种学科所习得的思维发展的样式。如果被看成是思维的长期演化的结果,他的结论往往变得容易理解得多,也有力得多。另外,历史研究也证明了遗传学方法即上文所说的“叙事的方法”。的不可或缺。至少从凯贝茨(Willy Kabitz)开始,专家们就已经意识到莱布尼茨的许多最基本的哲学信条是在很早的时候就被确立起来的。[13]然而,如果叙事性的阐明必不可少,那么这里的叙事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哲学方面。莱布尼茨尝试解决的问题远远超出了哲学领域——甚至是17世纪那种宽泛意义上的哲学——从而囊括了技艺和科学(arts and sciences)的大百科。事实上,它们的确超出了理论性的思考,进而将实践的关怀也包括了进来:政治学、伦理学、法学、医学,实践的、社会的和机构的改革,以及技术上的创新。正如对莱布尼茨思想的综合表述需要一个叙事的维度,叙事也必须从哲学扩大到他思虑所及的整个世界。
至此,我们又遇到了另一个难题;莱布尼茨生活在一个复杂而陌生的时代——现在已不存在的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the Holy Roman Empire of the German Nation)——这个时代深刻地影响着他一生中的每个阶段以及工作的每个方面。教会、政治与文化分裂的问题在中欧尤其严重,它们影响了在莱布尼茨之前的几代中欧知识分子,而这些人也给予了莱布尼茨那所不包的综合性规划最早和最持久的影响。正是这些最初的志向过滤了莱布尼茨后来受到的影响,而且它们也提供了智识语境(intellectual context)来整合他那看起来万般混杂的工作。同样地,这些奠基性的志向以及统一性的规划使莱布尼茨与同时代最出名的西欧人士截然分开,它们也解释了莱布尼茨在不同地区所受到的不同待遇:同时代的英国人怀疑他,晚一辈的法国人奚落他,而他对18世纪的中欧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则产生了巨大影响。最后但却绝非次要的是,莱布尼茨生长于斯的德国的具体环境,也为理解他的那些有关政治、外交、机构改革和教会重组的宽泛的非哲学的兴趣和活动,为理解这些活动与其相对狭窄的哲学关怀之间所具有的一贯性提供了钥匙和途径。因此,将莱布尼茨还原到他的中欧背景给我们提供了契机来恰当地描绘他,不是将他刻画为一个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落后的弱小的中欧邦国中被莫名其妙地孤立起来的现代西方知识分子,而是刻画为一个早期现代思想(early modern thought)——它在事实上曾受益于一个长期而富含成果但却或许在很大程度被忽略了的传统即中欧传统。——的特殊的中欧变体。因此,让莱布尼茨的生活和思想统一起来的许多要点可以在相对不出名的地方找到(还很少有人想到过要在这些地方寻求答案):不仅仅,或者说并不首要的是在巴黎、伦敦、海牙,而是应当在莱比锡、阿尔特多夫(Altdorf)、纽伦堡、黑博恩(Herborn)、黑尔姆施泰德(Helmstedt)以及沃尔芬布特(Wolfenbüttel),还有更显要的美因茨、汉诺威、维也纳和柏林。这是为破译莱布尼茨的遗著——如果还有任何工作是必要的话——所追加的挑战。
用莱布尼茨自己的语汇来说,冯特奈尔首次遇到的难题是:怎样将莱布尼茨行为的多样性还原为一个在传记中得到表述的统一体。让我们使用上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来编写一部智识译者将intellectual biography译为“智识传记”,理由如下:“智识”即“理智性质的见识”。按照作者的说明,这本传记所记述的内容不仅包括莱布尼茨的理论,也包括他的实践,但论理论和实践都具有可整合为一体并可获得理性说明的线索与结构。在中文的语汇中,“理智”与“感性”相对,“思想”与“行为”相对,如此的翻译都难以涵盖此传记意图体现的综合性,而“智性传记”则带有过强的康德哲学的痕迹,亦不取;唯独“识”则不只有“理论、理智”的含义,也意指一般的认识、见识,在特殊的语境中,甚至涉及人类身心的全部维度,如佛教唯识论中的“八识”。故“识”涵盖着“行”,不缺乏身体、行为、实践的内涵,因此“智识传记”是比较贴近作者原意的。而相应地,行文中的intellectual则根据上下文做不同的处理,如译成“理智的”、“智力的”、“思想的”等。传记,这部传记可以由四个基本的、奠基性的论点统一起来。第一个论点是,莱布尼茨的生活和工作需要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价。以往人们要么仅仅根据他的逻辑学或形而上学来刻画他的哲学,要么仅仅根据他的哲学来刻画他的思想,要么仅仅根据他的思想来描绘其一生,与这些倾向相比,这个论点主张:对莱布尼茨的全面而充分的理解必须包括他的生活和工作,他的理论的反思与实践的活动。因此,总括的说明(a comprehensive account)是必要的。
与此相关,第二个论点主张该整体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统一体。它不赞成将莱布尼茨的实践活动看做是使其从哲学研究上分心的可悲的事情,不赞成回顾式地将其思想事业中的一部分看得比其他部分更加珍贵。与此相反,这个论点试探性地假设莱布尼茨的生活就像他的思想一样:其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被少数几个基本原则与目标统一在一起,并且其中的每件事情都相互关联。更直接地说,它假设这最后一个全才(the last universal genius)并不是傻子,对于所有他能获得的资源,莱布尼茨并不是一个蹩脚的裁判,他从中选取了那些最能促进其核心事业的选项,而通过所有他那些主要的工作,莱布尼茨都要向我们诉说这与他的核心目标究竟有何关联。因此合理地进行系统性以及综合性的说明是必要的。
第三个论点:这些统一性的原则和志向中最基本的东西在相当早的时候就已经被确立,并且莱布尼茨生活和思想中的诸多要点也是从其中有机地生长起来的。虽然这样的研究进路绝不会视莱布尼茨成熟的哲学理论的重要性,但它还是强调这种哲学的种子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种下。在某种意义上,莱布尼茨理论体系中最基本的特性已蕴含在其开端之中,这让人联想到他的“单子”。与此同时,既然他的理论规划最终指向实践的目标,他也并不拒绝——实际上是在积极地追求——卷入实际事物之中。当新的发展态势以及不断改变着的环境重塑着莱布尼茨试图用来达到其目标的手段之时,他仍然以非同寻常的坚韧保持并追求着他原初的想法。因此,叙事性的说明是必要的。
最后,这些与众不同的诉求能够被极早地确立并固执地坚守,是因为它们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深深地扎根于莱布尼茨所生活的国家的大环境中。有人将莱布尼茨描绘为一个困于思想的一潭死水之中的进步的西方人,与此相反,本论点主张莱布尼茨本质上是一个德国哲学家,或者更加明确与充分地说,是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哲学家。虽然他的祖国在领土上以及宗教上的分裂使他最终丧失了实现其许多远大志向的资源,但首先正是这种分裂的状况使得这些志向产生并加以维持,而也是这些志向使得莱布尼茨极大地区别于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西欧知识分子。因此,尽可能紧密地与具体的历史背景相联系而做出阐明也是必要的。
当然,以上四个论点都不是全新的。尤其其中的第二和第三点在许多新近出版的高质量的莱布尼茨文献中都得到了或明或暗的阐发。但是将它们统筹起来并深入挖掘的唯一方法乃是将其编入一本综合的、系统的、叙事的并依据历史语境勾连而成的单独的大部头著作中。于是本书的总体目标便在于,通过强调一个包括了思想和行为在内的普遍和谐的系统在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所经历的有机的发展,来将冯特奈尔及其后继者肢解过的莱布尼茨重新整合起来。在这样做的同时,它也试图捕捉17世纪以及18世纪早期欧洲思想特质中的一些核心要素;对于这些思想特质,莱布尼茨既是典型的代表又戏剧性地超越了它们。通过传记叙述的载体来糅合各种复杂的理念,本书想要以这种方式表明:正如同生活只有在它的时空语境中才能得到充分理解一样,思想又是如何只能够在生活的语境中才能得到透彻理解的。
上述一般性的策略仍然留下一个更乏味(prosaic)意思是这种问题只有不理解莱布尼茨的智力能力的人才会提出,故显得乏味。的问题,即怎样对待莱布尼茨那种能够在他整个一生之中同时从事数条不同线索的理论研究的能力。纯粹的编年体例显然不切实际。有关莱布尼茨的生活和工作的详细的编年表在由穆勒(Kurt Müller)和克朗特(Gisela Krnert)所著、于1969年出版的极有价值的著作——《莱布尼茨的生活和工作》中已经存在;但这只是一部“参考书”,不被作为一本传记看待,而只是有关莱布尼茨的“学术传记的出发点,大家对这本学术传记的呼求已历时良久”[14]。如果人们对冯特奈尔最先遇到的问题的严肃性还有什么质疑,那么这本编年史便会将它展示余:在书的每一页我们都会看到有关“不同问题”的“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的混乱”,“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的突然而频繁的转换”。这让对莱布尼茨的思想和生活的任何严格的编年体的叙述都变得晦涩难解。
为了能用一种可以被我们这些并非全才的人们所理解的方式重塑莱布尼茨的一生,编年体的科学必须屈从于叙事的艺术。虽然以下诸章节仍按年代顺序编排,但在此框架下,各种或具体或抽象的发展脉络是以不同方式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一般来说,每一章(第一章除外)的开端都是对问题所涉及的相关时期做一个简要的概括。随后是对莱布尼茨的职业生涯在这一阶段的具体环境以及这一具体环境对他的研究工作的影响的详细说明。通常情况下,这种说明会中止,转而让位于对在这种语境(context)下莱布尼茨的心智发展(intellectual development)的其他特点的阐述,这样的阐述同样也会随处细分,以便保证多条叙事线索的推进。在这个过程中,笔者很小心地不在对众所周知的文本与理论的解释(exposition)上花太长时间,因为在这方面已有大量优秀的文献供读者们参考。正因为没有一条机械性的诠释规则能够应用于所遇到的全部问题,我们的应对方案就是让系统性的诠释服从于对心智发展过程的叙述,并将这个发展过程归置于它在本地的、帝国“帝国”原文为大写,指上文提到的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下同。的、欧洲的,有时甚至是全球的不断演变的语境之中。
最终,这本智识传记被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开篇的部分涉及莱布尼茨一生的前三十年,这个时期莱布尼茨可以相对地摆脱职业责任甚至父母看管的束缚来随意地进行身体和智力方面的探索,因此他也能够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发展起自己将用尽其余生来实践的见识、志向以及宏伟的规划。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志向得以追溯至生活在莱比锡——这个毫希望的外省环境里的少年莱布尼茨,在那里他已故父亲的教授品质的图书馆给这位早熟的少年提供了与传统的正规教育不一样的撷取丰硕精神食粮的渠道。在大学学习期间,莱布尼茨去往耶拿和阿尔特多夫,尤其是之后去往美因茨天主教廷的旅行拓宽并强化了其见识中有关神学、哲学、法学以及政治的蕴含。接下来在思想重镇——巴黎和伦敦所渡过的极为宝贵的年月,莱布尼茨的主要精力都花费在获取那些为实践其雄心壮志所必需的数学与哲学方面的最新的精密工具上。
在这段时期的末尾,莱布尼茨被迫放弃了永居巴黎的梦想,而他一生中第二个主要阶段,即后四十年,则目睹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他努力地想要从作为汉诺威省府的法庭顾问这个不利的背景中挣脱出来,去实现自己年轻时的理想。从行动上看,这种挣扎从莱布尼茨自己的梦想与其上司的要求之间所存在着的紧张关系中可见一斑,莱布尼茨想要自由地游走于当时的文坛,而其上司则越发强硬地要求他在汉诺威的岗位上随时待命。在思想上,这种挣扎同样清楚地反映在二者意愿的对立中,莱布尼茨孜孜以求实现自己的学术雄心,而他的上司则同样坚决地要求他要为布伦瑞克—吕内堡王朝(BraunschweigLüneburg)的相对狭隘的利益效力。面对这些困难时,莱布尼茨并没有显得优柔寡断、反复常,反而心中充满了想象力与决断力。大量的旅行使他通过讨好权臣而得以追求自己的目标,论是在汉诺威,还是在临近的公国,或者皇都,或者神圣罗马帝国之外以东、以南、以西的政治、文化中心。当回到汉诺威时,他则坚定地将其官方职责扭转为追求个人抱负的手段:法律协商、外交谈判、政治评论、技术创新和历史研究都成为莱布尼茨实现他那长期存在的计划中某方面内容的方式。论是在家乡还是在异国他乡,或者是在欧洲的王宫里,或者在哈尔茨(Harz)的矿井中,一得空闲,莱布尼茨总会发现些在逻辑学、形而上学、数学、物理学、神学、法学、伦理学领域中的新想法,从而持续地就自己的计划中理论的部分做出清晰的阐明,并与遍布整个欧洲以及欧洲以外的数通信者们交流自己理论体系中的一些片断。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故事中,悲喜的叙述不免相互交织:一方面是各种层次上的具体的困难,与上司的不和、与对手的争执、可避免或者不可避免的分心、工作方法上的缺陷以及对某些不可实现的愿望的固执追求;另一方面是尽管面对这些困难却能够持续获得的出色成果,以及我们的故事主角本人法遏止的乐观心理及良好心态。后来,莱布尼茨从维也纳(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长期羁留在此)被拽回汉诺威,结果只是发现王朝的主体已经丢弃了这座城市,前往伦敦;两年后,莱布尼茨去世,留下未竟的事业:一是作为官方计划的对韦尔夫家族历史(Guelf history)的编写,一是在数以万计的未出版的著作残篇中仅仅得到部分实现的私人计划。但是,论他的世界是否朝着他所期待的方向发展,直到生命的终结莱布尼茨都一直坚定地相信,自己所居住的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它由上帝的全知全善创造而成并朝向更美好的未来。
我们给莱布尼茨画出这样的肖像,实际上是特意地在一个重要的方面让它不能代表本人。他为两篇内容极为丰富的论文作序并以上千页的历史文献为支撑,花了几十年时间将一本简要的韦尔夫家族史扩充为一部卷帙浩瀚的历史年鉴。面对这部历史著作以及莱布尼茨去世后所留下的其他资料的卷幅、内在关切和复杂程度,任何一个勤恳的传记作者都可以轻易地投入其一生的时间来研究莱布尼茨的生平,并留下一大堆未完成的草稿。尽管在这方面模仿莱布尼茨的做法很有诱惑性,但我的目标却是在一段有限而又得到清晰界定的时间跨度之内,沿着前文提到的线索完整地讲述一个故事(an account)。不用说,有关莱布尼茨著作和信件的可修正版本的持续出版提供了取之不竭的资料来源,这方面还有众多或主要或次要的版本、译文及莱布尼茨档案馆所持有的丰富资源的补充。当然,直到可修正版本的巨大出版工程告罄,有关莱布尼茨的传记才有可能声称自己是完善的。同样地,直到对莱布尼茨的研究文献在历史上的不平衡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纠正,从而更多的注意力导向在他的生活和思想中占有巨大比重的非哲学方面,人们的著作才能够完整地勾勒出莱布尼茨的形象。但是不管怎样,对莱布尼茨的研究极不可能完善到以下这种地步,即人们对他的研究将不可能做出任何改进了。一个更让人愉悦的前景是,要将莱布尼茨研究的世界(the world of Leibniz studies)看做是,就像莱布尼茨所谈到的那个所有可能世界中的最好的世界那样,处于一种为了更加完善而不断前进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本著作所能希求的极致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将莱布尼茨研究缓慢地推向前进。
注释
[1] 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loge de MLeibnitz,” in Histoire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Année 1716.Paris: Impr.Royale, 1718, pp94128. Also in Dutens I, xixl iii (here pxx). Trans. by RAriew in “GWLeibniz, Life and Works,”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Leibniz. Ed. by Nicholas Jolley. New York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9.
[2] Leibniz to Vincentius Placcius, March 1696 (Dutens VI, 65).
[3] 关于ms.档案馆, 参见Eduard Bodemann,Der Briefwechsel des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der Kniglichen ffentlichen Bibliothek zu Hannover.Hanover, 1889; repr. Hildesheim: Olms, 1966 and Eduard Bodemann,Die LeibnizHandschriften der Kniglichen ffentlichen Bibliothek zu Hannover,Hanover, 1895; repr.Hildesheim:Olms,1966。包含莱布尼茨作品及书信的批判性版本的八个序列的名称已在“缩写”中列出。
[4] 复杂的出版历史,参见Emile Ravier,Bibliographie desuvres de Leibniz.Paris: FAlcan, 1937; repr.Hildesheim: Olms, 1966; 另见Paul Schrecker, “Une bibliographie de Leibniz,”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 126 (1938): 324346。
[5] Albert Heinekamp, ed.,LeibnizBibliographie. Die Literatur über Leibniz bis 1980.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84.
[6] 更多的近期文献,参见Albert Heinekamp,ed.,LeibnizBibliographie. Die Literatur über Leibniz 1981—1990.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6; 以及bibliographie.de上持续更新中的参考书目索引。
[7] 参见Bertrand Russell,A Critical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Leibniz.2nd ed. London: GAllen & Unwin, 1937, ppvi, xiiixiv。
[8] 参见Donald Rutherford, “Demonstr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The Eclipse of the Geometrical Method in Leibnizs Philosophy,” in Leibnizs ‘New System’(1695).Ed. by Roger SWoolhouse. Florence: Olschki, 1996, pp181201。
[9] 参见Heinrich Schepers在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vol14, p125中关于莱布尼茨的词条,以及他对于A VI, 4 的“导论”(Einleitung)(esp. ppxlvii, liii, lxxxi)。Demonstrationes Catholicae与the scientia generalis之间的关系,参见chapII4。
[10] Gottschalk Eduard Guhrauer,Gottfried Wilhelm Freiherr von Leibnitz. Eine Biographie.2 vols. Breslau: Hirt, 1842. 2nd enlarged ed. Breslau: Hirt, 1846; repr. Hildesheim: Olms, 1966.
[11] EJAiton,Leibniz: A Biography.Bristol and Boston: Adam Hilger, 1985.
[12] Eike Christian Hirsch,Der berühmte Herr Leibniz: Eine Biographie. Munich: Beck, 2000 (cfp627).
[13] Willy Kabitz,Die Philosophie des jungen Leibniz. Untersuchungen zu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seines Systems.Heidelberg: Carl Winters Universittsbuchhandlung, 1909.
[14] Kurt Müller and Gisela Krnert,Leben und Werk von GWLeibniz. Eine Chronik.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69, pix.(最终的短语取自书套。)
……
导言
第一部年轻时光(1646—1676)
1.眼界初生:背景、童年及教育
(1646年7月—1667年2月)
2.眼界拓展:纽伦堡、法兰克福与美因茨
(1667年3月—1672年3月)
3.新瓶装旧酒:巴黎、伦敦与荷兰
(1672年3月—1676年12月)
第二部梦想和现实(1676—1716)
4.作为图书馆长、历史学家和采矿工程师的
全才:汉诺威与下萨克森
(1676年12月—1687年10月)
5.踏寻韦尔夫家族的脚步:南德国、奥地利与
意大利(1687年11月—1690年6月)
6.返回韦尔夫公爵治下:汉诺威与沃尔芬布特
(1690年6月—1698年2月)
7.在哥哥与妹妹之间:汉诺威与柏林
(1698年2月—1705年2月)
8.光明与阴影:汉诺威、柏林、沃尔芬布特、
维也纳(1705年2月—1714年9月)
9.尾声:在汉诺威的最后岁月
(1714年9月—1716年11月)
附录
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