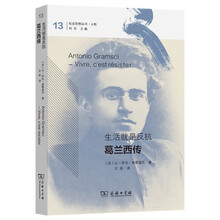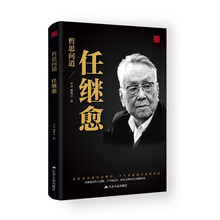《论衡之人:王充传》:
然而,王沉的期望等来的是失望。王蒙、王诵昆仲长大后勇蛮任气,比他们的爷爷有过之而无不及。“世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唐勇势凌人。”王汎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却无能为力,只好默叹命该如此。一方面,王家尚勇任气习性的遗传实在强烈,王蒙、王诵二子承袭祖上遗风,禀性难移;另一方面,这也是王家的漂泊处境使然。处于弱势群体的人家,昭彰武勇不失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唯其如此,方不致被人随意欺侮。王沉于这样的无可奈何之中,走完了王家世系接力棒中的一程。失去父亲管束的王蒙、王诵兄弟在蛮逞匹夫之勇方面更加放肆,凶悍的名声远近皆知,结果与“豪家丁伯等结怨”,在钱唐又待不下去了。王家再次南下渡江,东进到上虞章镇一带落户,以务农为生。
王家在章镇结束了漂泊不定的生活,安顿下来。这里是天然的鱼米之乡,司马迁曾在《史记》中记述此间的自然状况与人居条件:“地广人希(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窥偷生,无积聚而多贫。”这里虽然生产力水平低下,但地多人少物产盛,还是很养人的。经过汉代一百多年的发展,越地的农耕程度比司马迁所见,又有了进步。正常年景,普通农户只要随意稼穑,可不为温饱发愁。更让王家受用的是,当地无豪强欺侮外乡人,再也不用日日生活在遭仇家打击的恐惧之中,王家品尝到安居乐业的滋味,很自然地对过去的岁月进行反思:王家凭武勇为国御敌、建勋邀赏的日子已成遥远的过去。身为平民,热衷于打打杀杀,终究不是立家之本,想过个太平日子亦不可得,耕读传家当为立家立业的正途。安于做一户自给自足的普通农家,自食其力,勤于劳作以求生活改善,渐成家庭成员的共识。王诵浮躁不安的心态得到沉淀与调适,那种徒逞快意、容易冲动惹事的武人脾气趋于淡化。此变化可从王充《论衡·自纪》中窥见蛛丝马迹。王充记王蒙、王诵在钱唐时“勇势凌人”“滋甚”,到上虞后却未再出现滋事成仇的记录,家庭也未再因避仇而迁徙。
王诵成家了。结亲自古讲究门当户对,王家自王勇起即落魄潦倒,作为外乡来的游散平民,给后代娶亲不太可能攀附到为数甚少的北方军功人家,多半与当地民女结为夫妻,王沉如此,王蒙、王诵亦难例外。所以,王充的母亲十之八九是一位越乡女子。王家这一段的生活虽处于动荡漂泊之中,但比起当时中国的多数人来说,可谓不幸中的幸运。此间北方的大部分地区正遭受着新莽之乱的荼毒。失地流民所组成的绿林、赤眉军横行黄河两岸、大江南北,继而刘秀起兵逐鹿中原,战王莽、灭群雄,烽火硝烟绵延不绝十多年。战火过处,草木俱焚,小民耕无田亩,居无定所。相比之下,地处东南一隅的越地因远离政治中心,基本未受兵燹袭扰,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得以维系。《后汉书·循吏列传》记载:西汉更始元年(23),任延拜会稽都尉,“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延到,皆聘请高行如董子仪、严子陵等,敬待以师友之礼”。可见,会稽于西汉末年,堪称乱世中的一方安土,成为北方士族及“失所”之人的避难处。根据班固《汉书》及范晔《后汉书》,东汉初年会稽郡的人口较之于西汉末年增加了15万余。王家在北方大乱之前南迁定居于会稽,对于家族的延续与发展来说,应该算是福祸相应,福多于祸了。就在新莽之乱结束后,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史称“光武中兴”)的第三年(27),王充出世了。
这个呱呱坠地的新生儿禀承了什么样的天资呢?王家源出燕赵,世代从武,孤鲠刚烈、逞勇好强、宁折不弯的习性当为遗传基因的底色。这一点,在王勇、王沉到王蒙、王诵一脉相承之“任气”的脾气中显而易见。在王充身上不难看到这些性格特质,只是王充将桀骜不驯、争强好胜等化为贞介鲠直,并用于另一个目标——学究天人。不具备这样的品质,王充便不可能成为大思想家。王充母亲是位越女,越人发迹、成长于南方水乡,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底蕴,总体上表现出崇尚自然、轻死易发、进取务实、精明肯干的气质与习性,它们通过母系遗传流淌于王充的血脉之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北方人王诵与越女的结合,不仅超越了血缘关系,更跨越了地域,构成不同种群之间的结合。古代素有北人与南人结合生出聪明后代的说法,这是符合现代优生学原理的。具体到王充身上,其长成后所表现的超人智慧,与先天遗传的优异不无关系。
一个人从出生到少年时代,是其性格气质、爱好专长形成的重要时期,“性格决定命运”,一个人所要走的道路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在少年时代即可见其大概。性格的塑造受制于先天遗传、家境家风、生活环境、风土人情、文化影响等多重要素,这些要素随着年龄的增长依次递进、逐步展开,对生命主体产生综合影响,同时生命主体又依据本能和价值取向筛选、消化、加工各种外部信息,渐渐强化主体意识,凸显出有别于他人的性格特征。
王充出生时,王家经过祖上几代的大起大落,刚刚度过漂泊岁月安定下来,家庭氛围摆脱了重武轻文的习惯,走向安详、和谐,相应地也就萌生了对文化教育的渴望。
家境家风的转变使王充在成长中受益良多。他自小就远离动荡漂泊、躁动不安、喧闹不息的环境,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周围的一切,也有更多的时间体味自我、静心遐思,顺其自然地强化着自己的主体意识,这是日后理性思考的必备素质。家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简朴度日的艰苦生活也在王充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深深的印痕。他自幼便敬奉父母以及始终对劳动者感情深厚,均来自幼时家境的影响。
有着不凡过去的王家时不时会兴奋地谈起祖上的军功与荣耀,幼小的王充听来固然似懂非懂,但家人们那份豪情万丈的快意。那种睥睨一切的自信强烈地感染着他,构成一种充盈的生命力,也在无形中引导他小小年纪在眼界上超越小农人家执着于坛坛罐罐的局限,把思维和想象力投放于更广阔的时空中。
王充对自己幼时家境的影响和熏陶有着良好的感受。他成名之后,当有些世代儒门子弟挖苦他“吾子何祖,其先不载?况未尝履墨涂,出儒门,吐论数千万言,宜为妖变,安得宝斯文而多贤”时,他回驳道,“鸟无世凤凰,兽无种麒麟,人无祖圣贤,物无常嘉珍”,并不无体会地谈道:“是则澧泉有故源,而嘉禾有旧根也。”祥和的环境,成材的动力,王充自小浸润其中。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