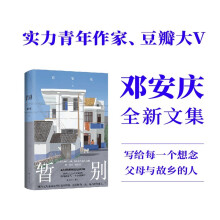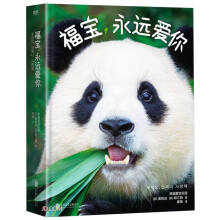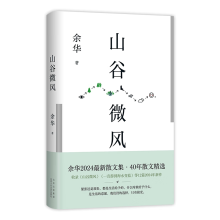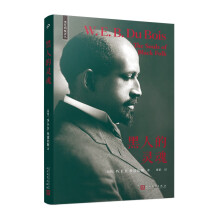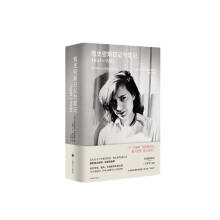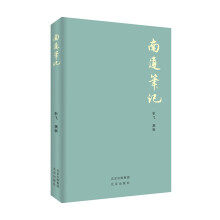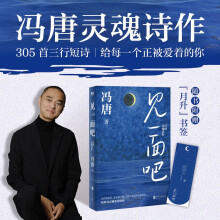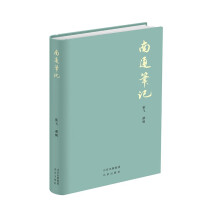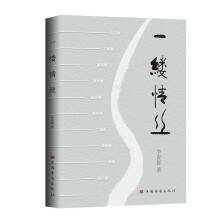《风景在你不在的地方/中国专业作家作品典藏文库·范晓波卷》:
初到麻州时,只在林子里望见几只放养的奶牛,时隔五年,就邂逅了不少拿着卡片相机的游客,他们的汽车歪着脖子栽倒在林中的树荫下躲避日晒。
这片樟树林的深度便被推土机和游客们的身影严重削弱了。
最初自驾游出行时,在高速公路上朝窗外望望就感觉在旅游。后来发现,田野的深度和道路的宽度是成反比的,就由高速而国道而省道而县道、乡道了,乡道之下,是开不了机动车只能徒步的蛇形小路。
连蛇形小路都没有的地方是田野最深的深度,这样的去处现在其实也不多见了,即便是在深得似乎到了世界边缘的山里,路在脚步不能翻越的山脊下断了,可是如果你有可能在空中俯瞰,山那边就有道路和人烟了,只是由于山脊的阻隔,两边都把彼此当作了尽头。
那些有深度的田野,往往保留着独立而完善的生态系统,植物以植物的脾性肆意蔓延,动物按照动物的食物链此消彼长,既彼此斗争又相互依存。唯一多余的物种是人类,不给人攀爬的坡度,也不腾出空间供你插足,甚至,你拿着望远镜都看不清它的深浅。或许也正因如此,它们的自足得以维持。在这样的田野面前,人类是不自信的,甚至充满了敬畏和恐惧感。
我刚读小学时,还常被豺狼叼走小孩的传闻吓得睡不好觉。豺狼偷猪、狐狸和黄鼠狼偷鸡的事也常在身边发生。因为长期和人较量,豺狼都学会了人的心计与狡猾,它猎杀体重远超自身的肥猪时,并不使用暴力,夜间翻人猪圈,拱开门,嘴巴衔着猪耳朵,尾巴充当鞭子一下一下温柔地抽打着猪屁股,猪就像被催眠一样不声不响地跟着豺狼走了,如果刚好是只母的,脑子里或许还萦绕着只是被掳去当压寨夫人的幻想。等脱离人的视野进了村后的山林,豺狼才露出劫命不劫色的本性。
那时还听说过六旬老太太走山路遇上豹子的新闻,老太太血肉模糊九死一生,最终还是凭着惊人的爆发力把豹子掐断气了。新闻的主角自然是人而非豹子,重点讨论人在危机时到底能激发出多大潜能。那时金钱豹和华南虎并不像现今,离人类远得像是一个传说。
再往前推二三十年,一九四九年前后,在鄱阳湖边的丘陵地带,都时有老虎伤人的事情发生。政府还悬赏号召猎户围捕为民除害。
我一个朋友的父亲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在鄱阳凰岗区政府工作时,常带队步行数十公里去县城开会,在山路上就亲眼看见过老虎,黄灿灿的皮毛在青翠的巴茅丛中格外耀眼。他被自己的心跳打乱方寸,慌乱之中胡乱放了两枪,老虎才极不情愿大摇大摆地走了。
虎豹的存活需要冗长而复杂的生态链与食物链,没有上百公里纵深的密林是无法养活一只虎豹的。可以想见,那时的田野是何其深邃而神秘。
生态学家的研究表明,因为人口的膨胀和科技的帮凶,人类近几十年对于自然的挤占和损坏,比过去几千年还要厉害。
这也渐渐培养了我近年对古典诗文及小说的热情。
当然,这更像是一种绝望的怀旧。
中国古典诗歌最常用的手法是托物言志,古诗里的物,最多的就是诗人们信手拈来的自然意象。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