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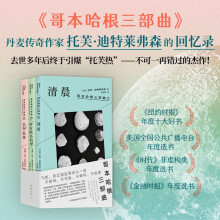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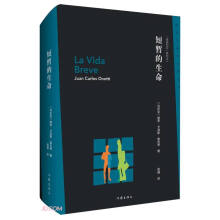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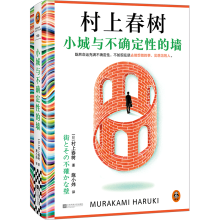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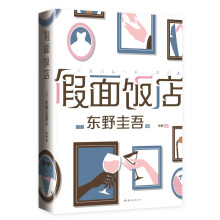


★ 银河英国图书终身成就奖、国会图书馆小说创意成就奖、哈珀•李法律小说奖得主约翰•格里森姆,被誉为“法律类小说的代名词”
★ 作品被翻译为42国语言,总销量超过3亿册,9部小说被改编为电影
★ 当代法律和犯罪题材通俗小说的实力派作家、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受欢迎的畅销小说家,每部作品一经出版必引起轰动,2018年作家福布斯榜排名全球第4。
★ 作家阿乙、小白对他推崇备至,称他的作品“内容丰富、意味深长”。
★“二十世纪流行经典丛书” 着重遴选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知名度高、引起巨大轰动,在我国读者中曾产生较大影响,且其严肃内容和通俗形式结合较好的通俗小说佳作。
格里森姆的小说叙事明快、简洁,文字和情节酣畅淋漓,《非常正义》的主人公塞巴斯蒂安·拉德俨然是 21世纪的菲利普·马洛,是一个亦正亦邪的法律界战士,他以种种特立独行的思考方式和办事风格,游走于守法与非法之间,却始终坚持一个律师所应有的道德底线。
塞巴斯蒂安•拉德不是一名普通意义上的律师,而是一名游走在正邪灰色地带的法律独行侠。他没有豪华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场所是一辆特制的防弹车;他手下也没有专业的雇员,他唯一固定的合作伙伴是他的全副武装的司机,同时也是他的保镖、法律助理和知己。塞巴斯蒂安专门为那些其他律师不会走近的人辩护:毒贩、顽童、黑帮老大,等等。之所以将这些人视为自己的客户,除了名声与金钱的吸引之外,还因为塞巴斯蒂安始终坚信:每个人都有权利得到公正的审判。
我叫塞巴斯蒂安•拉德,尽管我是位大名鼎鼎的街头律师,但在大型广告牌、公交站头,你都看不到我的名字;翻开黄页目录,我的名字也不会向你迎面扑来。尽管我常常上电视,但我从不交一分钱“出镜费”。我的名字同样不在任何电话号码簿里。我没有通常意义上的那种办公室。我随身带着把枪,那可是合法的,因为我的姓名和面孔容易吸引那些同样带枪,而且对开枪不计后果的人士。我一个人住,通常也是一个人睡,我没有足够耐心和理解力维持友谊。法律就是我的生命——它总在消磨、偶尔会满足我的人生。曾经有位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的名人,给法律起了个非常著名的外号叫“充满嫉妒的情妇”,但我不会那么称呼我的职业。对我而言,法律倒像是个“悍妇”,时刻控制着我的钱包。我已无路可逃。
这些日子,我发现自己晚上都睡在廉价的汽车旅馆里,而且每个礼拜都换一家。我不是在省钱;其实,我是在逃命。此时此刻,很多人都想杀我,其中一些人公然叫嚣要杀我。在法学院里,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某天我会为某个极端凶残案件的被告人辩护,甚至一些平日里温文尔雅的相关市民,居然也会冲动地拿起枪支,威胁要杀掉被告人,杀掉他的律师,乃至杀掉主审法官。
不过,我不是第一次受到威胁。十年前,当我不知不觉滑入到“流氓律师”这一法律分支后,受威胁就成了我不可避免的家常便饭。当时,我法学院刚毕业,饭碗十分难找。我无奈地在市公共辩护律师办公室里找了份兼职工作。从那里起步,我又转到一家小型、不赚钱的刑事案件律所。过了几年,那家律师事务所被炸飞后,我于是成了一名法律个体户,在大街上和一大批和我有着同样身份的人士,抢点小钱,混口饭吃。
有一起案件,让我成了焦点。严格意义上讲,我不能说是它让我成了名。试想,在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里,一个律师怎么会成得了名呢?很多当地的“律师混混”他们一面在广告牌上冲你微笑,一面暗地里诅咒,盼望你早日破产;他们在电视里神气活现地做广告,似乎真的很关心你的遭遇,而实际上,他们是付了钱,在荧屏上自吹自擂而已。我可不会那样做。
廉价汽车旅馆每周结一次账。我目前正在一个惨淡落后的乡下小镇麦罗打官司。这里离我居住的都市,有两小时车程。我的委托人是个十八岁的脑残辍学生。尽管我对杀人案见多识广,但他被指控杀害两个小女孩的手法,是我平生听过最残忍的案例。我的委托人通常都是有罪的,因此,我并不会花很多时间扼腕纠结于他们是否罪有应得。但在本案上,贾迪的确是无辜的——可这已经无所谓,无关紧要了。麦罗小镇这些日子里的头等大事,就是让贾迪罪名成立,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好叫整个镇上的人们宽下心来,大家的生活得以继续。往哪继续?见鬼了,我怎么会知道?好在我也不在乎。这个地方已经持续倒退了五十年,错判一起案子,对他们来说,丝毫也不能阻挡历史的进程。我读到并听到过麦罗小镇需要“划上一个句号”。管它是什么意思,反正大家都在说。但只有傻子才会相信,一旦给贾迪打了毒针,小镇就会立即旧貌换新,蓬勃发展,并且变得更加宽容。
我的工作涉及多层面,错综复杂;同时,却也是相当简单。州政府支付我工资,让我为死刑嫌疑犯做出一流的刑事辩护。这需要我在没人认真聆听的法院里,天翻地覆,拼足老命地进行斗争。贾迪被捕的那天,基本就算是被定罪了。对他的审判,也就是走个过场而已。那些傻头傻脑却又孤注一掷的警察们,不断抛出指控,伪造了一个又一个罪证。检察官当然完全明白,但他毫无斗志,一心只想着明年得到连任。法官在打瞌睡。陪审团基本都是一群善良而单纯的人们,在审判过程中,睁圆着双眼,随时愿意相信他们那骄傲的政府机构,在证人席上不停抛出的连篇谎言。
麦罗镇自己也有一些廉价的汽车旅馆,可是我不能住进那些地方。我会被上私刑,被剥皮,或被架起来烧烤。要么算我走运,会被狙击手一枪击中眉心,让我瞬时间一了百了。虽然整个审判期间,州警察确实给我提供了保护,但我明显感觉得到,这些伙计们好像并没有完全进入角色。他们看我的眼神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就是个长头发的流氓狂热分子,病态到愿意为摧残儿童的杀手以及类似犯罪分子的权利而斗争。
我此刻居住的汽车旅馆叫“汉普顿小旅舍”,距离麦罗开车二十五分钟。每晚六十美金的费用,州政府会给我报销的。隔壁住着“搭档”,一个全副武装的男人,他身穿黑西装,带着我东奔西走。“搭档”是我的司机、保镖、倾诉对象、法务助理、勤务,也是我唯一的朋友。当年,陪审团裁定他杀害便衣缉毒警官的罪名不成立,我因此赢得了他的忠诚。当我们手挽手走出法庭,从此便形影不离。起码有两次,警察下班后想要杀了他。还有一次,他们来找过我。
我俩依然站着走着。或者应当说,我俩依然蹲着躲着。
第一部分 鄙视
第二部分 轰响屋
第三部分 警察斗士
第四部分 交换
第五部分 U-Haul租车规则
第六部分 认罪
绝妙,极具创新……要做到这一切,对格里森姆而言依旧易如反掌。
——《华盛顿邮报》
格里森姆向引人入胜的方向迈出了新的一步。
——《纽约时报》
塞巴斯蒂安·拉德犹如21世纪的菲利普·马洛……有一种直率、粗鲁、沙哑、充满诗意和智慧的声音。
——《纽约时报书评》
极具吸引力和娱乐性……格里森姆让我们明白,我们的法律体系每天都在发生着激烈的小冲突。
——《今日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