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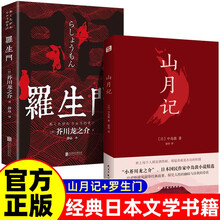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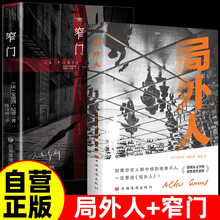

l 两度入围布克奖,诺贝尔奖热门候选人之一,英国科斯塔文学奖、百利女性小说奖及金匠奖得主,英国皇家文学学会成员,“蕞具天赋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继承者之一”
——英国当代作家阿莉·史密斯洞察当代生活的都市寓言,探讨分离与爱的温柔之作。
l 《卫报》《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出版人周刊》年度最佳小说
l 原柑橘文学奖入围作品、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短名单入围作品
l 时光交错的生活谜语、绵延记忆的灵魂偶遇
阿莉·史密斯用精巧的修辞与独树一帜的语言风格描写了四段截然不同却偶有交错的人生,探讨了人们对分离和真正的联结之间的矛盾需求,同时在机智与怜悯之间、超现实与深刻且感人的真实之间寻求平衡——只有阿莉·史密斯才能做到这种平衡。
麦尔斯·加斯参加了格林威治举办的一场晚宴,主餐完毕后,他突然上楼,将自己反锁在一间空卧室里,不愿离开,也拒绝交谈,只通过在门缝底下塞纸条的方式与外界沟通。这一事件引发了当地媒体的争相报道。人们聚集在窗外,只为一探此种行为主义背后的深层缘由。
阿莉·史密斯用精巧的修辞与独树一帜的语言风格描写了四段截然不同却偶有交错的人生,探讨了人们对分离和真正的联结之间的矛盾需求,同时在机智与怜悯之间、超现实与深刻且感人的真实之间寻求平衡——只有阿莉·史密斯才能做到这种平衡。
金句:
1.历史就是消失的或被处决的人、遭受灭顶之灾或者几乎遭受灭顶之灾的地方,以及承受苦难或焚烧的东西、地点或人。但是这不代表历史是看不见的东西。
2. 可以这样说,一个人的完整塑造不只归功于记忆,还有他的遗忘。
3. 真理如太阳。如果直视它,眼睛这辈子就瞎得什么也看不了了。
一个男人参加了一场晚宴。主餐完毕,甜点未上桌之际,他上楼将自己反锁在主人家的房间内。
曾经有一个女人,她在三十年前的一个夏天遇见了这个男人,他们相处了约两周时间,其间那个女人对这个男人了解甚微。那年,他们都十七岁。那之后的一些年间,他们偶尔也有互寄圣诞贺卡之类的来往,但却未再见面。
现在,那个叫安娜的女人正站在锁着的房门外,理论上来说,门的另一边就是这个叫麦尔斯的男人。她抬起手臂,手正准备——准备干什么?叩门?轻声敲门?任何一点儿嘈杂之声都会惹恼这座完美却又了无生趣的房子,哪怕开门的吱嘎声也是一种冒犯。而且已经有所不满的女主人就站在她身后两英尺处。但是,正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革命者的老套手势一般,安娜举起了拳头,她已准备好制造些动静。猛捶。连敲。重击。雨点爆裂①般地击打。
雨点爆裂?真是奇怪的表述。爆裂的雨点之上。他给安娜留下的印象不深,但倘若他不是那种喜欢蹩脚双关语的人,他们一开始也就不会成为朋友。如果换作是他站在锁着的门外,他是不是会与安娜不同,知道怎样让里面的人把门打开?他是不是会转身去逗那伸直腰板俯身躺在楼梯上看热闹的小孩——她的光脚丫踩着底楼大厅的木地板,手托着下巴,下巴已经伸到了第五级台阶;他是不是会立刻找到合适的玩笑话,问那小女孩:“你们都管放假的两只小蘑菇叫什么呀,有趣的家伙①?”是不是会马上滔滔不绝地谈起“雨点爆裂”出自何处之类的事情呢?
安娜身后的女主人叹了口气,不知怎的,她的叹气声听起来很深沉。紧接着是更深的寂静。安娜清了清嗓子。
“麦尔斯,”她对着门问道,“你在里面吗?”
但她声音颤抖,显得很不自然。“啊,现在,看我的。”——孩子好心地说,殊不知这好心其实不合时宜。这个很孩子气的女孩用手肘撑着楼梯站起来,跑上楼来正要捶门。
“砰砰砰。”
安娜觉得孩子每一记捶门都像是捶在自己胸口上。
“出来,从里面出来!”孩子叫道。
没有动静。
“芝麻开门!”孩子叫道。
敲门时她躲在安娜的胳膊下。此刻,她抬起头看着安娜。
“这句咒语能打开山边的石门,”孩子说,“故事里是这样讲的,一念咒语,石头门就会开的。”
小女孩把嘴凑到门前,又开腔了,但这次没有用力喊。
“咚咚咚,”她说,“谁呀?”
谁呀?
在人生的这个特定时刻,安娜· 哈迪有足够的理由思考,“存在”对她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其一是她刚刚辞掉的工作。她与同事戏称,自己的职位是高级联络官,并半开玩笑地将他们的公司称作临时工永久中心(或者,也可以叫永久性临时工中心)。
其二是几周前的某个晚上,四十多岁的她夜半惊梦,在梦中,她亲眼看到了自己胸腔内的心脏。 她的心脏因为被胎膜包裹而运作困难。那胎膜像是由我们晨起时从眼角处清除的垢物所组成的。惊醒后,她坐起来,用手按了按胸口,然后起身,走到盥洗室的镜前照了照。她还存在着。
这个说法让她想起在《晚报》工作的丹尼曾经告诉过她的事情。他们曾一起合作撰写了居住区居民活动的文章,而他们之间也有一段短暂的私情。他是在他们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共进午餐时跟她提起的那件事。丹尼是个体贴的男人。他们的第一次是在她的厨房里。他站在她身前,非常温柔地将他的阳具展露出来,羞赧,却又充满期待,对自己的勃起略感羞愧,同时又有些自豪。她对此很满意。她那时很喜欢他。但他们都清楚,吃过两顿饭后就不会再有下一次了。丹尼已婚,妻子叫希拉, 他们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在克莱蒙中学上学。安娜煮了壶咖啡,因为不知道他喜欢加什么,她就把糖和奶都放在了托盘上。她将咖啡端到楼上,又重回到床上。到了一点一刻,他们还有不到半小时的相处时间。丹尼问他能否吸烟。安娜说:“既然不会有下一次,有何不可?”他笑了笑。然后他在床上翻了个身,点燃了香烟,开始聊别的。他说他能用两句话总结过去六十年的新闻业,问她是否相信。
“你说来听听。”她说。
“我发生过。我存在过。”他说。
“这不是什么稀奇事,”他说,“二十世纪中期以前,每个重要报道都会如是说:我发生过。而现在会用:我存在过。”
“不久就有了第三句话,”安娜说,“新世纪的人们已经新添了一句:我存在过,伙计们。”他们大笑,然后喝完咖啡,穿上衣服,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他们最后一次交流是在几个月前,讨论了如何报道当地孩子将尿接在汽水瓶中给救济院的孩子喝的新闻。
几个月以后的那个午夜,她毫无感觉地按着自己的心脏,看着镜中的自己。她还存在着。存在的——镜中的她——是她的躯体。
两天前的夜里,这种感觉再次出现。当时正值夏天,她坐在笔记本电脑前,家家户户都开着窗,窗外不时传来邻居电视中在温布尔登进行的网球比赛的声音。她家的电视机也在播放同样的频道,但她把音量调得很低。那时的伦敦晴空万里,邻近的温布尔登绿草如茵,只是无法掩盖磨损的痕迹。越过电脑,能看到电视屏幕中的场景正不断切换着。不时传来的无法辨认声音源头的球的击地声、人们的惊呼声和失落声与她轻敲键盘的声音相伴,好像电视声带记录着的是整个外部世界。也许会出现一种叫作“网球选手精神病”的新疾病。患者认为自己始终被关注着,自己的每一个网球动作都能影响观众并引发观众与之互动。患者还相信自己的每个令人难以忘怀的瞬间都能引起他人愉悦、惊喜、失落或幸灾乐祸的情绪。兴许每一位职业网球运动员都有这种症状,那些仍然相信上帝的人或多或少也一样。这是不是意味着,从某种程度上讲,世界上没有这种症状的人的存在感就少了,或者至少存在的方式不一样,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那么受关注?安娜想,我不妨向网球选手的神祈祷。就像对待其他神一样,我们不妨请这个神赐予我们世界和平,保佑我们人身安全,保佑那些死去被埋于地下、羽毛化作尘土、骨头碎为沙砾的鸟儿重生,并让它们栖于窗台。让这些鸟儿按个头大小排着,小个的在前面,合唱一曲鼓舞人心的《再见,黑鸟》①。当她还是小女孩时,她父亲经常用口哨吹这首歌的旋律,如今她已经好些年没有听过这首歌了。
曾经有
但是
因为
这个
富于机智和刺激的都市寓言……如果你喜欢惊奇的和那些洞察当代生活的喜剧,那么史密斯值得拥有。——《纽约时报》
令人惊奇!极为聪明……点缀其中的幽默令阅读兴趣盎然。——《华盛顿邮报》
在史密斯的世界里,人们真正地联系在一起,并在彼此身上留下温柔的印记,这是一种迷人的浪漫主义。——《独立报》
太棒了……既有趣又感人。它的成功源于史密斯非凡的语言能力。——A.S.拜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