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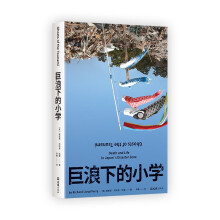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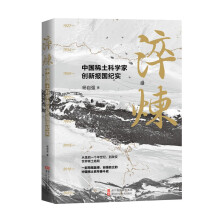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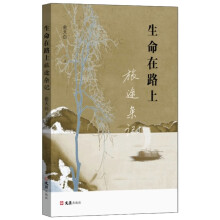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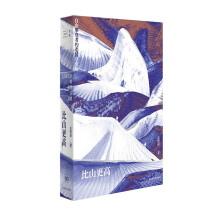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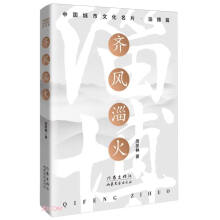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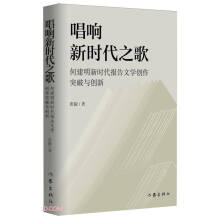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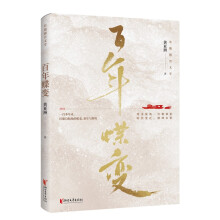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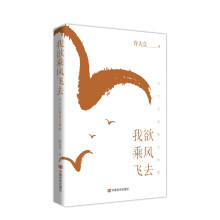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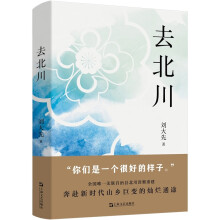
作者潘奕霖,采访了卢静、康辉、叶蓉、史小诺、郎永淳、瑶淼、凯叔(王凯)、鲁健、邵圣懿、尼格买提等知名主持人,深入挖掘每个人的青葱岁月、入行苦乐、创业艰辛、生活所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均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也就是原来的北京广播学院,他们对自己的母校,尤其是“广院”两个字有很深的情结,这也是本书书名的由来。
这是一场关于青春、梦想、困惑与抉择的对话,欢迎热爱、向往播音的你加入,与10位优秀主持人相约,感受横跨40年的中国电视业的辉煌历程。流逝的是时间,亘古不变的是对梦想的执着与渴望。
潘奕霖和他采访的主持人同行
潘奕霖是我在生活中遇到的第一个广院人。那是1995年的初秋,广院还没改名,还叫北京广播学院,2004年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直到现在,我们还喜欢用广院人称呼潘奕霖和他的校友们。潘奕霖在这本书里采访的主播们,也都来自广院。
我和潘奕霖相识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CCTV-6),那年央视同时新开几个频道,经过几轮考试后,我们一同考进了新成立的电影频道。他是主持人,我是撰稿人。
认识潘奕霖之前,我对毕业于广院,特别是来自广院播音系的主播主持人们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预设。他们有着不错的形象,声音都很好听,还有着超强的记忆力,可以把别人写好的文字精准地传达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或收音机旁的听众。作为撰稿人,我的工作应该就是把他要说的话一字一句写好,他再一字一句地背下来。
不过我们在开始阶段做着完全一样的工作。电影频道在开播前要准备出足够的片源,我们这些新招进来的人都以看片为主,每天连看几部电影,按照频道的要求写看片意见。为了在最短的时间里积累下最多的影片,我们不得不两班倒,上早班的早上六点开始看片,上晚班的要工作到晚上十点左右。潘奕霖在早班那一组,我上晚班,跟他对接时,我曾随手翻看过他之前做的记录。他的字迹很工整,每页纸上也没留空白,应该是个做事很认真的人。他还有很好的观点,有高度有深度,文笔也不错,我没想到做主持人的有这样的文字水平和思想,他好像并不需要撰稿人帮忙,可以自己为自己写稿。
除了审看片子写影片介绍,作为主持人,潘奕霖很快又接手其他的一些工作,出去采访一些电影人,采集片花、做节目导视、为宣传片配音…… 那是电影频道最艰苦的筹备阶段,超负荷的工作累垮了一些人,也吓跑了一些人,留下的免不了抱怨,大家凑一起时就发发牢骚。潘奕霖对身兼诸事一直没什么怨言,好像乐在其中,我这种一心不可二用的人就有些羡慕他,同时做着几件事,还能把每件事都做好。后来我才发现,做主持人的得有三头六臂,还要有很强的抗压能力。
1995年11月30日,电影频道试播成功,潘奕霖那富有激情和魅力的声音,随着一个崭新的媒体传遍了大江南北。
广大观众只闻其声不见其面的时间并不长,潘奕霖很快作为《流金岁月》的主持人出现在荧屏上。《流金岁月》是电影频道推出的第一个电视栏目,频道的领导发动大家为这个栏目起名字,最终选用的恰好是潘奕霖起的名字——《流金岁月》,这也算是潘奕霖跟《流金岁月》的缘分吧。
《流金岁月》最先确定的不是它的名字,而是它的主持人。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潘奕霖是这个节目无可替代的主持人,虽然那时候他还没有主持过电视节目。众望所归之下,他成为电影频道推出的第一个节目主持人。
1996年4月,《流金岁月》跟广大观众正式见面。这个栏目融电影剧场和评论访谈为一体,在每周一晚上的黄金时段播出一部经典老电影,影片播出后请这部影片的导演、演员等主创人员回忆当年拍摄时的幕后故事,也有专家学者和观众的评介。初上荧屏的潘奕霖还略显青涩,有时候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搁。《流金岁月》第一期的编导却在办公室里预言,潘奕霖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主持人。因为他非常敬业,不厌其烦地拍好每一组镜头,拍摄时总是全身心地投入,而且很虚心地接受编导和同行的指点,任何一个对节目有帮助的人都可以成为他的老师。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有非常好的天资和悟性,是一个做主持人的好料。
初次主持节目的青涩期果然倏忽而过,潘奕霖很快找到了做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感觉,并且渐入佳境,我们这些同事也渐渐看到了他的闪光点。他从不局限于背台词,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驾驭访谈。编导们都喜欢跟他合作,他不是一个被动的传声筒,他提的问题基本都是自己想出来的,而且问得很到位,不会说出让被采访者尴尬的外行话。他在节目中还常有奇思妙想,给他的合作者们意外的惊喜。遇到采访外国影人时,他还可以直接用英语交流。有次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个见面会,翻译不知跑哪儿去了,撂下几个外国影人和一帮外语一般的中国记者,一时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冷场,刚到现场的潘奕霖自告奋勇客串起翻译,场内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潘奕霖的表现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以前对主持人的定位有失偏颇,我们对广院出来的人有了新的印象。
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主持人,潘奕霖成为《流金岁月》的编导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他在做专职主持人的时候,就已经是半个编导了。有段时间《流金岁月》缺合适的编导,这个栏目当时的负责人就把目光投向了潘奕霖,没想到他编导的第一期节目就赢得了一片喝彩。
潘奕霖做编导延续了他一贯的敬业精神。为了采访到更多的老影人,尽可能地满足广大观众的愿望,他不辞辛苦地奔波于全国各地,让很多多年没有音讯的老影人又鲜活地出现在观众面前,这让关心他们怀念他们的广大观众兴奋不已。有些老影人并不乐于接受采访,这时候潘奕霖总是想尽办法说服他们。譬如我国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刘琼老师无意在电视节目中露面,后来潘奕霖的诚意终于打动了他。见面之后,潘奕霖对中国电影的了解令刘琼老师感到很愉快,两人聊得颇投缘。刘琼老师不仅破例接受了采访,还谈了不少,广大观众也就有幸见到了昔日“电影皇帝”的今日风采。
做编导不仅要做好前期的采访工作,还要做好后期的编剪工作。很少有主持人愿意坐在编辑机房一帧一秒地编剪片子,能拥有人前的风光,好像也就没有必要去接受人后的寂寞和繁琐。潘奕霖也可以找个理由把后期的杂事交给别人,但他一直是亲自动手,他认为前期和后期的工作是不能分割的,他要在一堆素材中精选出最感人的镜头。他跟那些老影人面对面地聊过,他知道他们在哪里动了真情,他是第一个被他们感动的人。我们有时走过编辑机房,还可以看到坐在对编机前的潘奕霖红了眼睛。这时候我们嘴巴上会“取笑”一下他,心里明白,感动了自己的作品才更有可能感动观众。
潘奕霖每完成一期节目,都会兴奋地向同事们宣布:“又一期精品诞生了!”其实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诞生一部精品谈何容易,难能可贵的是潘奕霖能认真对待并且始终热爱他做的每一期节目,尽可能让每一期节目都离精品更近一些。电视台常要加班加点,他觉得这很正常,有时会在对编机前坐上一整夜。1997年,他做了矫正近视的激光手术,医生再三嘱咐他在一段时间里不要看电视屏幕,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那段时间《流金岁月》组正在赶制上海电影节特别节目,大量的后期工作需要人盯着,他就戴着墨镜坚持工作。虽然眼睛受到刺激后疼痛不已,眼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淌,但他一直坚守在对编机房,直到节目圆满完成。
潘奕霖跟《流金岁月》特别有缘分,继主持人和编导之后,他又成了《流金岁月》的制片人。制片人、编导和主持人应该算是电视台里最重要的三种角色了,他在《流金岁月》里同时扮演着这三个角色。与大多数电视制片人相比,出身于主持人和编导的潘奕霖别具风格。他身上少了一些章法,多了些感性的东西。他可能不是一个理财的好手,分配经费和报账多少让他有些头疼,但他触摸到了一个节目的灵魂,让一个节目有了情感。这个栏目开播之前,大家就觉得他的形象气质颇符合《流金岁月》的整体风格,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由他娓娓道来,观众满足的并不是猎奇心理,而是浓郁的怀旧情绪和沉甸甸的历史感。当他成为这个栏目的制片人后,这个理念就更加丰厚地展现了出来。经过了几年的积累和实践,他已经可以驾轻就熟地驾驭电视语言,这令他在把握全局和细节时更加游刃有余。
作为一个介绍老电影的“老”栏目,《流金岁月》一直散发着新鲜的活力,这棵参天大树并不缺少年轻的朝气,常有新芽吐穗,才会这么枝繁叶茂。这也跟潘奕霖的努力分不开,平时跟同行或朋友聊天,他常会把话题扯到《流金岁月》上,他也很关心其他电视台的变化,也会借鉴国外电视节目的长处,他总在动脑筋想办法,让《流金岁月》更好看一些。《流金岁月》有过很多次改版,记得有一年推出过一个叫《我爱老电影》的新片场,每次请一位著名电影人到拍摄现场,跟影迷一起聊电影。变一种方式说电影,既有新鲜感和直接的冲击力,又拉近了跟观众的距离。王晓棠、谢芳、葛存壮、郭凯敏等都曾做客《我爱老电影》,让广大观众多方位地了解到电影人的生活和追求。
作为制片人,潘奕霖有很强的号召力、亲和力和协调能力,每次做节目,总能有一帮人死心塌地地跟着他忙前忙后。虽然为节目的事他也跟周围的人急过,但没有人会把那些争执放在心上,事后还会拿他发飙时的表现开开玩笑,他总是心平气和地听大家数落他的“罪状”,然后跟着大家哈哈大笑,有时还会添油加醋地自黑一下。不过在拍摄现场他从不越权:他是主持人而不是制片人,他会听从编导的调遣,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
潘奕霖做活了《流金岁月》,这个栏目不仅成为电影频道的名牌栏目,而且赢得了亿万观众的喜爱。很多观众写信告诉我们,他们看见潘奕霖就想到《流金岁月》,想到那些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经典影片,想到他们自己的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
奕霖作此访谈,多少基于自己难以磨灭的青春记忆,正因此,此书写法就显得格外率性、自然,没有喋喋不休的大背景、大道理,有的是来自亲友之间的娓娓道来,感谢奕霖花了那么多时间组织这样的访谈,也希望这些访谈给大家带去共同的时代性记忆,分享受访者多姿多彩的成长故事!
——中国传媒学术领域第一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 胡智锋
奕霖也是有温暖魔力的人,在这本书里,他采访了十位主持人,都是广院校友,都是他的同行,在奕霖面前,他们从从容容对上密码,自自然然洞开心扉,宝藏故事源源而出。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翁佳